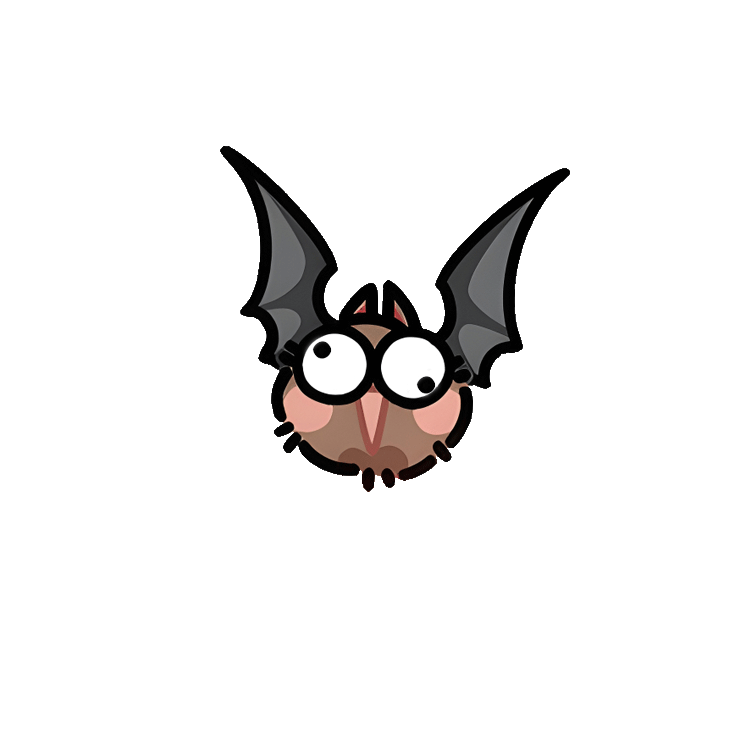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枉然来客Ⅰ❈
深宵,我坐在酒馆爬满锈迹与青苔的窗边,听着远处的夜半钟声。
一下、两下……我低声地数着,不出所料地,它在第十一下时戛然而止,和每天的这个时候一样。
坏掉的主钟无人修理,破败的酒馆歌舞升平——倒的确很符合我对比兰这座位于两国交界处的老城的印象。
毕竟行政上,比兰隶属西边蛮荒的扼索,却不太受其管辖;经济上,它更多依靠东边富庶的卡托斯,却也还是不受其律法的控制。
这样的地方,很快便成为了两侧诸多灰色贸易的温床,而比兰也需要它们漏下的一点金钱来支撑城市的运转。
享受着两国的资源,也承担着两国的罪恶。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边境之城。
在比兰,唯一不用受制于人的,恐怕只有那废弃港口前、漆黑水域中的游鱼了。可惜那个港口也已经很久没有船出海,一片沉沉死气。
这是我来比兰的第三天,而我还没有找到陆沉。
一周前的夜晚,我等待着陆沉从国外出差回来,却突然接到航班取消了的消息——
晚餐搞定,只等出差回来的陆沉了。我满意地拍拍手,又点上之前和陆沉一起在伦敦旅行时买的玫瑰香薰,准备出门去机场接他。
这时,手机推送了陆沉回程的那趟航班取消的消息。
我连忙给他发去信息询问,几乎是下一秒,陆沉回复了我。
陆沉的信息:“是的,天气不好,整条航线的航班都取消了。不过我会想办法早点回到你身边。”
我的信息:“好,不急。注意安全。”
虽然有些失落,但更多的还是担心。
就这样一直辗转到深夜,我逐渐有些困意,半梦半醒间,我感觉到脸颊似乎落下了一点温热的吻。
又带着一点夜晚的冷冽,熟悉的苦艾味绕上鼻尖,我慢慢睁开眼。
我:“陆沉,你回来啦……”
陆沉:“被我吵醒了?”
我:“……”
睡眼仍然朦胧,我下意识摇了摇头,又本能地向他伸出手。
陆沉会意地坐在床边、微微俯身,让我得以环住他的脖颈,又顺势托住我的后背,把我整个人都带到怀里。
我就这样靠着他,等待睡意散去,而他的声音低低地落在我耳边。
陆沉:“本来不想打扰你,但路过门口的时候,闻到了乌木玫瑰,是上次我们一起挑选的香薰。
想起那天在伦敦雨夜的街头,你高高地捧着它,递到我的鼻前时眼神很期待……我忽然就意识到自己今晚错过了什么。没忍住,就想要进来看看你。”
我:“你什么都没有错过……我就在这里呀。”
陆沉笑了起来,低头吻住我,渐而又加深,苦艾的气息便更深地侵入,心跳都跟着缠乱。
直到我们稍稍分开、呼吸渐趋平静,我这才注意到,陆沉的身上似乎沾染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
与此同时,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漆黑的雨夜,一群蝙蝠如阴云在半空盘旋,再眨眼时它们已经密密麻麻覆上陆沉的身体,尖牙刺入皮肤,似乎是在啃食其下血肉——
我顿时回过神来。或许是因为刚刚见到的画面实在恐怖,我的脸色有些不好,陆沉看向我的眼神有隐隐的担忧。
陆沉:“怎么了?”
我没说话,手摸到他的领口处扯开几颗扣子,借着窗外的月光检查起他的身体是不是又多了什么伤口。但还好,都没有异常。
刚想松口气,我又想起血族本身恢复能力很强,也许曾经有过伤口,而他只是在愈合后才来见我……
这么胡思乱想着,这时陆沉似乎已经反应过来我看到了什么。他微微笑了笑,握住我的手,一下一下安抚着揉捏起来。
陆沉:“我没事。只是一个擅长模仿的血族,复制出了一个拙劣的幻境,不足以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我:“模仿?复制出的幻境?”
陆沉:“嗯,一种天赋,在别人释放幻境的时候,可以复制出一小段幻境。但力量会比真正的要小很多。”
我:“原来是这样……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陆沉:“是比较少见。在今天之前,我还以为擅长使用这种天赋的血族已经消失了。”
我还想再问些什么,陆沉却笑了笑,又低头亲了亲我的发顶。
陆沉:“别担心,都是一些普通的事情,不算特别。”
我抿抿嘴,又尝试用天赋感受了一下,也确实没有看到更多的危险。这才略略放心下来。
距离陆沉成为血族家主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陆沉变得比从前更忙,“出差”得更频繁。
他去了许多个我从前闻所未闻的遥远城市,地图上飞行轨迹密织如蛛网,我猜他在清除异声、再借机布下新的棋局,这是更漫长的战争。
但我没有问。因为我知道,这个过程并不比成为家主之前的路好走。
很多个他从那些地方归来的深夜,我触碰他时感受到的都是疲惫甚至近乎死寂的冷意。
我:“陆沉……”
陆沉:“嗯?”
我:“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自己受伤,好吗?”
陆沉:“好,我答应你。”
我的手臂环上他的腰,更深地埋进他的怀里。
我:“想做的事,不想做的事,要做的事,以及不得不做的事……对你来说,现在有很多。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比不上你的安危重要。”
陆沉:“如果要这样比较,我的答案可能有些不同。”
我:“哪里不同?”
陆沉:“你说的那些,都比不上此刻。”
陆沉收紧手臂,也更用力地回抱住我。
陆沉:“比不上此时此刻,你带给我的温度,它是最为真实的存在。”
他的声音渐轻,落在我耳边时仿似融进心跳的叹息。我忍不住把他搂得更紧,希望至少在此刻,他能感到平静。
第二天一早,陆沉便又匆匆离开,他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像往常一样与我吻别。
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一次似乎有些不一样——尤其是在我看到行程图显示他一天内辗转了好几座城市之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他很少这样匆忙,也许昨夜我看到的那段“复制幻境”背后,是一些比以往都更加棘手的事情。我不由得担心起来。
思来想去,反正也在休假,我决定按照陆沉的行程信息,去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找他。
但飞机刚刚落地,我就看到他已经离开了这里。机场休息室中,我再次看向手机屏幕,上面和陆沉的聊天窗口却依然停留在半小时前。
按灭手机屏幕,我有些茫然地环顾四周,却发现面前的桌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只钱包可能是之前的旅客不小心留下的。
可等了好一会也没有人来找,我只好打开钱包准备确认失主的信息。里面有一张机票,目的地还是光启。
只是姓名那一栏里,写的,是我的名字。
与此同时,手机震动几声,跳出了陆沉的消息。
陆沉的信息:“厨房的冰箱里,有红茶芝心蛋糕,浴缸里的泡泡是野莓味。吧台上有新换的咖啡豆,你说很怀念去年我们在彼得堡街头喝的那杯有蜜瓜香气的咖啡。
以及,天气预报说,明日有雨。我们在院子里绑的那一排纸风车正在等待一位好心的兔子小姐,把它们安全地带回家。”
我不禁笑了起来。隔着大半个地球还在家里精心安排了这么多,显然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他希望我回程。
他说的这些的确十分诱人。但他忘了,我之所以喜欢它们,也是因为它们都与他有关。
于是我回复了一个摇头说NO的表情包,果断切到订票的软件,买下了另一张机票。
第二天,我在另一座城市落地——共享位置和行程图显示,昨天陆沉抵达了这里。他从不隐藏这些,即便他希望我返程。
不过,在酒店办理入住时,我收到了前台附赠的下午茶邀请券。
回到房间、打开信封,果然,里面除了邀请券外,还有一张音乐会的门票。是大提琴家“林”的演出,我期待了很久。
只是演出的地点在光启,时间就在明晚。送票人的意图简直一目了然。不过似乎还嫌不够,手机此时又一声嗡鸣。
陆沉的信息:“据可靠消息,“林”会在明晚演奏他十年前首场演出的特别曲目《寂静》。”
我的信息:“谢谢陆记者的报道,的确是很令人心动的消息。可惜现在,我只想找到我“失踪”了十天的男朋友。”
陆沉那边“正在输入”了一会儿,最后,发来了一只小熊逃之夭夭的表情。
渐渐地,这似乎变成了我和陆沉的一种默契游戏——我前往他的城市,他留下劝我返程的信号,而我会在抵达后去寻找,乐此不疲。
直到现在,我来到了比兰。陆沉在抵达这里之后一直没有离开,我便也暂时安顿下来,去每一个他去过的地方一一寻找信号。
而这处酒馆,是陆沉几个小时前刚来过的地方。
我望向酒馆的墙壁。墙上贴满了照片,还有不少色彩艳丽、图案诡异的涂鸦,骷髅、心脏、意味不明的符号,层层叠叠,看得人心惊。还有密密麻麻的“F**k”、“To h”“l with life”之类的宣泄,反而让这片死气沉沉的地方显得生动了一点。
令我有些在意的是,墙上照片大都是合照,还是和同一个人的合照——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而酒保告诉我,男人是比兰的警察局局长。
只要在比兰行动,不论黑的白的灰的,都得到他面前过一眼。因此大家都叫他“守护者麦登”,与他合照代表着比兰最高的荣誉。
最应该被悬置的位置,反而成了这里的守护者。这让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也是这时我发现,在这些合照中,突兀地出现了一张风景照。
从我现在坐的位置往外拍的窗外夜景,钟楼的指针也正好指向十二点。
我直觉这是陆沉留下的。但这回,这张照片里却没有什么希望我回程的信号。
年轻人A:“你听说了吗,死了好几个人。”
正思索着,耳边传来几句压低的议论。我循声望向吧台,是两个年轻人,头发都染成了不均匀的黄色,表情神秘,说话时眼神也飘忽。
年轻人B:“这个月已经四个了吧。偷偷告诉你,前两天我在河边看到了警察运送尸体。那个尸体可太奇怪了,身上明明瘦得皮包骨,跟个骷髅似的,但肚子大得吓人。”
年轻人A:“——诶,你看,她又来了。”
门口风铃响了一声,其中一个人还想说些什么,另一个人推推他的手打断了他,两人一同望去,脸上露出一点恶意的笑容。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大约四十岁,神色颓丧、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开裂的靴子上沾满结块的泥巴,是比兰随处可见的流浪者的装束。
女人一路径直走向吧台,从口袋里掏出两团皱巴巴的纸钞放在了吧台上。
她先是点了一杯特调,又很快摇了摇头,换成了更便宜的龙舌兰,一把抓回了那张多出的纸币,塞回了口袋。
而那两个黄发年轻人正往门口走去,经过女人时,上下扫了她好几眼,又不加掩饰地将手伸进了女人的口袋,拿走了剩下的纸钞。
女人明显察觉到了,她握着酒杯的手在颤抖,却完全没有反抗的意思,只是若无其事地垂下眼睛,苍白干裂的嘴唇紧紧贴住杯沿。
我皱起眉,暗自蓄力准备用天赋出手阻止。
可就在这时,女人突然爆发出惊恐的刺耳尖叫。
女人:“不,照片!照片……”
吧台上的龙舌兰被打翻,女人也没去管,而是疯狂地翻找着自己的口袋,很快她的动作停顿下来,骤然抬起头看向那两个黄发年轻人。
女人:“把照片还回来,还给我!”
下一秒,女人朝那两个黄发年轻人扑了过去——似乎是他们顺手牵羊的时候,还拿走了她的照片。
年轻人A:“哪里来的疯女人!”
原本胆小忍耐的女人一下爆发出了惊人的力气和恐怖的执拗,她撕扯住两个年轻人的衣服,似乎无论如何、就算同归于尽也要拿回照片。
年轻人B:“一张照片跟要命似的,快扔给她,扔给她……”
黄发年轻人连忙掏出照片丢在地上,又趁女人分神之际狠狠踹在她的胸口,就飞也似的跑出了酒馆。
女人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两只手仍不断向前挣扎,想要够到照片,我连忙走过去帮忙捡起,又扶着她在一旁坐下。
那是一张旧照片,折了四折,边缘磨损了,露出的一角上,是一只奇特的、有着星空似的眼睛的猫头鹰。
我还想仔细看,身前女人的喉咙发出浑浊的野兽般的声音,我抬起头,她正直直盯着我手里的照片。于是,我递还给她。
女人:“谢谢,谢谢……”
她小心地捏着照片一角,反复地检查过每处细节,确认没有损坏后,才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女人:“我只有它了……”
我:“这张照片,对你很重要吗?”
她低头看着照片,攥得手指都发白,凌乱打结的头发遮去了她的视线和表情。
女人:“嗯,上面的人,对我很重要。”
我:“既然是重要的东西,那一定要藏好了,别再被那些人发现。”
女人:“你说得对,很对。”
女人用力地点点头,像是认同,却又忽然陷入了沉默,许久都没有再出声。
气氛有些凝固,我偏头看向她刚刚打翻的龙舌兰。
我:“我请你喝酒吧,想喝什么?”
她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脏兮兮的头发背后透出的眼神却意外明亮。
女人:“谢谢。”
女人没有拒绝,但仍旧点了更便宜的那杯。
她和其他流浪者不太一样。或许是因为比起钱,她更看重一张旧照片、或许是因为她的眼神很明亮,人也很有礼貌。
又或许是因为,她掩藏在血迹脏污下的皮肤,不像一名流浪者……
我想说些什么,但女人很快喝完了酒,她的眼神迅速扫过四周,带着一点不想被人察觉的怯懦,在朝我躬身感谢后,飞快站起了身。
没想到这一下她猛地撞到了酒保,酒保嫌恶地伸手一推,她便又踉跄撞上墙壁,照片散落一地,肩膀和头发也都被酒液打湿,很是狼狈。
酒馆里安静了一瞬,霎时间又充满了叫嚷的咒骂声。
这一次她没有再说什么,低头爬起来,沉默地转过身,逃离了这里。
我还是有些担心,正想追上去,却听风铃又是一响,一个熟悉面孔出现在我眼前。
周严:“(ID)小姐,晚上好。”
周严平静地点了点头,显然是早就知道我会在这里。
我:“你知道我在这里?”
周严:“嗯,老板让我来的。”
我:“也对,他在这里留下这张照片,就知道我会找过来。派你来找我,合情合男理。他这次是想给我什么?
机票,酒店的卡片还是一张写着希望我回去的便签?嗯……如果上面写的是“我想见你”之类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收下。”
周严:“老板特意让我来接你,他已经准备好私人飞机。如果你愿意的话,今晚就能回到光启。这句是转述老板的话。”
……倒也是不用连语气都跟着模仿。我转过身,将几张纸钞拍在吧台上示意酒保结账,这才重新看向周严。
我:“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如果我不愿意回去的话,他要怎么做呢?”
周严:“他现在就在比兰,我会把你安全地带到他面前。”
我有些愣住,他终于要停止劝我回去了吗。
可既然如此,陆沉为什么不自己直接来找我?
周严:“老板有别的事情要办,抽不开身。他其实很想来。”
似乎是猜到了我的疑惑,周严又出声解释道。
我:“这句也是你转述的他的话?”
周严:“只有前半句是。”
我:“你倒是不会撒谎。走吧,带我去见他。”
我跟着周严走出酒馆。
比兰的深夜仍有些冷,风刮过皮肤激起战栗,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可走了一会儿,我发现今天的周严有些不对劲——他反而在放慢脚步。
我:“怎么了?”
周严:“有人盯上你了。”
我:“什么时候?”
周严:“应该是你刚进酒馆的时候。”
我:“你那时候就看到我了?”
周严没有回答,但想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他有一位料事如神的老板。
可这才是我到比兰的第三天。在此之前,我甚至从未听过这座城市的名字。
我:“那些人为什么会盯上我?”
周严还是没有说话,我又想到之前陆沉几次希望我返程的信号,难道是他在这里已经遇到了什么事?
我:“那陆沉现在在哪里?”
周严:“老板很安全。”
周严似乎不愿意多说,但这反倒让他的回答显得更真实可信。我略略放下心来,点点头。
就这样一路走到街角,正要拐弯时,前面突然闪出一道人影,是刚才酒馆的黄发年轻人,他的同伴也同时出现在后方,将我和周严堵住。
两人手里都拿着枪,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跟随他们的动作,走进了一条满是恶臭腐烂味的小巷。
年轻人A:“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原来除了盗窃,他们还会大摇大摆地抢劫。
周严:“如果你们真的只是抢劫,这件事情反而变得更好办了。”
年轻人B:“什么意思?”
年轻人A:“别跟他们废话,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年轻人正准备扣下扳机,周严迅速转身,抬腿接连击中他们的手腕,手枪应声落地。
两人一惊,急忙扑向手枪,但一人被周严踢中肩膀,狼狈地跌在地上,另一人被周严拽住了衣领,眼睁睁看着手枪被踢到巷子深处。
见已经拿不回武器,他们干脆一前一后冲上来,想用人数优势围击周严。但周严利落地侧身避开,两人反而撞在了一起。
他们不甘心对视一眼,而周严不动声色上前一步,动作间落下一声枪械声,显然年轻人也注意到了,这回他们不再犹豫,落荒而逃。
意外平息,我陷入沉思。看起来,从我进酒馆开始就盯上我的人,正是那两个年轻人。
他们看起来只为求财,但听周严的意思,似乎他们是别有目的,而这又是怎么回事。
虽然知道周严未必会说,但我还是想试着能不能问问清楚。
我:“周——”
我正准备开口,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眼前一道黑影迅速掠过,重重坠落在地面,很快,脏污的地砖上便漫起一阵殷红。
一具坠楼的尸体,出现在比兰深夜的街头。头骨几乎被摔得粉碎,躯干也有些变形,呈现出一种诡异扭曲的姿态。
我抬起头,看向坠落的来处——高楼顶端,风吹起比兰的旗帜,圆月的辉光中一道黑影一跃而起,很快没入夜幕。
我:“是她……”
怎么会这样?我想再靠近仔细看看,可周严却沉默着挡在了我身前。
或许是为了维护我的安全,又或许……是不想让我更仔细地看?我莫名想起了刚刚高楼上的黑影。
我:“我想去看看。”
周严看了一眼尸体,又看了一眼我,似乎斟酌了片刻他才点点头,退到了一旁。
我俯下身看她,除了难以辨别的面容,身上没有其他明显的伤痕,是坠楼招致的死亡。
或许是为了维护我的安全,又或许……是不想让我更仔细地看?我莫名想起了刚刚高楼上的黑影。
我:“我想去看看。”
周严看了一眼尸体,又看了一眼我,似乎斟酌了片刻他才点点头,退到了一旁。
我俯下身看她,除了难以辨别的面容,身上没有其他明显的伤痕,是坠楼招致的死亡。
又试探着触碰了她的手背,很快,她在坠楼前看到的画面在我眼前浮现——空旷的顶楼,沉黑的夜幕,一道笔直身影似要劈开高扬旗帜。
猎猎夜风掀起了他的衣角,也吹乱他的额发,露出底下那双暗红色的眼睛。
是陆沉。
我想起那道没入夜幕的黑影,也就是说,刚才他就在坠楼的现场?为什么?
身份明显不一般的女人、有着一只猫头鹰的旧照片、突然的坠楼死亡、陆沉的踪迹与行动……我的思绪混乱起来。
这时,耳边忽然传来尖锐急促的警铃声。
回过神时,一群人已经冲进巷子。月光勉强照亮他们的制服和胸前警徽,看来是当地警署的人。
为首的,是一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他的下巴上布满胡茬,眼神里藏着几分超越这个年纪的老练。
我:“……“守护者麦登”?”
麦登:“看来有位外乡人已经开始融入这里了。”
麦登看了尸体一眼才看向我,又意味莫明地笑了一声。
麦登:“跟我来吧,我有话要问两位。”
我看向麦登身后列队的警察,人数众多,正面冲突并不是理想方案。而身侧的周严也冲我点了点头。
于是我同意了,红蓝灯光闪过一路,我和周严被带到了警局。警局大厅被荧光灯笼罩在一片惨白中,久不流通的空气里满是呛人烟雾。
于是我同意了,红蓝灯光闪过一路,我和周严被带到了警局。警局大厅被荧光灯笼罩在一片惨白中,久不流通的空气里满是呛人烟雾。
我们分别被关在两个审讯室里。进门前,我听到狭窄的走廊深处传来一声绝望叫喊,又很快被沉重的门扉吞没。
审讯室的温度似乎比外面更低上几分,四面墙壁是压抑的深色,还有几道浅浅的划痕,像是人在挣扎时用指甲留下的刮擦。
我坐在冰冷坚硬的金属椅上,麦登站在我对面,正在看我刚才填写的信息表。再抬头时他的眼神又冷下去几分。
麦登:“姓名。”
我:“(ID)”
麦登:“不是本地人?”
我:“嗯。”
麦登:“你认识她?”
我:“她是谁?”
我当然知道他在问谁。但就像是他明知故问要问我姓名一样,我也同样抛出问题。
麦登:“酒馆里很多人都看到你们一起喝酒。跟我装傻,对你没什么好处。”
麦登的眼底浮起愠色。
我看着他,歪了歪头,又思考一会后,一摊手。
我:“不认识。”
麦登:“在比兰,没有人会请陌生人喝酒,除非对对方有所图谋。”
我:“可是,警长,我不是比兰人。这一点您不是刚刚才确认过吗?所以,我请谁喝酒又有什么关系。”
我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麦登的脸色果然沉了下来。
他双手按在审讯桌上,压身朝我迫近,吊灯在他头顶跟着人影摇晃,闪烁的光芒格外刺眼。
麦登:“果然是外乡人,还不太清楚比兰的规矩。看来,在我们继续审讯之前,该让你知道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看来,两句反问就是他的底线了。暂时不能硬碰硬。我思索片刻,开口解释起来。
我:“只是看到她被人欺负,又丢了钱,就请她喝杯酒。算是一点同情心吧。”
麦登:“就这么简单?”
我:“就这么简单。”
顿了顿,我抬眼,目光直直看向麦登。
我:“我也有一个问题。”
麦登:“说。”
我又想起了那个女人明亮的眼神和躬身道谢的样子,不知为何,我隐隐觉得她并不是坏人。
我:“她叫什么名字?”
麦登有些意外,像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麦登:“谁?”
我:“那个死去的女人。”
麦登:“她叫玛莲娜。”
我:“玛莲娜……”
我默念了一遍她的名字,心情有些复杂。
麦登盯着我,似乎有些玩味。
麦登:“说吧,你来比兰的目的是什么?”
我:“来找人。”
麦登:“找谁?”
我:“这似乎与本案无关。”
麦登:“有没有关系,我说了算。”
这么说着,麦登靠近我的耳边,威胁着压低了声音。
麦登:“就像是,你今晚有没有犯罪,也由我说了算。”
心头涌上难以抑制的反感,我抑制着要起身的冲动,维持着脸上波澜不惊的神色。
他几乎已经挑明,不论真相如何,他都有足够的权力让我被认定为凶手。这就是即便在两不管的比兰,也能站稳脚跟的警局局长。
这时麦登直起身,笑了起来。
麦登:“你以为他们为什么称呼我为“守护者麦登”?”
我:“不难猜,你是这里的警长。”
麦登:“在比兰,“守护者”的定义就不太一样了。人们很喜欢和我拍合照,但大多都不是因为爱戴我,而是想得到我的庇护OTHERS而你,在这里是没有人庇护的,你该知道,那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从腰间取出一枚手铐,将手伸向了我……我仍是抬头看着他,忍耐着刺眼的灯光和令人不适的气氛,努力保持着至少神色上的平静,与他对峙。
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防弹门传来一声轻响,随即又洞开,一个熟悉声音落在耳边。
陆沉:“抱歉,警长,但这位小姐确实受到人庇护。而且庇护她的人,就在这里。”
是陆沉。他没有戴眼镜,身上带着夜风的冷意,可神色又分明自若,似乎这里并非比兰警局,而只是属于他的某处领地。
他先是垂眼看我,安抚地笑了笑,又走到我身前隔开了我和麦登之间的距离。
陆沉:“我就是她在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