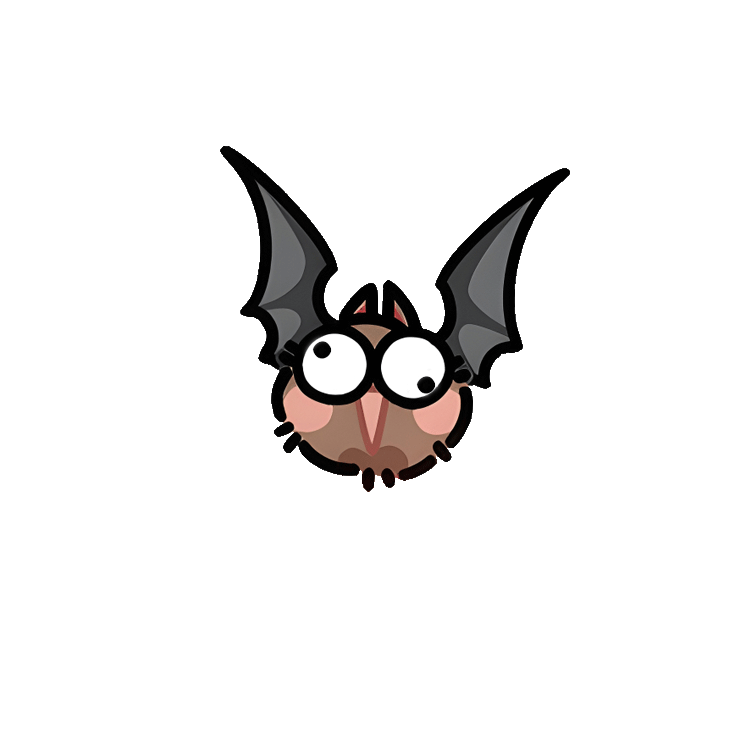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前置剧情❈
除夕刚过不久,屋外寒风料峭,卷着细雪纷纷扬扬地落下,给光启城的街巷覆上了一层茫茫的白。
屋内的炭盆烧得正旺,橘红的火苗跳跃着,驱散了雪天的寒意。
我将账册摊在桌上,噼里啪啦地拨动着算盘珠子,核对着这个月客栈的营收。
布料抖动的窸窣声响起,我抬眼去看,门口厚厚的布帘被掀开,我的贴身婢女茴儿搓着手走了进来,肩头还沾着一点未化的积雪。
茴儿:“小姐,上元节要用的灯烛、彩绦,还有给客人们备的果点,都按单子采买齐了。”
我倒了一盏热茶递过去,接过茴儿递来的采购清单,一行行仔细查看。
茴儿:“这光启城里的东西,可比咱们濯州贵许多。那些鲜花和果子的作价足足翻了六七倍不止!就算冬日里东西紧俏,也不该高到这个地步。”
茴儿一边拍打着身上的落雪,一边忍不住小声抱怨。
目光下移,一枚鲜桃的作价近二十文。若在濯州,足可提回满满一篮了,的确是贵了些。
不过这光启城中的铺子家家皆是这个价格,定价多寡,全凭商会决定,寻常人哪里有别的选择。
从前不是没有外地商人想来开家平价铺子,可每开一家,光启商会便去排挤一家。
到最后,那些铺子里货架空悬,房租无着,只得关张了事。
我放下单子,看见茴儿犹自气鼓鼓地站着,笑着捏了捏她的脸。
我:“光启城毕竟是天子脚下,比濯州贵些也正常。好啦,我新琢磨了一种花糕,预备添作上元节的新品。等下做出来,先给你尝个鲜?”
茴儿闻言撇了撇嘴,又想到了什么似的看向我。
茴儿:“小姐您怎么光想着上元节的安排,那件事您也得上点心呀!那……那可才是头等大事呢。”
她这样的语气,这段时间我是日日享用,我合上手中的账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那事儿急也急不来呀……”
思绪不由飘到了一年多以前。
那时我从南方海畔的小城濯州,辗转来到光启城。
我的爹娘为大晟征战多年,曾助当今圣上平定了边境叛乱,战功赫赫。
天下安定后,他们以年事已高为由自请辞官,带着年幼的我归隐濯州。
很长一段时间里,爹爹在濯州任微末小官,娘亲则开了家药铺行医配药,我在铺子里帮衬着日子平淡却也安宁美满。
可就在去年,爹娘相继离世,娘亲弥留之际告诉我,她在光启城为我留了一间商铺。
她知道我一向喜欢经商,若我心愿未改,便可回到光启城去。
来到光启后,我筹措资金,磕磕绊绊地开了家客栈,几个月后,生意也渐渐步入了正轨。
然而,不久前一道圣旨打破了我忙碌而平静的生活——圣上突然召见了我。
他说感念爹娘昔年的忠勤,要封我为县主。我并不想卷入这些朝堂纷争,只想安安静静地做点自己的小生意,因此便婉拒了。
可圣上话锋一转,又说要为我指婚,还特意点了在场的三位勋贵,询问他们家中可有适龄公子,让我择一定亲。
皇帝:“如何?这三位公子皆是良配,任你选哪一位都使得。”
大殿之中安静得针落可闻,落在身上的目光有如实质,我低头跪着,心中是叫苦不迭。
我根本不想同这些世家大族扯上关系,我与他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如何能定亲呢?
况且,这三家背后牵扯的势力盘根错节,哪一家都不是我能招惹的。真要嫁入这样的门第,往后想再出来经营客栈,更是难如登天了。
见我没有应声,皇帝看着我,叹了口气。
皇帝:“可是对朕的赏赐心有顾虑?这么多年,朕的确对你们有些疏忽了……你心中该不会怪朕吧?”
这一问,惊得我冷汗涔涔,这“该不会怪朕”,与当年夫子明知我未交功课,偏还笑着问我“今日玩得可好”,有何分别?
他多半还是忌惮我双亲威名犹在,旧部如云,想将我放在眼皮底下“看顾”起来。
圣心难测,手指叩击龙椅的声音一下下在我耳畔响起。
我心一横,清了清嗓子朗声开口。
我:“圣上言重了,爹娘在世时常教导民女要感念您的恩德。实在是因为爹娘在濯州时已为民女定下亲事。只因双亲骤然离世,民女尚在孝期,按礼制才不能完婚。”
本朝素来讲究一诺千金、贫贱不移。果然,圣上顿了顿,无形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审视良久。
皇帝:“原来如此,倒是可惜了。”
这关暂时过去,我立刻顺势将心中早已酝酿好的话说出。
民女自幼便立志经商,如今我大晟国泰民安,盛世繁华。
我:“民女便也想在光启城试着做些生意,不辜负这好年月。”
我这番诚恳的恭维显然让皇帝满意了,他微微颔首,语气缓和许多。
皇帝:“好一个“国泰民安”。既如此,朕便赐你一块“安业楼”的匾额做你客栈的招牌。希望你能安守本业,等到你成亲之日,朕会再命人送上一份厚礼。”
原以为圣上不过心血来潮,不多时便将我忘了,可两月后,宫里遣了人来,说是圣上惦记着,问亲事筹办得如何,可需要帮忙。
还说过段时日便是合欢节,邀我携家眷入宫赴宴游园……可我哪里能凭空变出个定亲对象来?
往后的麻烦事一定不会少,但也只能再想想办法,好歹先将眼前这关搪塞过去。
我摩挲着手中的账册,暗自思索着,或许我可以离开光启,回濯州去?到时候天高皇帝远,想来圣上也管不到我这孤女。
可这样就要放弃光启城里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的产业,实在是下下之策。
或者……等皇帝问起,我就说我那定过亲的夫婿不久前遭了意外过世了?
不行,这法子漏洞太多,经不起查证,稍有不慎就是欺君之罪。
思来想去,为今之计,唯有找一个可靠的人合计此事。那人需得知根知底,更要愿意担这份风险才好……
这样想着,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浮现在脑海中……
彼时,我在集市上瞧见了濯州才有的泥人娃娃一时兴奋忘形,扯住了他的衣袖。
那人侧过头看着我,目光温和,眼底隐含笑意,轻轻问我“怎么”?
后来,那对憨态可掬的泥人娃娃便被他买来,搁在了我的柜台上,我戳了戳泥娃娃胖乎乎的脸,若是……
茴儿:“陆老板。”
骤然听到这名字,我的心口颤了颤,声音也不自觉地带上几分慌乱。
我:“我还在想人选呢,可没准备找他!”
茴儿:“找谁,陆老板?这会找他做什么?”
见茴儿一脸茫然,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轻咳一声,低头假装整理账册。
我:“咳,我听岔了,你刚才在说什么?陆沉怎么了?”
茴儿:“外面都在传陆氏钱庄资金出了大问题,可能要关张了。”
我一下将方才那点不自在抛之脑后,立刻抬起头来。
我:“关张?怎么可能,前阵子不一直好好的吗?”
茴儿:“就是说啊……真是古怪,我刚去采买时路过陆氏钱庄。听了这传闻来兑钱的人排成了一条长龙,把半条街都给堵了。”
陆氏钱庄是陆沉家中的产业,也是他初到光启最先经营的生意之一,口碑一向极好,没道理会传出这样的流言,除非是有人蓄意为之。
莫非是商会?我倒清楚陆氏和商会素有旧怨,皆因陆氏的存钱利息给得优厚,放贷利钱又低,商贾百姓都爱去陆氏,商会早有不满。
先前他们就没少使些明里暗里的手段,如今又……
我不由蹙起眉,心知这样的挤兑对任何一家钱庄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短期内储户集中兑钱,等到库房现银告罄,无力兑付时,钱庄的信誉瞬间便会崩塌,到时纵有再厉害的手段也难逃关张的命运。
一旁的茴儿也忧心忡忡。
茴儿:“小姐,陆氏不会真关张吧?陆老板可是个好人呢。上个月他瞧见咱们的门帘薄了,还特意送了条加厚的来呢。”
我望向窗外纷扬的细雪,去年回到光启时的景象浮现在眼前。
彼时的我,踌躇满志地想要开起自己的客栈,却没料到光启城的物价这般高昂。
爹娘留下的积蓄连同变卖濯州房产所得的银钱很快便捉襟见肘,可我却连店中的家具都未能置办齐全,更遑论雇佣伙计的工钱了。
没法子,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寻钱庄贷钱。
接连几天,我跑遍了光启城大大小小的钱庄,可这些钱庄开出的利钱极高,条款也霸道得很。
我试着问,可否用铺子三年的租赁权当做抵押。
对方却说我未曾做过生意,又无人作保,他们担着我大概率还不上钱的风险,抵押物要整个客栈加上地契,利钱则半点也不肯松口。
起初,我天真地当他们担心我初出茅庐,没有经营铺子的经验。
于是熬了几宿灯油,精心撰写了一份客栈的经营规划,里头包含了经过详细考察和测算过的开销与进项,想要同钱庄争取。
可根本没人肯多看一眼。规划书一次次递出去,换来的总是那句“要不你再去别家看看”。
原来,我这种没有根基,没有经验的商人,是入不了他们眼的。
天色将晚,油灯的光斜斜铺在地上,客栈大堂里,只摆了一半的桌椅,另一半显得有些空荡。
空着便空着吧,横竖今夜只我一个“客人”。我索性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喝着。
心里有些无助,却也明白没什么可抱怨的——人家也是做生意,不肯把钱借给没把握的人,本也正常。
喝着喝着,面前暗了暗,坐下个人来。我有些微醺,视线也朦胧,抬眼望过去,来人是租下我隔壁铺子的陆沉,与我倒也相熟。
我:“陆沉,你怎么来这里了?”
陆沉:“方才路过这里,见屋子里亮着灯,你在喝酒。便想着进来讨一杯酒喝。”
骗人,他平日里最是守礼,哪会随便进人铺子讨酒喝?
我嘴唇抿了抿,还是倒了一杯酒推过去。
他的目光落在摊在我面前的规划书上,伸手轻轻翻了起来。
陆沉:“这是什么?”
我:“没什么……随手写的一些想法,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陆沉的神色却带着几分认真的赞赏。
陆沉:“我倒是觉得你这随手写的想法,写得很好。”
我只当他在说客套话安慰我,垂下眼睛,声音里带了点赌气的意味。
我:“你也就是随口安慰我罢了,未必认真看了。”
陆沉:“认真看了的。”
陆沉笑着,指着纸页上的字给我看。
陆沉:“这里账簿的“簿”,你少写了两笔,我都看到了。”
我凑近一看,果然如他所说,一时有些语塞。
我:“那你说一说,具体有多好?”
陆沉摸了摸下巴,故作沉吟之态,说得煞有介事。
陆沉:“若是能照着这规划做出来,寻常酒楼应当都会被比下去。但若是想要赶上“玲珑阁”的气派,怕还是有些困难。”
我被他逗笑了,玲珑阁是光启城最好的酒楼,幕后老板是位致仕的太傅,店里的桌椅杯碟皆是上等物件,自然气派得很。
我:“本来也没想着和玲珑阁比。”
陆沉望着我,眼中是和煦的笑意。
我吸了吸泛酸的鼻子,低声向他道谢,指尖无意识在桌面划着,轻轻叹了口气。
我:“做生意可真难啊……看中的东西买不起,银子总是不够用,处处都得求着人。”
陆沉笑了,也学着我的样子一手撑着脸,叹了口气。
陆沉:“是真难,你瞧我的钱庄刚刚开张,眼下不也找不到主顾?我让伙计去门口吆喝,想赚些人气,结果你猜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好奇起来,他家大业大,竟也有这样的烦恼?陆沉摇了摇头,神色颇有些无奈。
陆沉:“喊了半日,只有一个老婆婆走进来了。还是因为她耳背,把“存钱付息”听成了“赠米三升”,进来就问我讨米呢。”
这遭遇听着又惨又好笑,我忍了忍,到底还是笑了出来。
陆沉:“连着几日没开张,钱庄的伙计已经有些无精打采了。现下正需要一单开张生意,给他们提提士气,也能讨个好彩头。”
我的酒意醒了三分,放下杯子来定定看着他。
我:“你是说……”
陆沉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也望着我,唇边泛起浅浅的笑意。
清夜沉沉,有风顺着大门半开的缝隙吹进来,烛火摇曳,在他眼底落下忽明忽暗的光影。
陆沉:“我在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第一个主顾?”
像是在做梦一般。
他从柜台上拿来了纸笔,当场便将契约写了下来,我们各自签下了名字,契约便算成了。
我一直都知道,陆沉将钱贷给我,实在是冒了不小的风险,那时我既无人作保,又没有半点经商实绩。
可他不仅贷了,利钱比别家低了许多,连抵押物也只收了铺子两年的租赁权。
我不想辜负他的信任,唯有再努力一些。有了这及时雨般的银钱,客栈的筹备终于顺顺当当推进起来。
我几乎天天泡在客栈里,凡事都亲力亲为,连铺面的瓦当纹样都要亲手描过,力求与其他铺子做出区别来。
至于陆沉那边,钱庄的生意也日渐红火起来,口碑很快便在光启传开了。
上次我去钱庄办事,见往来的人络绎不绝,那贷钱存款的簿册,也装订得足有半尺厚了。
我:“陆老板真是生意兴隆呀!”
陆沉笑了笑,伸手将册子翻到第一页,正是我们当初签下的那张单子。
陆沉:“是沾了你的福气。”
后来我们各自忙碌,见面的次数少了些,但陆沉得了空,仍会到客栈来瞧一瞧。
这日,我正拈着一片琉璃瓦,同工匠交代着细节。
我:“这里要打磨得再精细些。”
工匠:“东家,这瓦片又不是珠串首饰,我都磨了一个时辰了,已经够精细了。”
我:“那可不成,边边角角都还很毛糙呢。”
工匠皱着眉,一脸不情愿。我正思忖着要怎么同他说,身后便传来一道温润的嗓音。
陆沉:“让我来试一试吧。”
循声望去,陆沉不知何时走了进来,拾起一片琉璃瓦细细地看了看。我有些惊喜,笑着同他打趣。
我:“怎么,亲自过来监工,看我有没有乱花你的钱?”
陆沉放下琉璃瓦,抬眸看向我,唇角轻轻扬起。
陆沉:“钱已经落到了你的口袋里,自然都由你说了算。”
四目相对,我们两个都笑了出来。
陆沉走到我身边,取过桌上的砂纸,迎着天光细细看了看琉璃瓦的边角,随后抬手打磨起来,力道不重,落点却是精准。
沙沙声细密匀实,不疾不徐,不过半盏茶的工夫,他将打磨好的琉璃瓦递了过来。
陆沉:“请(ID)老板过目,可还满意?”
沁凉的瓦片落在手心,光滑清透,再无半分毛糙。我递给匠人一瞧,他登时哑然,抱着余下的琉璃瓦默默干活去了。
他难得来一趟,还要帮我做活,我抿了抿唇,有些不好意思。眼见暮色渐沉,我便拉着陆沉到大堂中央的长椅上坐下。
我:“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陆沉:“看什么?”
我:“等一等就有了。”
我也在陆沉身旁坐下,一会儿探头看看外面的天空,一会儿又仰头瞧瞧屋顶的缺口。
我们两个就这么围在桌子旁,静静地等着。
不多时,月亮出来了,月光从屋顶的琉璃瓦落下,在桌子中央映出一个圆圆的小月亮,周围也荡出波浪一样的柔光。
我摊开手放在月亮上,轻轻一晃,像是掬起了一捧月光。
我:“方才不是我吹毛求疵,而是……”
陆沉:“而是不将表面打磨光滑了,月光透下来便也是毛毛糙糙的。自然也就没有此刻,我们共赏的这一颗小月亮了。”
我:“你早便知道我想用琉璃瓦借月光?”
陆沉:“嗯,大堂中央的屋顶空着一块,地上又放着许多琉璃瓦。你想要做什么,大概可以猜到。”
他顿了顿,眼底的笑意也像是浸满了月光。
陆沉:“不过,即便你真的想吹毛求疵,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为什么?”
陆沉:“做生意本就该这样,多一分认真,便多一分能让客人信得过的底气。”
月华将陆沉的身影笼在一片柔光之中,我看着他,像是有一片羽毛轻轻落在了我心上。
我:“说起来,还要谢谢你今日帮了我的忙,可有什么想要的谢礼?”
陆沉眸光微动,沉吟了片刻。
陆沉:“那么这张可以赏“月亮”的桌子,若我想预定,便留给我如何?”
他的眼里映着那一轮小月亮,我心里忽地软了软,弯起唇角笑着应他。
我:“好,这张桌子我专门留给你,你要记得来。”
日子就这样如流水般淌过,转眼就到了开店前最后的筹备,麻烦事接踵而来。
店小二做事总出岔子,谈好的厨子临了反悔不来,采买的新粮掺了陈米……桩桩件件都让人焦头烂额。
某日刚好同陆沉说起,他便将他管理店铺的诸般经验心得倾囊相授,我试了试,果然很有用。
我忙着筹备开业,每日脚不沾地,陆沉也同样忙碌,我们偶尔能在各自店铺打烊的时分遇上。
街上的吃食店大多关了门,只有街角一家卖鸡汤馎饦的小摊还冒着热气。
我看看陆沉身上的锦缎长袍,又瞧瞧摊子上简陋的木桌矮凳,正琢磨着叫他坐这会不会有些唐突。
却见陆沉已经从容地撩袍落座,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还邀请我也一同坐下。
冒着热气的粗陶大碗很快端了上来,浓郁的鸡汤香气扑面而来。我看着陆沉低下头,安静地吃了起来。
我:“我还以为你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会喜欢这样的食物呢?”
陆沉舀起一勺热汤,垂眸吹了一吹,热气氤氲模糊了他的眉眼,他笑了笑。
陆沉:“早几年在外行商,风餐露宿是常事。有时为了赶路,错过了客栈,一整天也未必能吃上一顿热饭。
那时若是能吃上一碗这样的馎饦,大概会觉得,人间至味也不过如此。”
氤氲的热气驱散了夜晚的寒凉,热腾腾的鸡汤馎饦熨帖了五脏六腑。
我托着脸,看向对面坐着的陆沉,远处是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好在此时此刻,我也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就这么过了数月,我与陆沉都在光启站稳了脚跟。陆氏钱庄以存息厚、贷息薄、从不坑骗主顾,迅速攒起了好口碑。
我的“安业楼”也挂上了御赐的金匾,凭借着周到的服务和美味的饭菜,渐渐在光启城中传开了名头。
这之后,我们两个都越来越忙,几乎没有坐下来好好说话的时候了,但那份于微时建立起的情谊和默契却未曾消减。
我们还是会不时关注彼此的情况,偶尔遇上波折会互相问一问,有了值得庆贺的事情,也会带上一壶好酒或好茶,向对方道一声贺。
思绪回笼,我想了想,放下了手中的笔。
我:“茴儿,去把我装银钱的匣子拿来。”
茴儿很快捧来一个沉甸甸的匣子,我打开细数里头的银锭和银票,加起来足有一千余两,这是安业楼这一年来全部的盈利。
原本我是计划用这笔钱开一家分店,或者将旁边闲置的铺子也盘下来,将客栈扩建成邸店。
但眼下,他应该比我更需要这笔钱。
趁着天色还不算晚,我抱着钱匣来到陆氏钱庄的门口。
钱庄大门被黑压压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焦急的储户们挤在门口,吵嚷着要兑付银钱。
维持秩序的伙计和管事忙着核对存单发放银两,累得满头是汗,见我走上前,头也来不及抬,扬手示意我往队尾去。
管事:“这位姑娘,兑付请到后头排队。”
我:“管事,我不是来兑付的,是来还钱的。”
“还钱”两个字在喧闹的人群中显得有些突兀,管事愣了愣,抬头细看了看,认出了我。
管事:“原来是您!您稍等,容我进去禀报一声。”
管事说着便匆匆离开,没过多久,陆沉的侍从便快步走了出来,躬身邀请我进后院。
侍从:“东家请您去内院一叙,您跟我来。”
我随侍从穿过几重月洞门踏入内院,比起上次来时,院中的池塘中央多了座小巧的假山,不知是何时添置的。
曲水环绕,几枝翠竹掩映着乌瓦白墙,处处透着不落俗套的清雅。
院中的那株红梅上次来时还是光秃秃的几根枝丫,现下已经开花了,红梅点点,清冽幽远的梅香在空气中浮动。
陆沉曾同我说过,他琛州的院中也种了一株梅花,是他幼时亲手所栽。
经年累月,想来已亭亭如盖,花开时节,定比眼前这株更为好看。
这样漫无目的地想着,我踏入室内,屋子里的暖意夹杂着沉水香的气息扑面而来。转过屏风我想见的人便出现在眼前——
方桌之上,棋盘铺展,黑白子纵横交错,远远看着,便觉战局正酣。
骨节分明的手指在棋盘边缘轻轻叩了叩,旋即“啪嗒”一声轻响,一枚墨玉棋子稳稳落在棋盘上。
视线循着执棋的手向上,许久未见的陆沉身着玄色氅衣背窗而坐,正与下属周严对弈。
窗外,正是那株凌寒盛放的红梅。
飘飘扬扬的细雪被吹进窗棂,四面的雪光映着他轮廓分明的脸庞,更显眉目清俊。
他微垂着眼,一手撑着脸,另一手拈着棋子,似乎正在凝神推演。
面上倒没见什么焦躁,仍是一副往日里气定神闲的模样。
再走近些,我才看见桌上还搁着个锦盒,他与周严正低声说着什么。
陆沉:“商会那边没有收下?”
周严:“是,他们说……除非咱们也把利钱提上去。”
陆沉又捻了捻棋子,有些漫不经心似的。
陆沉:“那就由他们去吧,不必理会。”
周严:“要将这些银钱送回库房去吗?”
陆沉:“便拿去柜台,给管事支用吧。别说是商会那边不收,就说我今日又省下一笔款项,他一定高兴。”
他眼底闪过一丝促狭的笑意,带着些善意的调皮。周严也忍不住笑了。
周严:“是,他正急得焦头烂额,得了这消息,定能高兴些。”
我心下了然,想来是他派人给商会送了些“薄礼”,却碰了钉子。
我轻叹一声,眼下这样的挤兑潮,对方显然已下了死手,摆明了要挤垮钱庄,又怎会轻易放过陆氏?
陆沉放下手中的棋子,朝门口望来,见是我,眼里绽开了淡淡的笑意。
他起身迎上前,周严随之站起,得了陆沉首肯,向我行了一礼,躬身退了出去。
陆沉:“这几日下了雪,来的路上想必不大好走。”
他将矮榻边的暖炉往桌旁挪了一挪。
陆沉:“你的裙摆上沾了些雪,快过来烤一烤我依言坐下,陆沉又递过一个软垫。”
他提起一旁的火炉上温着的茶壶,为我斟茶。清透的茶汤注入茶盏,逸散出一种如雪后初霁般的清冷幽香。
陆沉:“有段时日没有见了,(ID)老板一切安好?”
我:“是有段时日了,我还以为,你见了我,会先问我来做什么呢。”
陆沉笑了,又给自己添了些茶。
陆沉:“我以为你是知道我得了好茶,特意过来尝一尝。刚从琛州运来的雪茶,正好请你尝尝我家乡的味道。”
我托起茶盏,浅浅喝了一口。
我:“茶香清冽,回味悠长,果然是好茶。”
陆沉:“喜欢的话,给你备了两盒,等会让(ID)老板带走。”
我:“只有两盒吗?”
陆沉失笑,无奈似的摇了摇头。
陆沉:“好吧,再匀一盒我的给你。”
如此轻松的氛围渐渐抚平了我来时的焦躁。
我:“我是不是扰了你对弈的雅兴?”
陆沉:“我与周严方才并未对弈。是我最近新得了本棋谱,便想试试左右互搏,游戏一番罢了。”
我来了点兴致,垂眸打量起棋盘上的局势。只见棋盘上白棋攻势凌厉,黑棋被逼得几乎不能招架。
我:“看样子,白棋快要赢了?”
陆沉笑而不语,手指拈起一枚黑棋,轻轻落在棋盘一角,局面顷刻逆转。
原本被压制得几乎喘不过气的黑棋,瞬间便被注入生机,几处看似孤立的棋子遥相呼应,隐隐对咄咄逼人的白棋形成了合围之势。
这一手落得极妙,见我眸中闪过惊奇,陆沉温声开口。
陆沉:“白棋攻势凶猛,看似占尽先机,却逼得太急,后方反倒走薄。而黑棋看似弱势,实则步步为营,根基扎实,仍有反击之力。这棋局的胜负还犹未可知。”
这样自己同自己下棋,白棋占优,你便帮黑棋,黑棋上风,你又要帮白棋。
我:“下到最后,最可能的结果,岂不就是和棋?”
陆沉思索片刻,微微点了点头。
陆沉:“和棋倒也的确是不错的结果。双方各不相让,不如在这一方天地生生不息。”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这盘风云突变的棋局,隐隐觉得陆沉话中有话。
这时,他将目光转向我放在一侧的木匣。
陆沉:“听管事说,你今日来,是给我送钱的?”
收回思绪,我点了点头,将钱匣打开。
我:“嗯,先前向你借的八百两,连同利息,如数还上。”
陆沉没有去看匣子里的银钱,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陆沉:“我们约好的时间还没到。”
我:“现在你更需要用到钱。”
他微微一怔,随即眼中笑意更深,语气也带上了一点促狭。
陆沉:“难道不该祈祷我关门大吉,这样你连本带利都能省下。”
听出了他的玩笑话,我笑着摇摇头,将匣子往前一推。
我:“那可不行,过段时间我还打算开新铺子呢。你这里的利钱低,我还想再贷一笔大的,你可不能关张。
况且,这本就是你的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能帮上你一些自然最好,若是帮不上,也算我完成了与你的契约。”
陆沉顿了顿,定定看着我,半晌轻轻笑了笑。
陆沉:“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多谢。”
见他收下,我心头微松,正要起身告辞的时候却听到陆沉再度开口。你愿意和我再签一份新的契书吗?同等的银钱数额,两年为期,息钱照旧。如何?
我怔了怔,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他这是什么意思?
陆沉眼底含笑,不急不慢地解释道。
陆沉:“方才收下你的钱,是承你的情。上元节将至,你店中花销想必不小。”
话是如此,可他眼下的境况……我一时有些犹豫陆沉却看出了我的顾虑,笑着敲了敲棋盘。
陆沉:“不用担心,陆氏钱庄不会那么容易就关张大吉的。你即便信不过我的话,总也该信一信我的经营手段。”
是了,陆沉是个很厉害的商人,他这番话说起来,倒带上些笃定和傲然了。
话已至此,再推辞反倒显得矫情,我跟陆沉签完了新的契书,拿着银匣和陆沉送的三盒雪茶起身告辞。
他一路送我,院中新雪未扫,踩上去嘎吱作响,我低着头,看陆沉的锦靴与我并排落在雪地上。
没法在钱庄的事上帮到陆沉,我心中不免低落,一路无话,也不抬头,就这么兀自走着。
忽地,身旁的锦靴停下来,我也随之停下,不明所以地抬头看他。
陆沉:“明日便是上元节,安业楼想必筹备了不少活动。我也想过去凑凑热闹,(ID)老板肯不肯接待?”
陆沉抬眸望来,红梅的疏影落在他眼底,沉静的眸中似乎多了几分融融的暖意。
帮不上他的忙,能让他散散心也是好的,我用力点了点头。
上元夜是大晟百姓在除夕之外最隆重的节日,街上游人如织,灯火辉煌,处处都是欢声笑语。
安业楼内焕然一新,廊檐下悬挂起各式花灯,圆的、方的、花朵的,连缀成一片摇曳的光河。
大堂内人头攒动,宾客如云,其中不乏锦衣华服的勋贵子弟,跑堂的伙计们穿梭其间,忙得几乎脚不沾地。
我招呼着往来的客人,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一楼的角落,陆沉正静坐在那里。
他独自坐在一张八仙桌旁,正端着茶盏望向大堂中嬉闹的孩童和花灯下的人群。
我远远看着,他的神情同往日没什么分别,但在周围喧嚣热闹的映衬下,却莫名让我觉得有几分孤寂。
就在这时,身旁走来几位提着花灯的年轻女郎,其中一个凑到同伴身旁,声音里还带着几分羞涩。
小姐:“你们看那边,不知是哪家的公子?生得好生俊朗!怎么以前从未见过?”
还未等同伴回应,一道带着明显轻蔑的声音横插进来。
???:“嘁!不过是个没有靠山的商人,便是有一副好皮囊又能怎样。”
我侧头望过去,说话的是个衣着华贵的年轻公子,我一眼便认了出来,是光启商会一位高层的子侄,似乎是姓刘。
那几位年轻女郎听见这话,显然有些忌惮刘公子的身份,当即点头附和了几句,悻悻地提着花灯离开了。
我收回视线,心头莫名有些憋闷,径直拨开人群,走到了陆沉桌前。
我:“怎么来光顾着喝茶,不在店里逛一逛吗?”
陆沉抬头,见是我,唇边泛起温和的笑意。
陆沉:“好,那便逛一逛。”
我一路走一路介绍今日在店中布置的一些小巧思,每每说了前半段,陆沉便能接上后半段。
走到大堂中央,陆沉忽然停下脚步,目光落在悬挂高处的琉璃灯上,层叠的琉璃花瓣在烛火的映照下美不胜收。
陆沉:“流光溢彩,栩栩如生,这样的技艺,想来是出自淮扬广陵匠之手。”
我:“好眼力!这次筹备活动的经费,将近一半都砸在这盏琉璃花灯上了。这也是今晚最大的彩头。”
陆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琉璃花灯下,不少客人正兴致勃勃地围着千机锁摆弄,他眼中掠过一丝了然与赞许。
陆沉:“很值得。以这盏花灯作噱头,吸引来的客流价值,远远超过了这盏灯本身。”
我拊掌一笑,有些小得意。
我:“嗯,我计算过,便是每人进来只喝一碗最便宜的茶水,我也有得赚。”
我拉了拉陆沉的衣袖,示意他附耳过来,小声开口。
我:“若是最后没人赢走这盏灯,我便将它送给你,可好?”
陆沉垂眸看着我,低低笑出来。
陆沉:“那不如让我先来试上一试?”
他愿试试,那自然是好的,我拉着陆沉走上前指着桌案正中央的由数十个细小构件咬合而成的千机锁。
我:“喏,解开了我设计的千机锁,花灯就归你了。”
话音未落,一道刺耳的声音便横插进来。
???:“哟,陆氏钱庄眼看就要歇业了,你这破落户还有心思出来玩?”
我侧目,正是方才那位刘公子,他不知何时也凑了过来。
周围人的目光顿时望了过来,四下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我心头火起,这人当真是没完没了!
我:“刘公子慎言,陆先生可是我的贵客!今日这场活动,便是由陆氏钱庄出资,安业楼筹办。歇业之说,从何而来?”
刘公子被我当众驳斥,脸上有些挂不住,冷笑一声。
刘公子:“陆氏钱庄如今是什么光景,城里谁不清楚?不过是强撑着罢了!与其靠这些花架子撑场面,倒不如想想,怎么先把储户的银子兑了。”
人群中又起了些私语,隐约有几句对陆沉不利的议论。刘公子志得意满,正欲再言,陆沉却轻轻笑了笑,先一步开口。
陆沉:“今日上元佳节,宾主尽欢,不宜争执。这样吧,陆某也为(ID)老板今日的活动添上一分彩头。
若是刘公子能解开这千机锁,贵府在陆氏钱庄抵押田产的息钱,陆某愿减上一成。”
这话一出,满场哗然。
客人甲:“还说人家要歇业呢,闹了半天,自己还不是从陆氏借钱了?”
客人乙:“利息减一成那可是好大一笔银子,刘公子,快解啊!”
刘公子的脸色顿时涨得通红,又窘又怒。
先前他便围着千机锁转了半天,根本毫无头绪,此刻叫他解,他哪里解得开?
刘公子:“你得意什么?你解得开吗?”
陆沉:“若我解得开呢?”
周围顿时响起一片起哄声,撺掇刘公子再添个彩头。
刘公子环顾四周,对上陆沉那抹似笑非笑的目光,一时血气上涌,一咬牙松了口。
刘公子:“若你解得开,抵押在你那里的田产,我们刘家不要了!”
陆沉:“既如此,那便请诸位做个见证。”
话毕,陆沉看我一眼,眼底浮上一点笑意。
他走到千机锁旁,并未像其他人一样着急上手,而是不疾不徐地绕着它走了一圈。
我有些惊讶地发现,陆沉没有过多犹豫就停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他微微弯下腰,修长的手指探入机关的内部,轻轻一拨,转动手指。
一连串清脆的“咔嗒”声响起,环环相扣的榫卯精准滑动、解扣,不过片刻,千机锁便应声而开。
转瞬,散开的构件又重组成了一座精妙小巧的安业楼模型,飞檐翘角栩栩如生。
四周顿时爆发出一片惊叹与喝彩,掌声雷动。
我难掩震惊地望向陆沉,我料想过他能够解开,但应该会费上好一番周折,没想到他竟会一眼便看穿了最核心的关窍。
我:“你怎么知道解法?”
陆沉笑了笑,并未直接回答,而是伸手指向千机锁上一处细微的反光。
陆沉:“今晚的月色很好,这一块机括恰好比旁边更亮些。我想起那晚我们一起赏的小月亮,便试了试。”
他注视着我,唇角微微扬起。
陆沉:“所幸,猜对了。”
我想起那晚我们静静地坐在桌旁等月亮,那时的月色也像今夜这么好。
心尖像是被温热的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对上陆沉望过来的目光,我也轻轻笑了笑。
陆沉:“我有(ID)老板给的提示,原本是胜之不武的。但送上门的彩头,不拿白不拿。”
那是自然。我转头看向人群中面红耳赤的刘公子,笑着揶揄。
我:“刘公子,大家可都看着呢,别忘记兑现自己的承诺。”
他用手指着我和陆沉,“你”了半天,脸涨得像猪肝色,一甩袖子,带着几个跟班灰溜溜地挤开人群走了。
我看着他狼狈的背影,说不出的解气,先前的不快一扫而空。
我转过身,朗声向众人宣布。
我:“诸位贵客,看来这盏琉璃花灯已经有了归属。恭喜陆老板拔得头筹!”
在我的带动下,满堂掌声雷动,笑声、赞叹声和羡慕的议论声交织在一起,将今夜热闹的氛围推至高潮。
四周人声鼎沸,陆沉的目光却始终落在我脸上暖黄色的灯火在他眸中摇曳。
陆沉:“多谢,也谢谢你方才的仗义执言。”
听见他的道谢,我连忙摆摆手,冲他眨了眨眼睛。
我:“我只是说出了事实而已,筹办这活动的资金,可不就是你贷给我的?要说感谢,应该是我多谢你才对!”
我踮起脚尖想要将琉璃花灯取下来,指尖却只够了到灯下的流苏穗子。
流苏穗被我拨得乱晃,又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稳稳托住,那手掌虚虚覆在了我的手背上,握住灯盏下方的支架,将花灯取了下来。
一股清苦的香气混合着淡淡的墨香从我鼻尖拂过,是陆沉身上独有的味道,清冽干净,很是好闻。
他低头看着我的眼睛,忽然笑了,我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怎么在笑?”
陆沉:“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满堂最好看的灯也并不是这一盏。”
这句话轻轻落入我耳中,周围的喧嚣笑语、鼎沸人声刹那间都化作了模糊的光影。
心跳得快极了,一阵陌生的悸动,如同初春时冰封的水面乍裂,汹涌又滚烫地涌上来。
我怔怔地望着他,一时忘了言语。
这一年来与他相处的点滴,倏忽间纷至沓来,眼前蓦地出现许多个陆沉,凝神听我说话的他,笑着同我赏月的他……
既然必须找个人定亲,为什么不能是他?
他见识广博、谋略深远,为人磊落可信,又与我志趣相投,还有……
我:“陆沉……”
他看着我,神色专注,眉眼在灯影下柔和而鲜明,好看得让人移不开眼。
陆沉:“嗯?”
还有我心底那点模糊摇曳的心绪,仿佛也被此时的灯火催生,化作一股破土而生的冲动,径直涌至唇边。
我:“你可有婚配?”
陆沉的身形几不可察地一顿,托着灯盏的手指微微收紧。静默一瞬,他才缓缓开口。
陆沉:“没有。”
我:“那你……可愿意同我定亲?”
夜色已深,光启城中的灯火与喧嚣都渐渐散去。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面红耳赤地将自己埋进被子里。
回想起方才的情景,我问出口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脸颊瞬间烧了起来。
我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还是陆沉先开了口。
陆沉:“为什么想要和我定亲呢?”
他定定地看着我,问出口的话却自然而然的像是在问我要喝什么茶水一般寻常。
被他的从容感染,我也稍稍压下了紧张,磕磕绊绊地说起自己的理由。
我先是将圣上见我之事同陆沉和盘托出,说完了麻烦事,又急急说起了好处。
我:“成亲对你也有好处的,我虽是小商户,好歹有一面御赐的匾额。光启商会多少会给我几分薄面,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他没有说话,我不敢停歇,唯恐冷场,索性将盘算尽数倒出。
我:“我们可以签订一份契书,婚约期间,双方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彼此经营,更不会有财产纠纷。
若是哪一天……你我各自有了心仪之人,解除婚约便是,于你也没有太大损失。”
我越说声音越小,越觉得底气不足,总感觉自己像是在街上拦住姑娘问愿不愿意嫁给我的登徒子。
脸颊烫得厉害,我不由得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袖边缘,心里把自己骂了千百遍,真是美色误人!实在是太唐突了!
我正想找个借口说方才是在开玩笑,一声极轻的笑突然传入耳中。
陆沉:“我愿意的。”
我忽地抬起头来,恰好撞进他含笑的眼眸。他就那样看着我,眉眼清俊,神色温柔得不像话。
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满堂的灯笼被风吹得发出轻微的声响,我突然有些庆幸,这样他应当就听不到我的心跳声了。
他倒是迅速进入了状态,和我说起要签订的契书。
宴席活动需要彼此撑场、年节应酬各自行事这些细碎的东西被我一股脑摆了出来……陆沉听得认真,没有丝毫不耐,含着笑一一应下。
我:“那要不……要不就找个地方,把契书签了?”
他摇了摇头,语气温和,却带着郑重与认真。
陆沉:“定亲是大事,不能失了礼数。”
一夜心绪难平,直到天色熹微我才迷迷糊糊睡去。然而次日一早,门外便传来了茴儿带着惊诧的轻唤。
茴儿:“小姐!小姐您醒了吗?我在做梦吗?陆老板派人送定亲信物来了!”
我瞬时思绪清醒,匆匆忙忙地起身,拉着目瞪口呆的茴儿疾步走到店铺门口。
只见陆沉的心腹周严恭敬地立在门外,身后还跟着几名捧着锦盒的仆役。
除了送来的庚帖外,锦盒里还有四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任我择取一件作为定亲信物。
他送来了四样定亲信物,该选哪一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