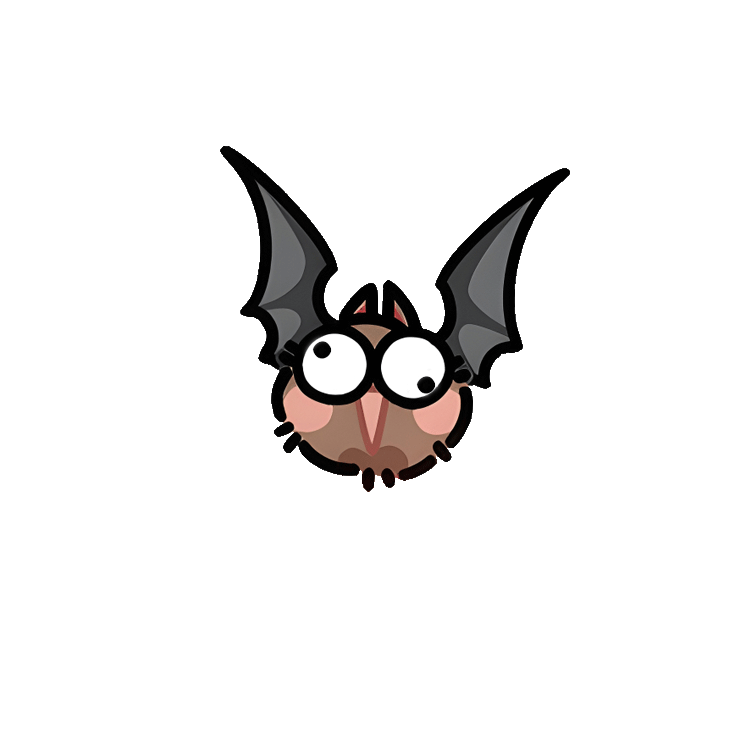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先收拾床铺❈
木板床上堆着许多杂物,烧烤架、简易炉子、防护用品以及一个大大的编织袋。
“阿嚏——”湿透的鞋袜把双脚冻得冰凉,我连打了两个大大的喷嚏。
陆沉微微蹙眉,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刚生好火的简易炉子旁坐下。
我:“陆沉,你有没有听说过关于打喷嚏的传说?打一个喷嚏代表有人在说你坏话,两个喷嚏代表有人思念你,打三个……阿嚏!”
陆沉:“在淋了雨的前提下,不管打几个喷嚏都代表着要感冒了。”
他看着我湿了一块的外套,叹了口气。“这么大的雨,果然伞也不管用了。把外套换下来吧,编织袋里有干净的防寒服。”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走到门外,把门轻轻掩上了,小木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毕剥作响的柴火。
我脱下外套,把湿衣服挂在架子上,换好防寒服后去叫陆沉进来。
陆沉搬来两张椅子,招呼我坐下。接着又往玻璃瓶内灌了些热水,仔细地用毛巾裹好,让我抱在怀里取暖。
陆沉:“暖暖手和脸。”
我抱着温热的玻璃瓶,盯着陆沉的背影出神。
我想我真的有点不了解他了。或者说,我从没真正了解过他。我对他的认知全部来自于这段时间的点滴相处。
可越接触,越好奇。我也隐隐有种感觉,一直以来的陆沉似乎都不是真正的他,那个真正的他早已只存活在某个遥远的、不可能被触及的地方。
我想要了解他,非常想。
陆沉:“木柴不够了,我去找点过来。”
我急忙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吧!”
陆沉:“光着脚去?”
……忘了自己刚刚把鞋脱下来烘烤了。
陆沉:“你好像很像帮忙做点什么?还是说,一个人在这会觉得害怕?”
我:“不是害怕。是你一直忙前忙后,我什么都不用做,心里会过意不去……”
陆沉了悟地点点头,突然抬起手,一颗一颗解开外套的扣子。
我:“你——”
陆沉:“那就麻烦你帮我把外套烤干吧。”
我:“原来是这样……”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他微微俯下身,凑近我的耳畔
我:“没什么没什么,我现在就去烤干!”
雨渐渐小了。卸下一天的疲惫,我躺进睡袋,准备迎接好梦。
我:“蛇和老鼠不会钻进来吧?”
陆沉:“我已经检查了三遍,不会有的。”
还是有些放不下心,我又扯了扯陆沉的衣袖。
陆沉:“嗯?”
我:“你不会消失吧?”
陆沉笑了笑,帮我将碎发绕到耳后,“不会,我保证。乖,快睡吧。”
尽管没有认床的习惯,但对于第一次在野外过夜的我来说,还是有些难以适应。
刚睡着就梦到了白天的蛇,我从梦中惊醒,一不小心碰倒了脚边的水壶,“哐”的声音在屋内回响。
“没吵醒陆沉吧……”我转过头,却发现炉火旁只剩下空荡荡的睡袋,身旁的人已不见踪影。
我的心一沉,起身穿好鞋袜,准备出去看看。
我:“不会有什么事吧……”
雨不知何时停了。刚打开门,远远的便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站在木屋前的大树下,微微仰头,望着垂挂于树梢的一条黄丝带发呆。
寂寂月光下,他的影子被拉的很长,看上去有些孤单,像另一棵被遗忘的树。
我裹紧衣领,顺手捎了件外套,朝那个背影走过去。
感觉到肩上落下外套的重量,陆沉转身看向我,略有些惊讶,“怎么醒了?”
我:“做了个噩梦,看到你不在,就出来找你。”
陆沉:“冷吗?”
我摇摇头,指了指身上厚实的衣裙,“你一晚上没睡吗?”
“睡了一小会儿。”他将目光转向远方,脸上没有表情。
我似乎永远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比如现在,他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呢?为什么眼底好像浮着稠稠的寂寥?
我抬起头,也望向风中那已经有些褪色的丝带。
我:“系着条丝带的人应该在期盼着谁的归来吧。妈妈离开我之后,我也在家门口的树上系过黄丝带。
书里说这象征着亲人会平安归来。我那时一直相信她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
陆沉极缓慢地眨了一下眼睛,将我被风吹开的领口拢了拢,“如果知道她不会再回来,还是会系吗?”
我:“会。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直觉,只是不肯相信。
后来系上黄丝带,我忽然有些释怀。我觉得妈妈好像从未离开,存在于身边万物。”
发顶被陆沉轻轻揉了一下。
陆沉:“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在这方面和你不太一样。”
我:“诶?”
“他认为人离去了就是既定的事实,悲痛并不能使人死而复生。
所有生命都是大自然的偶然,死亡只是生命里的一个常态。
既然都要死,怎么去死、什么时间死,就无关紧要了。
因此他没有为与亲人的死别哭泣,也很少怀念。”陆沉顿了顿,转头看向我。
“很多人都说他冷血。”他的目光里有一丝悲悯,还有许多的不解。
我用力地要摇了摇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
或许对一些人来说,生命是一场体验,不是为了得到或证明什么。
也许那个人也是经历了很多,想了很多,反而变得通达。”
月光愈发明亮,安静地照耀着我们。
我:“是这样吗?”
陆沉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们席地而坐,他把外套披到我的肩上,“这个孩子从小出生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家族,他不被父亲喜爱,母亲也过早离开。
他就像是这个世界的多余品,即是在‘家’里,也常常感到无处可去。
家族有条族规,族中小孩在长到十二岁时会被单独放逐野外半个月。
如果他能存活下来,就会被接回家族,着力栽培。
于是,少年被送到了这座山上。十几年前的天虞山远不如今日这般美好。
少年不吃不眠,在山上度过了两日。
第三日野兽出没,少年遇到一个老人,帮他大跑了袭击过来的野兽。
老人问他,怎么一个人在山里?家里住哪里,要不要送他下山?
少年都没有回答。老人递给少年半块冰凉的红薯,少年犹豫地接了,却没有吃。
那天很冷,少年体力不支,几乎失去意识。老人一直在和少年说话,试图让他保持清醒。
老人说,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能到他住的地方,那里可以看到日出。
少年终于开口问为什么要看日出?老人说,因为那是他见过的最温暖人心的画面。等少年看见了,就明白了了。”
陆沉的目光有一刹那的温柔,很快又冷却下来。说这些话时,他的脸上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同情,而是非常平静。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陆沉口中的那个少年就是他自己。
我:“幸好少年遇见了善良的老人。”
陆沉:“可那块红薯少年一口都没吃。”
我:“为什么没吃?他不相信老人吗?”
陆沉:“不,是少年厌恶那个老人。
‘如果老人不出现就好了。被野兽吃掉或者饿死,都无所谓’。
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一股莫名的情绪堵住胸口,我忍不住脱口而出,“如果我是那位老人,我也会像他一样保护少年,带走他的。”
陆沉微微停顿,不知想起了什么,唇角倏而浮现出一丝笑意,“人总是以‘为别人好’为理由,做一些单方面的付出,可大多时候,别人并不需要。
一旦拒绝,错的反而是不接受的那个人。”
“不,不是这样的。”我拼命摇头,看着陆沉毫无温度的笑容,心被牵扯得很疼。
“如果是我,甚至都不会放少年回那个没人爱他的‘家’。因为真正爱他的人,不会那样对他。更不会以爱为借口折磨他。”
陆沉:“你同情那个少年?”
我:“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难过和生气。生气那样的家庭,那样残忍的培育方式。”
陆沉:“那你又怎么能确定,少年骨子里不是和他家族的人一样?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成为他们期待的人。”
我:“我……的确不确定,但我觉得他不是。我能从故事里感受到,他没有伤害别人,他只是在伤害和压抑自己。
他不会成为残忍的人,他就是……运气不太好。”
陆沉眸光微动,眼睛有一瞬的失神。他看着我,用那种我从未见过的、充满哀伤和落寞的眼神看着我。那目光像一根根滚烫的刺,在我心里落下密密麻麻的痛觉。
我忽然……很想抱抱他。
我:“爱一个人,是没有条件的。爱不占有,不是交易,而是给人自由。
是即使不了解一个人,也愿意毫无保留的相信他。我不知道那个老人是怎么想的,但这是我全部的想法。”
陆沉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
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头倏忽燃起了一簇微小的火苗,然后呼啦一声,照亮了整个世界。
片刻的静默后,他抬起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吗?”
我对上陆沉的双眼,在他的注视下点头。
“那一天,刚到达老人的住所,山里就下起了雨,天空乌云密布,少年没有看到日出。
说来也奇怪,那个时候并不是雨季,可雨却整整下了十多天。少年没有看成过一次日出。
生存考验结束的前一天,他告诉老人,自己想在离开前看一次日出。
老人笑着说,那他要早点出门,卖掉今天打的猎物,回来就可以安心带少年看日出了。
老人出了门,少年等啊等,直到他被带离这儿,都没有等到老人。
后来少年才会知道,老人曾经因为屡次偷窃坐牢,出狱后无家可归,所以才一直定居在山里。”
故事听到这,我的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你现在还觉得老人善良吗?”他的话很轻,飘进风力让人听不清楚。
“我——”
良善的人有着肮脏的底色,本该令世人不齿的一颗心,却努力为另一颗冰冷的心描摹希望。
“我想人没办法用纯粹的善或纯粹的恶来划分。明明可以如少年所愿,让他自生自灭,可老人还是保他平安。
因此我相信也愿意相信,遇见少年的那一刻,老人是真的想保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