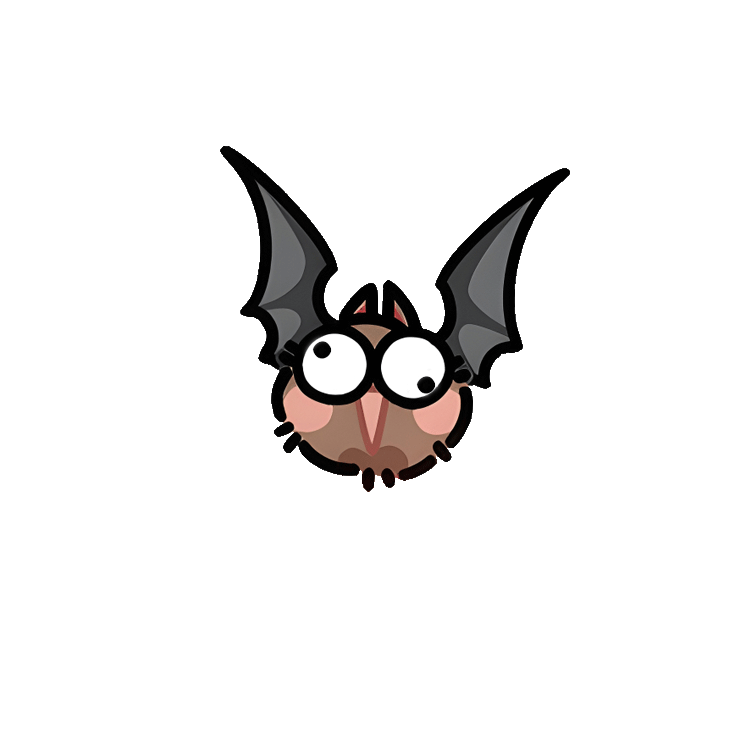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夏日油画❈
直觉一般,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幅描绘了浓郁盛夏的油画上。
就这幅画吧,看起来会是一场好梦。
我走到门前,又转身看向陆沉,他笑着点了点头,也走到我身边。
陆沉:“好,走吧。”
话音刚落,眼前门如水波一般荡漾散去。有一股力量从门内轻轻拽了我一下,我一个趔趄,跌入了另一边的世界。
扑面而来的,是照彻满目的日光与鼎沸人声。
黑石铺就的街道向远方延伸,在天光洒落的淡金色中泛出经年累月的车辙与脚步磋磨后的柔光。
街道两侧,建筑、花园、河流,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有着简洁又流畅的线条,又因为格外清晰而平衡的结构显出一些庄重的古典感。
就连点缀其中的灌木与伞松,也有着一样散漫却规整的形状。
这里也是夏日,铺洒的浓金日光、深绿的繁茂树木,天幕有着旷远的蓝色,花朵又鲜妍,一切都有着浓郁的色彩,风情各般。
我终于回过神来、转过身时,原本站在我身边的陆沉却不见了踪影。
我:“……陆沉?”
没有回应。可能是这处梦境的规则限制。
无论如何,得先和陆沉汇合。于是我顺着街道往前走,又向四周仔细观察着。
街道上的车辆、街边人们的穿着打扮都十分复古,从那休闲西装与宽大裙摆能大概看出,这是一座正处于上个世纪中期的欧洲城市。
楼宇间垂下横幅,街边墙上灯柱上贴着各色海报,旗帜在风中飘摇。
这里似乎正处于节庆期间,一切都显得悠闲、松弛而欢快。
人们或是坐在路边椅子上借着行道树投下的荫蔽看书,或是三两结伴倚在栏杆处交谈。
而交谈时落下的零星言语里,也总有一个被反复提及到的词语——
路人B:“不愧是帕拉蒂诺艺术节,也太热闹了。……说起来,你怎么了?已经这样唉声叹气一上午了。”
路人A:“唉,乔治·德里柯的画展,你去看过了么?”
路人B:“没有,是新人么?”
路人A:“是新人,也是天才!我可太喜欢他画里的空旷广场和雕像碎片了。但也因为他太天才了,所以我更感觉,在他面前,我的那些东西简直就是儿童涂鸦。说实在的,我甚至有些后悔来帕拉蒂诺参加艺术节了……”
帕拉蒂诺艺术节——这是我沿街一路走来,听到人们提及最多的一个词。
现实中的帕拉蒂诺也的确有这么一个节日,也是在夏天,持续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各行业创作者都会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艺术节。
而他们提及的乔治·德里柯,就是上个世纪中期活跃在帕拉蒂诺的画家。
看来,这场节日很可能会是梦境的关键了。我停下脚步,正纠结着要不要找人问一问节日的具体内容,就在这时,远远地驶来一辆花车。
似乎是艺术节巡游表演的花车,有许多身着华服的演员站在花车上,唱着歌剧中高昂又澎湃的选段,他们还朝四周各处抛撒着什么。
我下意识伸手捉住,是一朵纸折的玫瑰花,再展开发现,原来是一张传单。
上面用花体字写了帕拉蒂诺艺术节各种活动的安排与时间。除了画展,还有沙龙、创投比赛,从小说诗歌到剧本音乐,几乎覆盖所有领域。
而其中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沙龙后面,跟着的主办人的名字。
费德里科、阿尔贝托、贾科莫……一长串的人名读起来绕口也看得我眼花。
其中的一些我听说过,一些没有。而我听说过的那几个名字,无一不是闻名后世的导演、作家、画家。
难道在这个梦里,还有机会当面见到他们?这让我的思绪跟着有些神游。也是这时,一串风铃声落在了我耳边——
叮铃铃、叮铃铃。
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夹杂着花与可可的馥郁咖啡香气。
我心中一动,抬起头时,街边咖啡店门正被人拉开,玻璃晃动光影,我看到了其中那张熟悉的面孔——
是陆沉,他穿着一身花西装,端着一杯咖啡正坐在落地窗边。
浩荡日光穿过玻璃落在他身上,于是那斑驳的摇曳花影也随之覆上他的额发与眉眼。
它们流连在他的眼睛与皮肤,反而更显出他的洒脱、随性、落拓……
像是谁都无法握紧、忽远忽近的,却又实在令人着迷的一段诗节。
眼前的他,和平时的他实在有些不一样。我看着看着,就有些出神。
直到咖啡店门口的风铃又响一声,我才眨了眨眼。陆沉见我回过神来,歪歪头,冲我一举杯。
陆沉:“(ID),下午好。”
我也笑起来,冲他挥挥手,推门进了咖啡店,在他面前坐下。
这样坐近了再仔细看,西服的布料、剪裁都很好,可从袖口与衣摆的细节上,能看出来反复洗涤的痕迹和一些擦不掉的墨水印。
这些细节反而更增添了他身上那种文艺气质。再配上这张脸……不错不错,以后就应该多试试各种颜色和风格的衣服嘛。
我沉浸在自己的畅想里,而陆沉看我往他面前一坐却半天没说话,有些莫名起来。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又看看我。
陆沉:“这么看着我,是这身衣服有些奇怪吗?”
我:“哎?不奇怪不奇怪。就是看起来有些……嗯……风流倜傥的。”
我迟疑着说出口,又觉得这个词还是没用对,但咂摸想半天,也没想出个更合适的。
我:“哎呀总之,和平时的“陆董三件套”很不一样。简直就是文艺电影里的艺术家。陆沉挑了挑眉,很是有兴趣的样子。”
陆沉:“艺术家吗?”
我:“嗯!而且必须是那种,因为家族底蕴丰厚……所以从小接触艺术,对各种名家作品都如数家珍。
而长大后,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叛逆地离开家族。所以虽然被迫落魄,但依旧保有贵族习惯的艺术家。”
越想象就越觉得这样的身份也很是符合现在的陆沉。我有些兴奋起来,而陆沉看着我,撑着头,眼角眉梢都带上一点笑。
陆沉:“都是艺术家了,怎么还是躲不开有家族的背景。”
我:“毕竟你的个人气场实在太强啦,再怎么落魄,也很难觉得你会真是个穷光蛋。”
陆沉:“这样啊……”
陆沉拖长了语调,而眼里笑意更深。
陆沉:“但在这里,我的确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小编剧。就像现在,我只点了一杯咖啡,却已经在这坐了一下午。
因为点完咖啡、坐下后我才发现,我的口袋里干净到甚至掏不出一杯咖啡的钱。”
我:“诶?”
好吧,想象归想象,出现在眼前,我还是很难把穷困潦倒这个词和陆沉联系在一起。而陆沉却好像已经全然接受了似的点了点头。
陆沉:“所以,我只能一直坐在这,等你来救我。”
他看着我,轻轻笑了一声,而眉眼里也带上了那无辜又期待的神情。这让我愣了愣。
回过神来时,我已经掏出口袋里的钞票,挥手喊来侍者多点了些吃的,又一同随手结了账。
怎么感觉,我好像成了那些文艺电影里,因为爱上落拓艺术家而甘愿付出一切金钱与爱的角色。
但好像……还挺爽。毕竟平时偶尔几次,我也想象过陆沉“破产”后,被我“金屋藏娇”的情节。
我心情颇好地喝了一口咖啡,又忽然想到一点疑问,抬起头看向陆沉。
我:“不过说起来,你怎么知道现在你是一名编剧?看你的装束,也有可能是画家、雕塑家,甚至设计师之类的。”
陆沉笑了一笑,伸手轻轻擦去了我鼻尖沾上的泡沫。
陆沉:“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梦。那时候我刚写完Jude的故事,休息的间隙又看了很多和帕拉蒂诺有关的电影。漫长的夏日、无所事事的午后,一切好像都会在这里停留。
于是有一天,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梦见了夏日的帕拉蒂诺,而我是旅居此地的编剧。会到处游览采风,也会在街角的咖啡馆一坐就是一下午。
每天思考的,只是笔下的故事要怎么继续。在梦里,故事好像永远都写不完,夏日也因此永远不会结束。”
随着他的讲述,我开始想象起那时做了这样一个梦的陆沉来。
他想要与自己对话,于是在梦里,他写了更多故事;他期待某种永恒,于是在梦里,故事无法写完、夏日不能结束。
而在这种他所希望的永恒中,似乎还有着一点微妙的、潜藏其中的困顿。
我看向眼前的陆沉,在刚刚落下的安静里,他已经微微偏开了目光,望向了窗外似乎也并无尽头的长街,神色渺远。
所以至少现在,并不是个继续往下仔细讨论些什么的好时候。
于是我坐直了身体,清清嗓子,看着陆沉,认真开口。
我:“我觉得,这是很好、很美的一个梦。”
陆沉回过神,他与我对视。深红的瞳孔微微张开,里面在花影之外,又多了我的影子。
良久,我们一同笑了出来。
离开咖啡店,走到街上时,已经是傍晚。
太阳向西方沉落,从建筑之间落下的日光也投下一些被截断的影子。
老城的街道,建筑与树木本来已斑驳,而在此刻的夜色与暮色之间,一切反而模糊成百年来都始终如一的影子。
帕拉蒂诺似乎变成了一处水潭,流经的时间都藏进了影子的缝隙,于是一切都能不变、都能永恒。
怪不得,帕拉蒂诺又被称为永恒之城。就这样,我和陆沉并肩穿梭其中。
我环顾四周,不由得有些感慨,原来这就是以前的陆沉会做的梦;脚步不由得跟着慢下来,甚至有了迟些离开的想法。
离开——这时我才突然想起,刚刚好像没问陆沉,在这个梦里,要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毕竟要从梦里离开,实现梦境的愿望是唯一的办法。
我:“对了,陆沉,我们要想从梦境出去,得实现你的什么愿望呀?”
陆沉看向我,他顿了一顿,才摇摇头。
陆沉:“……没有。在这个梦里,我没有一个非常迫切而明确要实现的目标。”
我:“那这样,不是就出不去了……”
这么说到一半,我愣住了。
我忽然明白了,刚刚听陆沉讲述这场梦时,我感觉到的那点微妙的、潜藏其中的困顿感是从何而来——
永远写不完的故事、因此漫长而永不结束的夏日。
它们像是头尾相衔的圆,不存在某个终止的节点,就好像……
就好像,是要困住什么。
而转念一想,就在刚刚,连我都有了迟些离开的念头,那对那时候的陆沉来说……
看着眼前的陆沉,不再犹豫,我直接说出了我的猜测。
我:“难道,出不去,就是这个梦的目的?”
夜风吹过长街,摇落一地树影,也吹起陆沉的额发,露出底下那双全然坦诚的眼睛。
他就用这样的眼睛看着我,半晌,笑了起来。
陆沉:“嗯,那时的我是这么想的。我从梦里醒来之后,觉得这个梦实在很好,连我都有些流连忘返。于是,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可以困住以后的我的、又一层保障。”
陆沉没有继续再说,而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用令人沉迷、让人流连忘返的美梦困死自己。也许是一点恻隐之心,但更是在机器人可能的失败与故障外,他也能走到注定结局的保障。
是从前的陆沉会做出的选择。
只不过现在……
我:“结果没想到,现在,是困住了我们。”
陆沉:“嗯,完全没想到。”
陆沉露出一个带着歉意的笑,又伸手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
而我又重新盘算起这个梦的逻辑来。
我:“要出去,就得实现愿望;可就目前看来,那时你的愿望又是永远待在梦里。这简直死循环,完全无解呀。”
陆沉看着我,眼神里又流露出那种无辜神情。
我:“算啦,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地方也挺好的,我们也不急,先到处逛逛吧?”
陆沉:“那现在,想做什么?”
我:“现在啊……我想回你在这里的家看看!”
陆沉:“我家?”
我:“嗯!我好奇了一路了,穷困潦倒的编剧陆沉的家,会是怎么样的。”
陆沉笑着点了点头,伸手牵过我。
陆沉:“好,出发。”
拐过转角的古董书店,穿过路灯昏黄模糊的小巷与花园,走过上古时神庙遗址旁的一条绿篱小径,又转过再一处花店的街角……
陆沉对这里很熟悉,牵着我在帕拉蒂诺复杂的大道小路中穿梭。
天色渐渐暗下去,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陆沉在这梦里的帕拉蒂诺的家。
是临河的一处公寓,斑驳的墙面、繁复的雕花,看起来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电梯是手动打开木门的类型,但已经坏了,我们只好爬楼梯。
楼梯就更是帕拉蒂诺老城住宅一贯的狭窄和危险,踩上去时会发出嘎吱声响,像是随时都可能倒塌。
终于抵达顶层的阁楼,推开门、按亮灯,出现在眼前的,是一间并不大的公寓房间。
完全不同于刻板印象里,落魄编剧总是不见天日、各种文稿墨水酒瓶杂乱堆叠的样子,眼前的房间十分简洁干净。
房间里最多的是书和笔记本,除了床和书桌外,几乎挤占了绝大部分的空间,但都被仔细地分类摆好,也沿着墙面摞得整整齐齐。
房间的一侧还放了一个巨大的黑板,看上面的内容,是用来记录平时分析故事起承转合、人物变化弧光时的思路。
除了写作相关的东西,房间里还有一台唱片机、机器旁散落着零星几张唱片,床头放着烧到一半的香薰蜡烛和一只兔子玩偶。
而平常写作的书桌,则占据了这间房里最好的视野——正对着窗外帕拉蒂诺波光粼粼的河景。
在帕拉蒂诺,随时随地都会有故事发生;而站在这里,那些藏在街头巷尾、藏在光影与缝隙中的时间,也都会被一一看到。
这么一圈走下来,再回到门口,我看着陆沉,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我:“这地方还真是不错。感觉,以后我要是辞去工作准备自由职业了。也可以找这么一个小小的、能在热闹和寂静之间进退自得的地方躲起来画图。”
听见我的评价,陆沉笑了起来。
陆沉:“那现在,你离你的构想,就差辞去工作、准备自由职业了。”
我:“嗯?”
我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
我:“在现实里,你不会真拥有这么一间阁楼吧?”
陆沉:“嗯。我醒来的第二天,就跑到帕拉蒂诺,找到了它,把它买了下来。”
我:“……我应该已经适应了的,你这令人嫉妒的超能力。”
看着我摇头叹息的神情,陆沉没忍住笑出了声,又走上前来,捏捏我的鼻子。
接下来,我和陆沉便一起坐在地毯上,翻起了那些书籍与笔记本。
从物理到诗歌,从哲学到农耕与航海,还有不少讲述编剧技巧的工具书。
书类很杂,看来就算是梦里,陆沉也还是什么都看。
而那些笔记本里,有一些是观察分析的笔记,里面记录着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
还有一些,是那时陆沉的手稿,也是不论后来还是梦里的他,都没能写完的故事。
鬼使神差地,我想到了帕拉蒂诺艺术节里的诸多活动,似乎有剧本比赛。
陆沉,梦中作为编剧的你,会不会想参加剧本比赛呀?
我:“把自己的剧本拍出来,感觉是所有编剧都希望看到的。也许……这会是这个梦里隐藏的愿望,也说不定?”
陆沉思考片刻,点了点头。
陆沉:“有可能。”
我:“那现在这里有这么多没写完的故事……挑一个,我们一起把它写完,拿去参加比赛,怎么样?”
陆沉看着我,笑起来,又点了点头。
陆沉:“好。”
于是我们挑选起来。童话、寓言、爱情、战争。各种题材内容都有;有的写了几幕,而有的只是纸上一个犹疑的灵感与想法。
翻到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在陆沉的允许下,我轻声读起来。
我:“一名自认为没有感情、因此从未失败的杀手在这天,忽然发现自己无法再杀人了。这天,和往常一样,杀手找上了他这次的任务目标。
也和往常一样,他架起了狙击枪,瞄准了目标,准备扣下扳机。就在这时,他的手顿了一顿——因为他看到,他的目标买了块蛋糕。涂着蓝莓酱的奶油蛋糕。
而目标并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挖着蛋糕就吃。他用勺子仔细收集起蛋糕上的蓝莓酱,再将蓝莓酱一次性送入嘴里。美味地品尝完蓝莓酱后,他才开始享受剩下的奶油蛋糕。
这时,杀手的嘴里也泛起了蓝莓酱的味道。因为他平时吃蛋糕时,也喜欢和目标这样,先吃完蓝莓酱,再享受奶油蛋糕。
他因此放下了手里的狙击枪。那一瞬间他发现,原来杀人是这么难——他忘不掉蓝莓酱的味道。”
我咂摸一下,感觉读完这个故事好像也尝到了蓝莓酱的味道。
我看向陆沉,用眼神问他这个故事怎么样。
陆沉思考了一会儿,摇了摇头,露出一个抱歉的笑。
之后我又翻出了几个没写完的故事,但陆沉也都还是没有什么兴趣。
陆沉的手指顿了一顿,又在书页上摩挲几下,接着,他轻声念起了那个故事的内容。
陆沉:“濒死的凡人得到了一次与天神对弈的机会。天神承诺,只要凡人能赢过自己,他就能活下来。在万物的见证下,誓约生效。
于是在天神和凡人面前,出现了一张满是黑子的棋盘。黑子是天神的黑子,而每一颗,都是天神对凡人提出的问题。
凡人每回答出一个问题,就能用自己的白子吃掉天神的一颗黑子。只有白子完全占领棋盘时,凡人才能活下来。”
剧本的前几幕,就是凡人与天神之间的问答。
一开始,问题都很具体。比如三岁那年生日蛋糕的夹心、宠物眼睛的颜色、挚友的名字、三年级时没能成功的恶作剧。
这些问题,凡人都一一回答了上来。
但接下来的问题,变得令人茫然起来。它们像是来自哲学课本,比如爱、痛苦、命运——以及在所有这些问题终点的,所谓“意义”。
天神问凡人,意义是什么?
世界、你、快乐与悲伤、离别和相遇……所有的这一切,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没有意义,那又何必与世界相处,又为什么、还要挣扎着活下去?
凡人答不上来。这些问题,凡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在思考、在困惑、在为眼前这无意义的一切而挣扎痛苦。
他甚至一度以为,死亡就是所有无意义的一切,最终的答案和归宿。
如今他就要死了,却发现死亡同无意义不过一丘之貉,于是他仍旧回答不上来。
陆沉:“……就这样,几天过去,棋盘上白子与黑子的数量仍相去甚远。凡人感到无法控制的颓败——在他活着的时候,虚无的意义曾那样折磨着他。而现在,那同样带来虚无的死亡,也要将他吞没了。”
故事就到这里为止,那时的陆沉没有继续写下去。
我思索着那些问题,好半天,还是摇了摇头。
我:“这天神设下的,简直是死局嘛。所以陆沉,你写的时候,是希望凡人活下来,还是不希望?”
我看着陆沉,他也看着我。而片刻后,他又稍稍偏移了目光,手指也微微松力,那书页便纷纷落了下来。
在书页落下的簌簌声里,我想起关于这个问题,陆沉已经在不久前,承认过自己真正的答案——
陆沉:“活下来。我希望他活下来。”
陆沉重新看向我。这时的眼睛,便与那时的眼睛重叠了。
公寓的昏黄灯光在头顶闪烁起来,明明灭灭,落在我们身上、落在那些书页里。
二十四岁的陆沉,也在这些书页里。
陆沉:“但很可惜,那时的我发现不管怎么写,凡人都不可能完全吃掉黑子、赢下这场对弈。
所以,我没能写完这个故事。因为有很多问题,即便到了现在,我也还是没能找到答案。”
我:“所以,你想借这个机会,再去试试能不能回答上来吗?”
陆沉:“嗯。不过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至少,我想试着给他一个结局,或者一种别的可能的开始。”
就像现在的陆沉一样。
他没有继续说,而我依旧能明白他的意思。
于是我看着陆沉,认真地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好!那这回,不论怎样的后来……我们都一起把这个故事写完。”
陆沉看着我,也跟着我一起点了点头,目光里满是期待和动容。
不过……
虽然嘴上满是信心充满干劲,但仔细思考起来,确实头痛。
我:“好难的问题,爱、痛苦、命运、意义……无论哪一个挑出来,都可以称得上是人生的终极命题了吧?
要不我们去古希腊,去问问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也许他们就有答案……哎,对啊!虽然没有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也许,我们可以找他们问问?”
我一个激灵坐起身,从口袋里翻出了那张皱皱巴巴的、写了许多后来的艺术巨匠名字的传单。
陆沉接过传单,仔细看了一会儿,手指停在其中一个名字上。
我:“……努埃莱·塞维里诺?”
陆沉:“嗯,我记得他是帕拉蒂诺闻名后世的哲学家。”
我眼前一亮。
我:“那说不定,他对故事里的那些问题,会有回答?”
陆沉:“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试试,去那里找找答案。”
我:“好!”
而传单上标注的塞维里诺沙龙时间,正好是今晚。
简单修整一番后,我和陆沉从公寓出来,又走上了石砖铺就的长街。
已经入夜,帕拉蒂诺遍目灯火,音乐、酒与光线在空气中浮动,城市跌入狂欢的梦。
沙龙举办地就在离公寓不远的酒吧,不需要门票也不需要请柬,只要是感兴趣的,都可以进去一同交流。
因此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聚集在了酒吧。
可惜的是,塞维里诺本人因为身体原因提早退场了;但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场沙龙的代主持人,正是画家乔治·德里柯。
德里柯带来了自己的许多画作,供沙龙的参与者欣赏和讨论。
我和陆沉站在其中一幅面前,甚至都没有隔一层防弹玻璃,它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每一处笔触细节都清晰可见。
我蹲在画作前,仔仔细细看了很久,才终于满足地站起身。
我:“这幅画,上过拍卖行吧?”
陆沉:“嗯,最近一次出现,应该是在去年。我记得拍出了四千万的价格。”
我:“四千万……”
我不由得转身,看向酒吧里这幅画的作者。
现在,在我们眼前的乔治·德里柯还是一位刚有了一点名气的年轻人。
他正与旁人讨论他画里那些无生命的物体、梦魇一般的投影光线和诡异的透视。而说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会跟着亮起来。
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之外,德里柯还向大家展示了他的草稿与构思图。
对着画纸上那堆看似杂乱无章的线条看了半天,我才似懂非懂地摇了摇头。
我:“嗯……”
大师的草稿,果然也很非同一般。陆沉站在我身旁,只看着我笑。
陆沉:“在我眼里,你的草稿也总是画出这样非同一般的线条。”
我:“哇,那四舍五入我也是大师了。等等,你什么时候偷看的我的线条草稿!”
还有更多流传后世的名作,在此时此刻,只是德里柯与他人交谈时不经意提起的一个想法。
我拉着陆沉,拿了一杯香槟,走到附近,装作不经意地偷听起德里柯与别人的对话。
石膏像、手套、儿童玩具……这些日常生活的事物,在他眼里被赋予了与日常生活完全相反的寓意。
世界就像是一场梦,一场神秘、宁静却又隐含着不祥隐喻的梦。
而除了德里柯之外,沙龙现场的很多参与者,都是后来十分有名的艺术家。
还没有拍出街区浮华的费德里科,刚结束隐居来到帕拉蒂诺的艾尔莎,尚未签署绘画宣言的贾科莫,还没有写出代表作的德西卡……
此时此刻,在这场虚构的梦里,时空得以交错,尚未成名的他们也得以被聚集在一起。
他们谈论艺术、人生、命运,也谈论帕拉蒂诺的甜酒、烩饭与火腿。
他们彼此鼓励,也彼此针锋相对地争吵。而灵感似乎就在这些充满激昂情绪的词句中碰撞而出。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多少有些向往。但一想到眼前这些人都是后来的大家,还是有些畏怯瑟缩。
这时,一只香槟杯轻轻碰了碰我的,落下一点清脆声响。
是陆沉,他微微低头看着我。
陆沉:“想去和他们说说话吗?”
我:“我……”
陆沉:“不用害怕,毕竟这只是一场梦。不是吗?”
陆沉冲我鼓励地笑,又握住我的手,慢慢揉捏着,带来熨帖温度,也揉散了我的畏怯和瑟缩。
是啊,这只是一场梦,更何况陆沉就在我身边。我顿时感觉充满了勇气,抿了一口手里的香槟,我拉着陆沉走上前去。
这些领军时代的先锋艺术家们意外地都很友好,在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很快,我也参与进了这场对话。
从绘画、文学、电影本身,再到它们背后无法挣脱的时代与隐喻,又或者,影响到艺术表达的,其实只是蔚蓝海岸旁的柑橘园与沙滩。
我们的对话天马行空,跟随心的流向肆意铺展;偶尔也会沉默,而在安静之后,又总是有更有趣、更吸引人的想法出现。
这场沙龙持续到了深夜,离开时,我还有些依依不舍。
深夜的帕拉蒂诺街头,昼时夏日与狂欢的梦褪去,眼前永恒之城才终于显出那柔软又坚定的亘古不变的沉默。
人群散去,我走在石头路面上,脚步因为刚刚的谈天说地而兴奋得有些一蹦一跳。
而陆沉则一步一步跟在我身边,我只要回过头,都能看见他笑着注视我。
陆沉:“看起来,今晚你很开心。”
我:“当然啦!和那——么多厉害的人聊天。费德里科、艾尔莎、贾科莫、德西卡……虽然是梦,也值得来这一趟了。就是有点可惜,没能见到塞维里诺。想到这里,我的脚步顿了一顿。”
而陆沉只是走上前,与我并肩,也顺势牵住我的手。
陆沉:“没关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梦境里多停留一会。”
我:“哇,我当然非常愿意!那故事的续写……”
陆沉伸出手,安抚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陆沉:“就像你曾经说的那样,灵感总是难以捉摸。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就这样,我和陆沉暂时留在了梦中的帕拉蒂诺,开始了一段看上去有些无所事事、甚至是游手好闲的夏季假日。
陆沉买了一份地图、租了一辆汽车,于是我们能去更远更多的地方,游览采风。
在许愿池边,我们没有许愿,而是辨认着池底形形色色的硬币,想象着抛下它们的来者在遥远异国会留下怎样的愿望。
在无人的旧日宫殿里,我们奔跑,只为了打破一部电影的记录,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几乎惊醒其中沉睡的故日,我们便又在他们苏醒前离去。
而在斗兽场遗址前,我和陆沉又只是静静站着,等待一阵风。风吹过,带回千百年前野兽的战栗与怒吼,日光照彻下,岁月便在此刻重现。
还有更远的地方,一座高山、一汪湖泊、一片沉默的森林或是一条歌唱的溪流,我们也都一一走遍。
而每去一个地方,我们都会搜罗一些纪念品放进公寓。公寓里不再只有书籍与手稿,渐渐也变得如窗外夏日的帕拉蒂诺一样缤纷。
不过,也不算是彻底的无所事事。
因为就算是在梦里,到处游玩也需要花钱。为了维持生计,陆沉开始给杂志社写稿。
而写稿的第一个下午,陆沉坐在书桌前,阳光爬上桌面又消失,我打了个盹醒来,看到他一手撑头一手转笔,盯着面前的稿纸,无从下手
听到我喊他的名字,他才回过神,转头来看我,眼睛里流露出一点难得的委屈和无措。
陆沉:“(ID),这回,我好像切切实实体会到你无论如何都画不出稿子的憋闷了。”
我反应过来,没忍住,笑出了声。
于是为了我们唯一的收入,我担任起了陆沉编辑的角色。
帕拉蒂诺图书馆,也成了我和陆沉最常流连的地方。
高大书架将光影切割成起伏的明暗线条,尘埃颗粒在其中跳动,图书馆似乎被光与尘的潮水浸润,而我们在同样浩如烟海的书页中辗转。
还有咖啡馆里、草地树荫下、湖上泛舟时……还有许多安静的、能让我们好好思考与讨论的地方,我们经常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讨论要交给杂志社的稿件,也讨论那个没写完的故事里、没能被回答的问题。
不过讨论着讨论着,我和陆沉又好像总是会在午后满溢的日光里迷迷糊糊地依偎着睡去。
有时,路过的冰淇淋车、花车也要比文稿卷宗吸引人。我便会推推陆沉,他也欣然起身下楼,再推开门时,怀里总是抱着更多礼物。
我们还花费很多时间做了许多和写作毫无关系的事情——演奏竖琴、长笛;学习帕拉蒂诺古语言;研究记录在一本不知名书册里的所谓炼金术。
在公寓街道的第一个拐角,我们甚至和一只鸽子混熟了——每次傍晚散步,我们都会带上点吃的喂它,它渐渐习惯,每天准时等待。
在这里,时间对我们来说成了最可以浪费的东西,我们肆无忌惮地挥霍,也不求换回什么。
而就算我们这样挥霍,夏日——这里的夏日也永不结束。
似乎,我们真成了电影里,虚度时日的艺术家。
当然,艺术家必须经历一次的情节就是——
面对着空荡荡的钱袋,我的肚子咕噜一声,和陆沉面面相觑。
我:“赚稿费的速度,好像完全赶不上花的速度啊……”
话音刚落,陆沉的肚子似乎也响了一声。
陆沉藏在棕发里的耳尖一下红了起来,他有些不好意思,又同时因为眼前从未预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滑稽情形而忍不住憋笑。
就这样,我们彼此笑着看了对方好半天,直到陆沉轻轻咳了一声,指了指桌上的方糖。
陆沉:“我记得,家里应该还有些材料,也许够我们做一个蛋糕。”
我:“哎,在哪?”
眼睛一亮,我坐起身,和陆沉在家里一番搜寻。
方糖、面粉、鸡蛋、牛奶、果酱……有是有,当然也能做蛋糕,但做出来小小的,我和陆沉分着吃了,勉强缓解了饥饿感。
陆沉坐回书桌前,而我也躺回了摇椅上,风吹起白纱的窗帘,晃动一室的光影,房间像是寂静的水底。
我不由得闭上眼,脑海里忽然浮起一句不知从哪本书册的角落寻来的一句话——
夏天除了用来浪费,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用途。而此时此刻,我深以为然。
我:“陆沉,你说夏天,是不是都是这样,只用来浪费?”
陆沉没有马上回答,我也依旧闭着眼,分辨起他的声响。我听到他的呼吸声,听到钢笔被搁
置在书桌上,木椅与地板摩擦出细微声响……下一秒他握住我的手,身上气息将我环绕。
陆沉:“对我来说……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才算不上浪费。”
我睁开眼时,陆沉正低头看着我。
他在我发顶落下一个吻,接着是额头、眉眼、耳垂、鼻尖。
最后,那一点蛋糕的香气便在交缠中落在了我和陆沉湿漉漉的唇边。
唇齿厮磨间,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不是就是艺术家还必须经历的另一个情节——有情饮水饱。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陆沉便轻轻咬了咬我的舌尖,示意我专心这个吻。
当然,我们也继续参加着沙龙、展览、观影等等一系列能和名师大家交流的活动。
我们也确实成功结识了更多后来的艺术巨匠、同他们交好,彼此间可以聊的话题也终于到了更深入的哲学思考。
而我也逐渐发现,即便是这些日后扬名的大师,此时此刻,他们也有着相似的迷茫和痛苦。
比如问及意义时,他们总是一开始兴高采烈,可说到最后,只剩下犹疑的沉默。
是的,他们也无法回答出那些问题。他们也对更早以前的作品、时代和人有着“他们才能回答出这些问题”的幻想。
甚至有一天,我和陆沉去酒廊游览采风,无意中撞上了一位之后名垂青史的诗人——他喝得烂醉,满嘴空想,似乎整个世界都与他作对。
好吧,文艺点来说,那叫醉生梦死。但我不敢苟同,这样的他也多少让我有些幻灭。
于是渐渐地,我和陆沉很少再去参加那些活动、见那些人。
我们更专注于剧本里的那些问题,想要回答上来、想要继续写结局。
但这种专注和讨论,无论多么慷慨激昂,兜兜转转最终也还是回到失去答案的起点。灵感走失了枯竭了,不肯光顾,不愿续写。
夏日,永不结束的夏日,似乎的确同二十四岁的陆沉想象的那样,变成了一个头尾相衔的圈,将我们困在其中。
又一次讨论无果,我叹了一口气,在草地上翻了个身。
思考着要不要睡个午觉忘掉烦恼时,我感觉到陆沉靠近了我身边。
陆沉:“(ID),怎么了?从刚刚开始,你的眼睛就闷闷不乐的。是在苦恼,无法回答出剧本的那些问题吗?”
我抬起头,他正垂眼看我,又挡去了在树荫间都遗落的刺眼日光,脸上眼里的神色也因此被渲染成恍惚又隐约的温柔。
我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
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是毫无进展。虽然知道创作就是如此,但难免有些泄气……”
陆沉耐心听着,神色温和,见我讲完,便抬手轻轻按摩起我的脑袋。
夏日午后的世界总是格外宁静,我也逐渐放松下来。
这时,陆沉的声音便又响起落在了耳畔。
陆沉:“其实,我还在想另一个问题。”
我:“什么问题?”
陆沉:“就是这段时间——在梦里的这段时间——你回忆起它,会想到什么?”
我:“嗯……”
我闭上眼,开始回想起这一段的自由夏日,许多画面出现在我眼前。
我:“冰淇淋、花、街角的鸽子,还有在许多地方,和你为了一个小情节反复讨论修改。”
陆沉:“那这些,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
我:“当然有意义啦。”
陆沉:“可它们,明明都只是一场梦。对我们的现实来说,一周半月的时间不过瞬间,从梦里醒来,这一切就都会消失。
我们喂的鸽子、四处搜罗的纪念品、写下的诸多文稿……我们将再也无法感知它们。就像这个世界一样,既然终会消失,那意义也就成了谬论。”
我:“不,你说得不对。”
我下意识反驳,可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而陆沉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点笑,神色坚定又温和。我反应过来——他在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思考出了他可以接受的答案。
我:“所以,陆沉,你有答案了吗?”
陆沉:“嗯。”
我:“那这个世界、这一切,究竟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
陆沉:“有意义。”
我:“可它们总会消失。”
陆沉:“所以在它们消失之后,我会从你的眼睛、我的心里,重新看到它们。”
我愣了愣,而陆沉脸上笑意更深。
他注视着我,目光又似乎跨过了漫长的夏日时间,站在了世界与自己的尽头。
陆沉:“喂鸽子时的快乐、买下纪念品时的惊喜、完成文稿时的畅快——这些事物和它们的意义,都是我们一件件创造的。
是我们选择了去做这些事、去让它们发生,它们才得以拥有意义。因此,它们属于我们,不属于世界。”
顿了顿,陆沉脸上的笑又带出一点叹息的意味。
陆沉:“当然,我们也都会消失。但也只有在我们消失之后,意义才不能被称之为意义。”
万物静默,在陆沉的话音里。
四下世界似乎都静止着屏息凝神,等待如今的他给出从前他不曾写下的答卷。
于是我看着他的眼睛,问出了此时此刻最关心的问题。
我:“那,你也已经想好了故事里凡人的结局吗?”
望向眼前似乎永远湛蓝、永无尽头的长空,陆沉点了点头。
也是这时,一阵风吹来,吹散手边文稿,纷乱中,眼前的梦境也开始化为无数纷飞的书页。
声响簌簌,眼前书页犹如在风暴中翻飞的蝴蝶,而陆沉的声音便在其中又响起。
如今的他,终于可以回答出二十四岁时的自己提出的问题。
陆沉:“结局就是,凡人输了。他必须迎接自己的死亡。他必须去承认、去看到,死亡的确会将一切消弭。
但他不会再因此感到痛苦了。因为他已经明白,那些所谓意义,他已经自己一件一件创造过、赋予过。”
眼前的漫长夏日、浓郁世界,就在陆沉最后的一点话音里,散尽了。
陆沉握住了我的手,我们十指相扣,又不约而同地闭上了眼。
恍惚间,我们好像和故事里的凡人一样,也经历了某一次死亡的消弭。
但没关系,我们的心已经安静——
不必再向他人或世界追问意义,因为世界荒谬无序,它们本不存在。
要向自己追问、让自己选择、让自己创造。
虚无的阴影也许永不消退,但我们是能够永远紧握现在、将一切去记录、去复述,从而比肩永恒的白子。
再睁开眼时,我和陆沉已经回到了花园。
曲折的绿篱、折射碎光的喷泉,还有远处的庄园、草地与山谷。
这里是长夏,一切如常。
再下一眼,我看向身侧的陆沉,他也正望向我,我们相拥。
听着陆沉的心跳与呼吸声,我缓了好一会,终于平静下来,才稍稍离开一点这个拥抱,与陆沉面对面,看向彼此的眼睛。
我:“……所以,那个梦,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死局?看起来好像没有愿望,就无法出去。
就算找到了可能是愿望的剧本,也会因为想不通、无法续写那个故事依旧出不去。但其实,这也仍是留了一线生机。”
陆沉看着我,又靠近,将他的额头紧紧与我相贴。
又有风吹过,但风中不再有蝴蝶或书页,它只是一阵风,吹过长夏的山谷,也吹过从前和现在。
陆沉:“嗯,也许就像我写下那个故事时一样……活下来。他希望我活下来。”
他的声音很轻,混着一点叹息与怀念。这是一个藏在他过往生命每一处缝隙里的答案,如今他翻出了其中之一,往后,也许还会有更多。
是从前的陆沉,送给现在的陆沉的礼物——尽管有时候,可能是以相反的面目出现。但每一份,都能将我们带去更远的未来。
陆沉注视着我,又贴得更近,嘴唇蹭过我的耳廓。
陆沉:“幸好这回,你还是在我身边。”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又不想此时此刻变得这样沉重。
于是我故意哼哼一声,上去咬了咬他的嘴角。
我:“当然啦!而且没有我在旁边给你当编辑,你可就要给不出稿子、在梦里饿死啦!”
陆沉笑着点头,很是赞同,又皱巴着表情低头蹭了蹭我的鼻子。
再开口时,声音神情也和他的动作一样,黏黏糊糊起来。
陆沉:“嗯。这么看来,当一名编剧,好像也没有想象里的那么有意思。还是继续当董事长吧,这方面我比较擅长。”
我:“哇,陆沉,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但这话你说出来……怎么还是有点欠揍。而且不行,你得继续当编剧——Sonder还有好多故事呢。其它的你可以坑,这一系列的故事你可得继续写下去。”
我张牙舞爪一通威胁,而陆沉看着我好半天,没回答,忽然就这么直接亲了上来。
我愣了愣,完全没反应过来,而呼吸与身体都已经下意识跟随起陆沉的节奏。
这样交缠含混间,我又听到陆沉带笑的声音。
陆沉:“好,知道了。不过,Sonder的故事,是属于我们的。我得和你一起,才能继续写下去。所以,故事不会结束。”
只要我们还在呼吸、还在思索、还在疑惑与追问、还在感受到爱感受到痛苦,那故事就会一直生长。
夏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