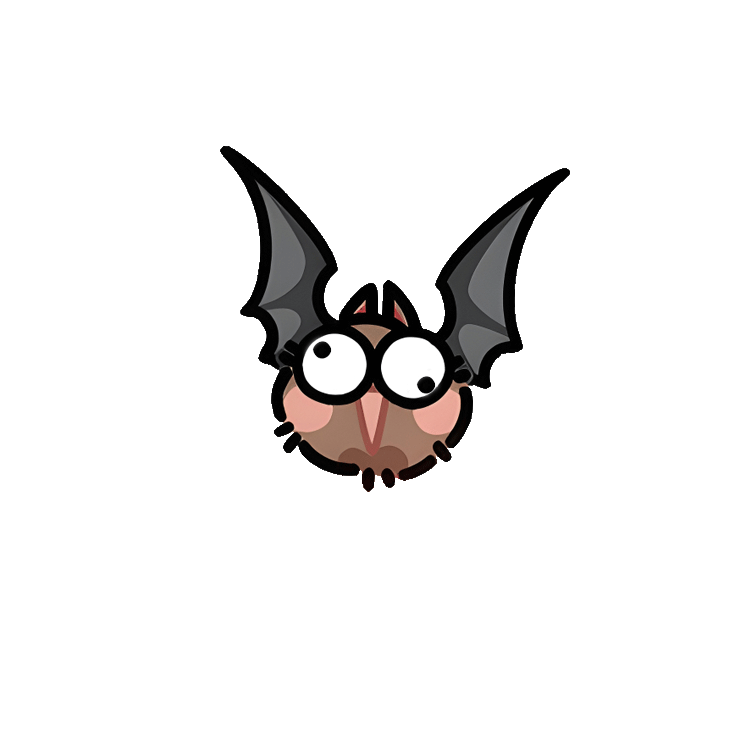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前置剧情❈
金色的朝阳自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希尔国的都城——沉睡的涅斐图也从睡梦中醒来。
王宫两侧金合欢树的阴影打在平整光滑的地面上,空气中飘来金盏花的香气。
大殿里,数十根雕刻着太阳神的巨柱自主殿门口依次向王座延伸,希尔国的高官和贵族齐聚一堂,例行宫廷议事会。
金色的帝王长袍在地上迤逦而过,雕刻着太阳神图腾的黄金项链沉甸甸地压在胸口,尖锐的棱角时不时刮擦过皮肤,但我已然习惯。
踏上高台,我抚平薄纱手套的褶皱,缓缓落座于镶嵌着宝石的黄金王座。
王座高台下,众大臣向我深深俯首行礼。
众大臣:“女王陛下安康,愿太阳神的光辉永远照耀您。”
我摆了摆手,示意今天的议事会可以开始了。
我:“各位,今天有什么要事呈述?”
话音刚落,一大臣迈步而出。我抬眼望去,是传信官。
传信官:“陛下,边境总督今早发来了加急书信。信上说帕里曼帝国的大祭司有长驻那普利亚的迹象。而且,他才驻守那普利亚不到三个月,那里的本土反抗军已经自行解散了”
我皱了皱眉,那普利亚与希尔接壤,同为信仰太阳神的国度,只是数年前被帕里曼帝国征服后,便成了它的附属辖区。
但据我了解,那普利亚的本土反抗军常年与帕里曼政府对峙,一年前甚至刺杀了新上任的地方总督,本应该是最令帕里曼棘手的地区。
我:“自行解散?他是怎么做到的?”
传信官:“信上说,他到任的第一天就独自去了反抗军营地,没有带任何随从和侍卫。反抗军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还想用绳子绑住他,但他完全没有反抗。
反而主动伸手任由他们把自己绑起来,淡定地跟着他们进了营地。一天一夜之后,反抗军的首领亲自把他送了出来。还同他握手致意,好多民众都亲眼看到了。在那之后,反抗军就自行宣布解散了。”
传信官:“解散后的成员们也没有离开那普利亚,而是选择继续留在那里生活。”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大臣们也忧心忡忡地议论起来。
大臣A:“帕里曼把这个大祭司调到那普利亚究竟是什么目的?”
大臣B:“我国和那普利亚接壤,他们可能把希尔当做了下一个目标。”
大臣A:“并且,既然那里的反抗军解散了,那普利亚的帕里曼驻军就空闲下来了。”
他们所言不假,帕里曼是一个强大而有野心的帝国,过去十数年四处扩张,征服了不少国家,希尔也曾和他们有过数次交战。
这位大祭司我也略有耳闻。他名唤陆沉,是帕里曼前任最高执政官的长孙,年纪轻轻便已执掌帕里曼教廷,算得上是核心政要。
据传,他与堂兄不和,他的堂兄甚至带着军队在他继任大祭司的庆典上逼他让位。
但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继任庆典照常举行,堂兄临走时还给他留下了一马车的金币当做贺礼。
还曾有几个城池的总督联合起来,写信向帕里曼执政官指控陆沉干涉地方军政权。
然而在陆沉配合调查,抵达中央的几天后,总督们又一个个送来书信,声称是自己误解了大祭司的美意。
思忖间,我注意到传信官正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眼角的余光还有意无意地扫向站在王座下首的大司教。
我:“还有什么情况,你一并说出来吧。”
得到了我的首肯,传信官才低着头开口。
传信官:“信报上还说那普利亚的大部分民众已经转信帕里曼的圣主教,不再祭祀太阳神。”
他偷瞄着一旁的大司教,说得吞吞吐吐。
传信官:“而且……圣主教的传播速度极快,已经蔓延到了希尔边境的卡夫拉城和尼布城——”
大司教:“哦?你是说边境的希尔国民也已经背叛太阳神,改信圣主教了?”
不等我开口,下首的大司教倒是冷笑一声,兀自转过身,咄咄逼人地看着传信官。
大司教:“这么严重的情况,我这个大司教竟然完全不知情,看来我要向陛下忏悔失职之罪了。”
眼看传信官在他的逼问下脸色发白,我压下心中泛起来的郁气,沉声开口。
我:“传信官只是例行汇报,大司教言重了。”
大司教转过身,向我浅浅鞠了个躬,勉强算作行礼。
大司教:“陛下,臣在几天前已经和边境的祭司了解过这件事,情况并不严重。只有少数几个民众受到了蛊惑,但在太阳神的教诲下,他们已经不会再动摇了。”
我不动声色地盯着他,不错,大司教当然有权力处理这些宗教相关的事务。
但能让边境总督专程写信传报的,必定不是小事,至少不会像大司教口中这么轻描淡写。
我:“高屋毁于蚁穴,帕里曼是我们的对手,任何小事都不应该轻视,大司教认为呢?”
大司教与我对视一眼,随后耸耸肩,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大司教:“陛下说的是。既然您不放心,那么臣就亲自去边境看看吧。”
临近正午时分,太阳高悬于天空,阳光饱满到像是要破裂。
薄纱手套长至小臂,我的手臂在密不透风的包裹下洇出细密的汗,皮肤上的黏腻触感让我有些心情烦躁。
踏入寝宫正殿,我褪下手套,随手掷在地上。这个大司教,竟是愈发嚣张了。
一旁的侍女迅速走上前,连连说着陛下息怒,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手套。我用力闭了闭眼,压下心口的怒火。
我:“没事了,你去准备仪式吧。”
我犹豫了一下,又叫住了离开的侍女。
我:“还有,把传信官也一并唤来,仪式之后我会见他。”
侍女点头应声,沿着小路快步离去了。
来到寝殿深处,用清水沐浴后,我挺直脊背跪在软垫上,仰头注视着高大的太阳神像,这是我即位以来每一天的固定仪式。
视线穿过袅袅烟雾,仿佛回到了那个人声鼎沸的祭神大典。我独自站在巨大的太阳神雕像前,身后则是摩肩接踵的贵族和民众。
我长久地凝望着高悬于天空的太阳。炽烈的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但我没有眨眼。
我:“太阳神在上,我将接受您的神谕,成为您在人间的伴侣,以您的名义统治这片土地。我承诺,将永远遵从您的旨意,竭尽全力以勇气和智慧引领希尔人民。请您注视着我,愿您的光辉永远照耀在希尔的大地上。”
作为希尔第一位女性法老,即位之初,我接连发布多条发展民生,削减宗教支出的政令,引得诸多宗教神职官员对我颇为不满。
朝野上下充斥着或明或暗反对我的声音,考虑到希尔国民对太阳神的信仰根深蒂固,我并不打算完全与宗教决裂。
于是,为了坐稳王位,我宣称自己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伴侣,代行祂的意志,这才将政局稳定了下来。
而大司教是追随父王多年的老臣,在时局未稳之时也为我提供了诸多助力。
他因此自诩三朝功臣,对我这个年轻的女王毫无忌惮。而我也出于维稳和感激,容忍了他诸多堪称跋扈的行为。
我应该满意的,改革推行顺利,举国清平,百姓和乐。
只是……每日长时间的例行祭祀、不能和任何人有肌肤接触、不能吃任何加调味料烹煮过的食物……
还有今日议事会上以大司教为首的旧臣,他们的肆无忌惮与阳奉阴违,我早已经历了无数次。
我无意识地摩挲着脖子上的太阳神项链,如铁锁一般冰凉沉重。保持跪姿这么久,我的脊背也隐隐传来僵痛。
莫名的烦闷如同暗火灼伤着胸腔,我不由得想起童年时,每次不开心,父王都会为我准备库纳法——一种用糖和油烹制的甜点。
那是我最喜欢的食物,然而即位以后我就没有再吃过了,我闭上眼,咽下一口冰水,勉强压下心头的烦躁之感。
侍女:“陛下,传信官大人已经到了。”
我点了点头,站起身,迅速戴上了薄纱手套,外面的人影也被侍女领了进来。
传信官:“陛下有何吩咐?”
我:“今早议事会上你没说完的话,现在继续说吧。”
传信官沉吟片刻,递上了一个木匣。我翻开木匣,见里面是一页写满了字的莎草纸。
传信官:“陛下,这是地方总督随信送来的东西,是在……希尔境内发现的,数量还不少。”
我粗略扫了一眼,辨认出这正是传布圣主教教义的告示。
纸上写着一些诸如“快乐即为圆满”、“追求欲望即是主的指引”之类的词语。
页脚上还有一个颇为抽象的花朵,细细观察,更像是在别的图案上被人随手添了一笔变作了花朵,倒是有几分肆意的潇洒之感。
圣主教的教义我多少也了解一些,大多是歌颂圣主功德、祈求圣主庇佑之流的表述,倒是从没见过这些。
对任何宗教来说,教义都是神圣的,教廷很少会对其大幅修正更改,这个圣主教怎么会如此行事。
但圣主教传播很快,又的确是事实……
我:“这么短的时间,这圣主教的传播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传信官:“这似乎是教众自发的行为,他们成为圣主教徒后便拉着亲朋好友一起入教。胆子大的还会到街上去向路人传教,地方总督已经抓了好几个关在监狱里了。”
我:“自发的行为?那位新任大祭司究竟是怎么布教的,竟能让这么多人沉醉其中?”
传信官也蹙起眉头,口吻有些犹疑。
他似乎并没有主动布教,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行宫里,甚至很少出席祭祀活动……
传信官:“但却有很多人被他吸引,自愿改信圣主教……”
他抬起头,像是想起了什么。
传信官:“对了,他有时会在圣主日举办一些宴饮的活动,很多教徒都会去参加。”
不主动布教、不参加祭祀活动、还在圣主日大肆宴饮,但却吸引教徒自发追随?
让一个信仰坚定的教徒转变信仰,这非常艰难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道真的是个人魅力?这未免太匪夷所思。
我摩挲着手中的莎草纸,直到它们变成碎屑从指尖滑落。不,圣主教能有这样大的影响,绝不可能仅仅靠大祭司所谓的个人魅力。
这个圣主教的大祭司,一定还有别的手段。
不止如此,今早议事会上大司教的态度也非常奇怪,他好像是刻意想要引导我忽视边境的异动。
重重疑团,都指向那普利亚和那个神秘的大祭司。事关重大,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亲自动身去边境一探究竟。
黄昏时分,那普利亚港口旁停驻着不少商船远处,新起的白房子错落有致,虽然还有几分战争过后的疮痍,但城市整体十分干净整洁。
紧挨着教廷的是一条商业街,道路两旁满是熙熙攘攘的摊位。街道上人来人往,大多数人脸上都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笑容。
我身旁的摊主是个中年妇人,她身边原本用于盛放圣主的神龛,里面正躺着一个小小的婴儿。
妇人一面向路人兜售商品,一面轻轻摇晃着被用作摇篮的神龛,轻声哄着熟睡的孩子。但没有人觉得奇怪,仿佛对此习以为常。
上次我来边境视察,那普利亚不说是废墟,至少也是一副百废待兴的样子,没想到一段时间没见,这里已经是生机勃勃。
我:“是因为……那个大祭司吗?”
换上一身平民装扮站在圣主教廷大门前,我取出怀中的铜镜,打量着镜中的女子。
擦去深绿色眼影与红赭石唇膏,换上帕里曼常见的妆容,如果不是隐藏在衣服中的黄金项链
与熟悉的薄纱手套,我几乎要认不出自己。
几天前,安排好政务与宫中诸事后,我带着两个身手绝佳的暗卫轻装出发,颠簸几个日夜后,终于抵达了希尔边境的卡夫拉城。
我秘密会见了卡夫拉城的地方总督,他向我讲述了和这位神秘大祭司的某次短暂照面。
地方总督:“那天我看到一匹发狂的烈马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眼看就要伤到行人。这位大祭司当时恰好就在现场,他骑着马追上去,和烈马并辔而行。他右手勾着缰绳,一个闪身就到了那烈马的背上,很快就把它制服了……”
回想起过往听到的一幕幕传言,我在脑中逐渐拼凑出他的形象,有城府、有手段、又很会招揽民心,我心中不由涌起几分忌惮。
从地方总督那里,我得知不久后将会有圣主日祭典在那普利亚举办,届时陆沉有很大可能亲临现场。我不由得生出了想会会他的念头。
令人意外的是,圣主日祭典并没有准入门禁,甚至不需要出示任何凭证就可以随意出入。
在我印象中,祭典应当会由教廷的神官充当临时工作人员,严格审查参与祭典的教徒身份,为此我甚至提前备好了一张身份证明。
不过,没有资质审查倒是免去了许多麻烦。我让暗卫随时待命,迈步走入了祭典现场。
穿过灯火通明的长廊,就是教廷的正殿了,高大的门扉站着一位笑意盈盈的妇人,我走上前,向她打听起来。
我:“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需要先去拜见圣主和祭司大人吗?”
她笑呵呵看了我一眼,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妇女:“不需要,咱们这没那么多规矩。祭司大人开明得很,他有时候都不来参宴的,大家吃完也就散了。喏,里面的空位不多了,快进去坐着吧。”
我点了点头,顺着她指的方向跨入了正殿中。
比起祭典,这里布置得倒更像是宴会,大殿内空间十分宽敞,提比亚管和里拉琴美妙的声音交相辉映,回荡在空气中。
四周白色的墙上挂着装饰用的红罂粟花环,华丽的深红色地毯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大厅深处。
地毯的尽头,本该是主座的位置并没有摆放椅子,甚至没有台阶,而是铺了一张地毯,随意堆叠着几个精致的蒲团。
大厅居中摆放着数十张巨大的长桌,桌旁坐满了打扮各异的教徒,有富贵人家,也有贩夫走卒,甚至还有不少衣衫褴褛的乞丐。
长桌上堆叠着精致的菜肴,有各式各样的肉类和蔬菜,还有用无花果、椰枣和西瓜拼成的果碗。
镶嵌着红宝石的银质酒壶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迷离的柔光,显得华美而精致。
可据我所知,圣主教的祭典活动多是由祭神仪式和聆听祭司教诲组成的。
虽然偶尔也会举办一些招待教徒的宴席,但这些宴席大都是在教廷内的小房间举办,菜品也以清淡的蔬果为主。
我打量着四周的人群。主座还无人入座,宾客们已经一边享用食物,一边互相攀谈起来。几个乞丐甚至抓起桌上的食物狼吞虎咽。
一旁站着的侍从面色如常,非但不出声制止,还不断地为空掉的盘子重新添上食物。
我四下看看,找了个视野不错的空位坐了下来。
刚坐定,身后便传来两个教众交谈的声音,我凝神去听。
教众A:“欸,你听,又是那首乐曲,每次开宴演奏的乐曲好像都是这首?这个旋律……也不是圣歌啊,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曲子。”
教众B:“你不知道吗?这好像是祭司大人自己谱的曲子,果然能让人的内心非常平静呢。”
大祭司自己谱的曲子?我心中一动,认真听了起来。
开始时曲调舒缓,宛如在月夜下的海面上撑着船航行。
可随着船越行越远,原本平静的水面渐渐泛起细微的波纹,似乎有波涛的啸音卷起旋涡与暗流,在深深的海底涌动。
我不由自主便被那克制的汹涌吸引,完全沉浸在音乐中,意识搭载着小船越走越远。
耳畔的音乐声依旧柔和,但我却在那平静的曲调下听出了澎湃的激越之感,那小船也在海面上踏浪迎风,向着月亮航行。
我被这畅快自由的感觉所慑,更加沉浸在音乐中。当那小船借着翻腾的浪头跃空而起,我也随之心神激荡,情不自禁重重拍了一下桌面。
突然,四周安静下来,从沉浸的状态抽离出来,我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闭上了眼睛,还将刚才畅快的感受说了出来。
我睁开眼睛,却发现大家并不是在看我,而是看向了主座的方向。
??:“我很少见到,有人以这样的方式欣赏我的音乐。”
我望向声音的来处,两个侍女拉开主座后的金色纱幔,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显现出来。
来人的视线遥遥定在我脸上,似乎是笑了笑,随后施施然走了出来,一条被金锁固定住嘴部的鳄鱼跟在他身后。
他的音乐?难道他就是大祭司陆沉?
想到自己刚刚的忘形之态,我不由得有几分窘迫。
我抬眼对上他的视线,见他的唇角似乎轻轻勾了勾,像是单纯在笑,又像是在缓解我的尴尬陆沉
我:“我很高兴。”
说完,他不再看我,理了理衣摆,随意靠坐在主座的蒲团上。
他的五官轮廓略深,窗外的夕阳打在他身上,半边脸沐浴在阳光中,如同雕塑般俊美。
丝质长袍披在他身上,鎏金暗纹在阳光下折射出黄金般的柔光,他身上挂着许多饰品,无一不镶嵌着名贵的宝石。
如此奢靡的打扮却并不让人觉得违和,珠光宝气都被他周身的气度压了下去,好像他生来就该是这样的。
他的坐姿随意而慵懒,一手轻轻搭在身侧的鳄鱼上,手臂舒展间,他的衣衫微微散开,露出轮廓分明的腹肌。
大厅内响起潮水般的欢呼,不少教众离开座位向他鞠躬行礼,口中高呼祭司大人安康。
而他神色如常,只是淡淡抬眸,颔首示意,既不因赞美欢欣,也不因尊敬倨傲。
一举一动都透露出一种游离于尘世之外,漫不经心的优雅。
他看起来更像优雅的贵公子或是闲散贵族,怎么也和我脑中想象的那个手腕强、有威胁的政敌形象搭不上边。
教众们安静下来,等待着他的教诲,我以为他要说些教义相关的东西,可一开口却并不是。
陆沉:“诸位,不必拘束,美酒和佳肴应有尽有,尽情享受吧。你们的喜乐与满足,就是献给圣主最好的礼物。”
欢呼声和赞美声更猛烈地涌来,人们大快朵颐,交谈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大厅里洋溢着轻松和乐的气氛。
而陆沉正一手撑着脸,一手把玩着手中的酒杯视线静静落在沉浸于欢宴的众人身上。
侍从在身后为他扇着风,而他懒散地望向席间众人,偶尔用银质酒壶倒一杯葡萄酒,慢慢品
着,手指在桌上随着音乐节奏轻轻敲击着。
奏乐声不停,宴会继续,众人酒至半酣。
他看着人群自斟自酌,偶尔来了兴致,还随手拿过一旁的里拉琴跟着弹奏一段。
台下教众也捧场地卖力鼓掌,大声喝彩,倒真有几分宾主尽欢的感觉。
侍从在长桌间穿梭,端上新的菜肴,鼻尖嗅到甜蜜的味道,我定睛一看,新上了一盘库纳法,就正正放在我面前。
开心果碎和蜜糖包裹在金黄的酥皮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被这味道吸引,我的肚子也有点饿了起来,便在果碗里随意捡了一样慢慢吃。果香清甜,汁水充盈,但我总觉得味蕾有些不满足。
意识到自己的视线总是被库纳法吸引,眼不见为净,我索性将它端起来递给了桌子对面眼巴巴望着这道甜品的小孩。
就在我思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身旁的两个教徒不知聊到了什么话题,激烈争论起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教众C:“我不同意!金银只是世俗之物,真正的感谢应当出自本心!”
教众D:“不奉上金银供奉,怎么表达我们对圣主和祭司大人馈赠的感谢?我看是你想一毛不拔才这么说的吧,祭司大人仁慈,但我们不能不懂分寸啊。都像你一样白吃白喝,末了去教廷祈祷一下就心安了,那还了得?”
被诘问的教徒脸涨得通红,不甘示弱地反击回去,两人声音越来越高,将四周的目光都吸引过来。
幸畫两人越说越激动,其中一个见我离得很近,便要拉着我让我评理。
我用余光瞥见陆沉正看向这个方向,一股莫名的兴奋和蠢蠢欲动将一个念头顶了上来。
我转过身,看向陆沉。
我:“难得有幸当面聆听祭司大人的教诲,不会有谁比他更权威了。二位的争论,不如就请大人裁决如何?”
我的声音不算低,人群静默下来,大家纷纷望了过来,陆沉的视线也定在我身上,过了片刻他笑了笑。
陆沉:“可以。”
两个争论的教众见陆沉同意,便也离开座位走到大殿中央,解释说方才两人是在争论该如何表示对圣主日宴席的感谢。
认为金银重要的教众从随身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莎草纸,向众人展示。
教众D:“大人,这是我的献金文书,我每月都会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献给圣主。”
教众C:“呵,连每五天一次的祭神仪式都缺席的人,只是奉上些银钱,就能说自己虔诚了?”
教众D:“据我所知,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献过一笔金了,你还欠着教廷不少钱吧?”
四周的宾客小声讨论起来,有些觉得金银重要,有些觉得不参加祭神仪式是不敬神的表现,大家各执一词,不由自主把目光投向陆沉。
陆沉仍是慵懒地靠在软垫上,面上波澜不惊,他看向认为金银重要的教众,声音温和。
陆沉:“就在月前的宴会上,我似乎说过,此后不强制大家参与祭神仪式。献金多少也各凭本心,量力而行即可。我想,就算我当时在喝蜜酒,但没有醉,这话应该还是有效的吧。”
他摩挲着手中的酒杯,神色还是一派从容温雅,周身的气质却隐隐显露出一股威压。
陆沉淡淡勾了勾唇角,教众们安静虔诚地望向他。
陆沉:“不过,既然是为你们的争论裁决,那便请说说你缺席祭神仪式的理由吧。”
献金的教徒涨红了脸,急急开口解释。
教众D:“我是商人,时常需要出海贸易,并不是故意缺席祭神仪式的。”
陆沉略微点了点头。
陆沉:“的确情有可原。不必担心,遵从契约精神,做好商人的本职工作。让买卖双方都获得愉悦和满足,也是回应圣主恩德的一种方式。”
献金教众对陆沉感恩拜谢,但他只是略一抬手,便转向另一个教众。
陆沉:“家中可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被问到的教众攥紧了双手,嗫嚅着开口。
教众C:“不是的,只是最近家里盖了新房舍余钱不多,之后我一定能补上……你的献金文书带在身上吗?”
他连连点头,从怀中取出一张纸,递了上来。
陆沉接过,一旁的侍从为他呈上清水,他伸出手,指尖轻点过水面,随后略一旋手腕,在文书上洒下水痕。
陆沉:“好了,你的欠款已经两清了。”
说罢,他面向众人,淡然开口。
陆沉:“强制征款是前任祭司的教令,从今天起,所有人与教廷的遗留欠款都一笔勾销。”
人群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和赞美声。
他似乎又是在宴会上,随口就颁布了一条了不得的教令。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陆沉所执掌的圣主教,一定不是我所了解的那个圣主教。
但他如此行事,究竟是他个人的想法,还是帕里曼帝国的决策?这个陆沉,倒是愈发让我捉摸不透了。
我隔着人群看向陆沉,却正对上他望向我的目光,他笑了笑,从身旁的花瓶里撷下一支蔷薇花。
他招了招手,对着侍从耳语了几句,侍从点点头,端着花和一个餐盘径直向我走来。
众目睽睽下,侍从停在我身前,将花递给我,微微弯腰向我行了个礼。
侍从:“小姐,祭司大人想知道您对他刚刚的裁决是否满意。”
淡粉色的蔷薇花散发着宜人的清香,露水顺着枝叶滴落在我的指尖,留下微凉的水印。
我:“请转告祭司大人,您的回答与这支蔷薇的香气一样令人豁然开朗。”
侍从点点头,将手中的餐盘放在我面前。
侍从:“这是祭司大人特别赠送给您的菜品,请您慢慢享用。”
他回到陆沉身边,弯着腰说了几句。陆沉笑了笑,遥遥向我举起了酒杯。
想了想,我也举起桌上的酒杯向他遥遥致意。他眉梢轻挑,脸上绽出了一个颇为英俊的笑容。
收回视线,我打开了面前的餐盘——是库纳法。
和刚刚那盘不同的是,金黄色的酥皮表面多刷了一层无花果酱,微酸的气味中和了甜腻的香气,让它看起来更加诱人了。
他刚刚一直在关注着我吗?所以才送来了这盘点心?
最终,我还是拈起叉子浅尝了一口,甜蜜微酸的味道瞬间在口中融化开来。
待到这久违的味道在我唇齿间消散,我克制地放下叉子,将餐盘重新扣了起来。
这时,主座的高台上传来了侍从的声音。
侍从:“诸位,今天是本年度第一个圣主日,是个特别的日子。稍后大人会亲自挑选一名信众,被选中的人今晚可以单独觐见大人。”
话音刚落,人群骚动起来,从周围人那充满期待的神色中,不难判断出与大祭司单独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陆沉饶有兴味地笑了笑。
在众人目光注视下,他拍了拍身旁的鳄鱼,这条鳄鱼颇有灵性,登时摇着尾巴,晃晃悠悠地爬下来。
陆沉:“去吧,挑选今晚的客人。”
这是可以和陆沉单独交流的绝佳机会,我不能放过。
鳄鱼的声音细细簌簌地由远及近。我正低头想办法,没注意到面前的人群已分开一条通道。
那鳄鱼在人群中蜿蜒爬行,竟是朝我而来。
下一刻,鳄鱼在我身边停下,不再动了,它冰冷而有力的尾巴勾住了我的脚踝。
一时间,我被教众们艳羡的目光包围,我隔着人群与陆沉对视,只见他已经走下高台,缓步向我走来。
夜幕降临,在灯火柔和光辉的映照之下,陆沉的面庞有一种慑人的俊美,那双红宝石般的眼眸中也透出几分笑意。
他向我伸出手,语调放得又轻又缓,我竟隐隐品出一丝暧昧。
陆沉:“看来我们很有缘分。那么,这位小姐,你愿意留出今晚的时间,与我共度吗?”
这正是我今晚来这里的目的,我又怎么会不愿意呢。我勾起唇角,将手放在他手上。
我:“当然,我的荣幸。”
片刻之后,我身处教廷深处一间私密房间内,地上铺着厚厚的丝绒地毯,熏香的气味弥散在空气中,矮桌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捧新鲜的蔷薇。
我应下他的邀约之后,陆沉便带我来到了这里。
他正坐在我对面的软垫上,侍从已经静悄悄地退下,房间内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
房间内的装饰不似宴厅一般奢华,也并不宽阔,但从陈设到装饰都很考究,跳动的烛火在纱幔上投射出幽暗的阴影。
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他胸膛起伏呼吸出的热气,以及他身上酒香混合着苦艾的味道。
我还在思忖接下来要说些什么,陆沉先开了口,他的声音温醇,低低在我耳侧响起。
陆沉:“你的脸有些红,很热吗?要不要取掉手套和丝巾?”
我一怔,伸手摸了摸鬓角,果然察觉到细密的汗,不自觉地调了调手套和丝巾的位置。
我:“没关系,我习惯戴着它们了。”
陆沉笑了笑,倒是没有再坚持,而是拿过一旁矮桌上盛放着冰水的银壶,倒了一杯水递给我。
冰水沁凉的温度稍稍缓解了我的热意,我理清思绪,斟酌着开口。
我:“抱歉,我还是第一次被选中,没什么经验,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陆沉闲适地靠坐在软垫上,看着我,唇角勾起一抹笑意。
陆沉:“不必拘束,有任何烦恼的事,或想知道的问题都可以问我。”
我:“任何问题都可以吗?”
他唇角的笑意加深,望着我点了点头。
陆沉:“任何。”
等待我开口的时候,陆沉似是有些无聊,随手摩挲着花瓶里的蔷薇,花瓣的汁液在他指间洇出一抹暗红。
我:“那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您今晚要选择我?”
陆沉:“我选择你?何以见得?”
我:“没猜错的话,应当就是您赠给我的那朵蔷薇吸引了鳄鱼吧。”
他深红色的眼底闪过一抹兴味。
陆沉:“你猜的没错,的确是我的意思。至于为什么选择你,大概是因为,你看起来是唯一没有在享受宴会的宾客。”
没有在享受宴会?我有些愣怔,看向陆沉,他顿了顿。
陆沉:“欢宴的氛围不能让你露出笑容,教徒间的闲谈也没有让你想参与其中。除了几块水果,宴会上其他的食物似乎并不合你的胃口。”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这位大祭司的神态间竟
然有些淡淡的委屈。
陆沉:“而且,那盘库纳法你也只浅尝了一口。”
他眼睫低垂,像是在遗憾这场宴会没有取悦我,但他的眼神却平静如水,带着几分探寻的意味,几乎像是一种暗示。
他发现我不是圣主教徒了?
我低下头,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
我:“抱歉,大人……”
陆沉看着我,我几乎可以确定了,他知道我不是圣主教徒。但他脸上并没有怪责的神色,连唇角的笑意也是安抚而温和的。
陆沉:“不必紧张,我从没说过只有圣主教徒才能来参加宴会。哪怕你只是对这场宴会有些好奇也没有关系。”
烛光摇曳,在陆沉的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衬得他整个人仿佛身处迷离的梦境。
我轻轻吸了一口气,明白他这是默许我继续问下去,便顺着他的话,装作一副纯良的样子继纹开口。
我:“您所说的,正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您所治下的圣主教,似乎和我从前了解的不太一样……”
我:“简直就像是……保留了圣主教的名字,但是内里完全换了一个样子。”
闻言,陆沉轻笑一声。
陆沉:“如果大家能正视自己的欲望,并最终得到满足,用什么名字应该不太重要。”
他似乎完全没有觉得这是个事关神权与国事的严重问题,轻描淡写地给出了他的回答。
我:“那么,如果他们的欲望是改换信仰,你也会允许吗?”
他眉梢轻挑,点了点头。
陆沉:“当然,圣主允许一切发生,只要能让祂的信徒们感到幸福和宁静。改换信仰自然也是如此。一个人愿意相信什么、又愿意奉行什么,圣主尚且不去置喙,何况是我呢。”
他的视线定在我身上,神态慵懒,却又莫名让我觉得有几分认真。
我收回目光。
我:“原来是这样。不过,现在的大家似乎还是很依赖和崇拜祭司大人。他们向您请教很多问题,甚至在做决定时也依赖您的指示……”
在我看来,只要人们心存信仰,就会有被统治和控制的风险,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自由。
陆沉不置可否,端着酒杯直起身来,轻轻与我手中的银杯碰了碰,然后一饮而尽。
随着动作,他身上的珠宝发出一点清脆的声响,细碎的叮当声轻轻重重地落在我耳畔。
我低下头,看着手中的银质酒杯反射出烛火微渺而迷离的光。
陆沉:“那是因为,他们想要在我身上寻找自己不敢正视的欲念。想要藉由我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是什么。而我只是一种投影。”
他走到我身旁,俯下身与我对视。
我在他的眼底深处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伴随着微微闪着的一点光,像是碎冰在红色的海水中荡漾。
被他这样注视着,我有些晃神,陆沉轻轻笑了一下,微凉的指尖轻轻拂过我的侧脸。
陆沉:“这样的表情……之后你也许可以告诉我,在我的眼中,你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他的尾音温和而轻缓,仿佛想将我的意识也包裹其中,我抬起头,不闪不避地对上他的双眼。
关于宗教理念的见解只是引子,我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问,陆沉到底对希尔境内的圣主教是什么想法?是默许还是纵容?
我:“可是,与周围其他宗教相比,您的教义是如此不同,这样不会产生冲突吗?如果产生了冲突,您又要怎么处理呢?”
陆沉:“满足欲望和恪守教律都只是获得安宁的方式而已。有的人着眼来世,所以选择苦修换取安宁。
而有的人更在意眼前的幸福,于是及时行乐、不留遗憾。有的人需要权力与地位傍身才能感到平静……那自然也有人选择不参与人事、不碍于俗务。”
陆沉平静地笑了笑,似乎不以为意。
陆沉:“我只知道来到那普利亚的人们都获得了满足与安宁。”
不知不觉之间,屋内的气温似乎越来越高,我喝了一口杯中的冰水。被我攥了许久,水温只剩下微微的凉意,根本无法缓解我的热意。
他说了很多,似乎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但却对最关键的症结模棱两可。
他暗示自己不在意俗务,却又对理念冲突和可能由此产生的战争不置可否,也许是他真的不在意,也许是他对我有所隐瞒。
但我知道,即使再问下去,我也不会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
我关于他的一些猜测终究是对的,他比我想得更加深不可测。
奇怪的是,这个认知并没有让我恼火,反而让我心口有些鼓噪。
我将手中的水杯放在矮桌上,直起身看着陆沉,并没有再问下一个问题,我打算结束今晚的会面了。
但陆沉却像是没有察觉到我的想法,依然闲适地靠在软垫上,丝毫没有要送客的意思。顿了顿,我还是问了出来。
我:“今晚已经叨扰您许久,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您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吗?”
陆沉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拿起矮桌上的水壶,往我的水杯里又添了一点冰水。
陆沉:“你的烦恼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除。”
我:“可是——”
陆沉:“我说过,今晚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任何,这个词语再次轻轻地、格外鲜明地叩在他的齿间。
仿佛只是一次单纯的重复,又仿佛是在埋怨我没能够好好地利用它。
宴会上,隐藏在平静乐音下的激昂旋律,再一次在我的耳畔响起。
我知道,我还有许多被掩饰过的、滴水不漏的问题可以问。
可是,陆沉指尖的蔷薇花散发出影影绰绰的香气,我心口的火苗也似乎被他指尖红色花汁留下的印记引燃。
任何问题……那么,我想问却又压在心底的那个问题是
我:“既然您说来到那普利亚的人都获得了安宁,那么您呢?您也获得了安宁吗?”
我抬眼,对上陆沉略带错愕的神情,他似乎完全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他沉默了片刻,并没有移开视线,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我看到他深红色的眼底深处洇出了一抹笑意。
那笑和他今晚所有的笑都不一样,带着真诚的快乐,仿佛是看到了某种非常喜欢,非常感兴趣的景象。
陆沉:“如果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会感到满足吗?”
我:“……您怎么想?”
陆沉:“我想,不会。因为……”
他的声音轻而低缓,轻轻重重地落在我的耳畔,带来一阵酥麻的微痒。
陆沉:“让你不满足的东西并不全在我身上。”
陆沉靠了过来。
他轻轻抬起我的手,握住,带着我的指尖移向另一只套着薄纱手套的手臂。
陆沉:“你觉得热,想要脱掉手套,让这片皮肤自由呼吸。”
他带着我的手,又移向我的腹部。
我后知后觉感受到了饥饿,这才想起晚餐我只吃了几块水果。
陆沉:“很饿,是吗?你应该吃些喜欢的东西。”
然后,手指慢慢挪移到我的心口。
陆沉:“而这里,还有很多欲望,比一个回答多得多,无穷无尽。所以你不会满足。”
四目相对,陆沉深红的眼中倒映着烛火暖黄的光晕,如同有明灭不定的情绪在他眼中跳动。
蔷薇的香气忽远忽近,仿佛某种让人迷离的香料,将我心中那一点蠢蠢欲动的兴奋勾了出来。
我:“那您知道,我要怎样才能满足欲望吗?”
耳畔传来一声轻笑,陆沉看着我,英俊的五官在这样的环境下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魅力。
他做出个邀请的手势。
我:“那您知道,我要怎样才能满足欲望吗?”
耳畔传来一声轻笑,陆沉看着我,英俊的五官在这样的环境下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魅力。
他做出个邀请的手势。
陆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一些方法。”
一瞬间,那些被我一次次压下去的,无数压抑的、躁动的、渴望的记忆片段如云雾般从脑海深处翻涌上来。
我抬眸对上他的眼睛,终于做出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