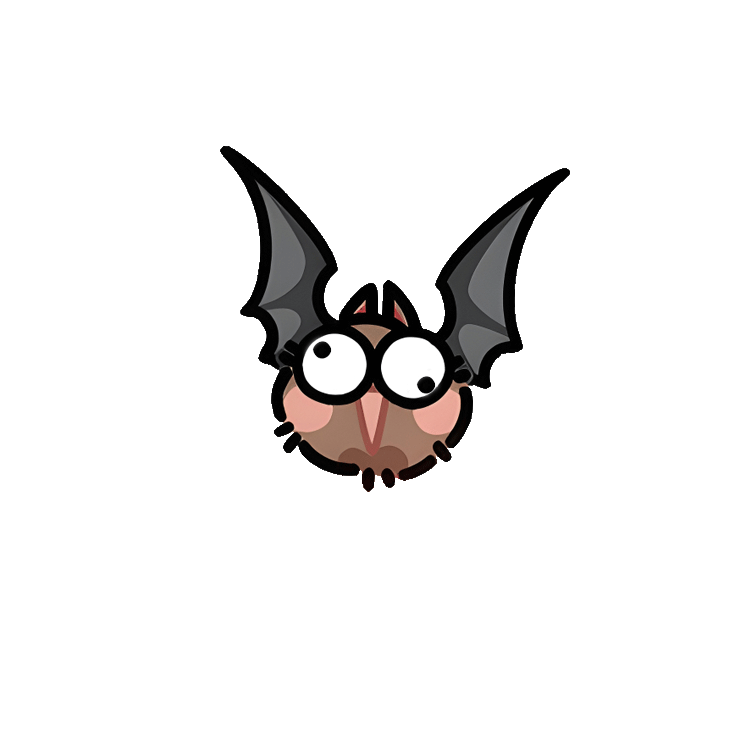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11年前.春天❈
在我庸俗的人生里,我愿意想起的只有十四到十五岁那一年。但你如果问我是因为喜欢吗?我的回答是不。同时我也肯定地知道,我不讨厌。事实上,我找不到一个精准的词去形容或总结,它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是在那年春天偶然捡到了一本波拉尼奥的小说。在此之前,我能接触到的文字只有乐谱上的注释,冗长的家谱以及热衷把谎言说成真理的课本。它们像盐一样无孔不入,将我腌制成一块越来越干瘪酸咸的肉,挤不出任何灵感和梦想的成分,没有品尝的必要。
每当身体被摊开来涂抹时,我都会在心里祈祷腐败的到来,我想我会格外平静甚至面带微笑地迎接,当然我允许自己保留一点凄楚,这是我对生命最后的敬畏与友善。
直到身上出现了第一块霉斑,我是说胸前那个新鲜的、还在流血的碗口大的伤,大到心脏几乎可以脱落。
没有哪个时刻比现在更接近死亡,然而一种久违的恐惧却猝不及防地在体内疯长着,到最后,我被打败了,我看着自己将一颗颗棉球连同所有的痴迷和邪念都塞进身体,血将它们都粘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块自成一体的新的皮肉。假如死神恰好在这时到来,定会嘲笑我的虚伪和怯懦,幸好窗外浓稠的夜如火车铁轨横亘在面前,我甚至都听见了他懒得跨过来而离去的脚步声。
我站在原地想了很久,这些天来,每每一个人待着的时刻我都在想,我困在那场投降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解释。后来有一天我想明白了,是因为那本未读完的小说。
大概我从没见过那样无所畏惧的文字吧,我是个在葬礼上都挤不出眼泪的人,很难想象有什么悲欢的场合,我愿意从心底主动掏出仅存的那点情感。
可它荒唐得妙不可言,又浪漫得妙不可言,让人目眩神迷。我开始昼夜不分地阅读,后来甚至每隔几天就往枕头下放本新书。就着月光,席地而坐。
我想我就是在那些时刻,爱上的它们。
当下一次试炼即将到来的时候,我读Olivier不堪忍受虐待,逃出寄养的棺材铺,从乡野小镇独自徒步前往伦敦。当我想念因我而逝的伙伴的时候,我读拉里目睹朋友牺牲,怀疑活着的意义,一路从煤矿厂到修道院,发现体力劳动和宗教都无法给他答案。
我嫉妒书里面的每个自己,也痴迷无数个与我截然相反的他们。我读在未知的荒谬里尽情绽放的理想,奴役人的爱情,望不到底的痛苦,读不再诗意的世界,卑微的下限,放浪的肉体,喷薄的情欲,读终其一生也无法抵达的天堂我想恐怕他们都不知道,我最迷恋的就是每个困在挣扎里的人张开双翼时,那些羽毛刮擦过我灵魂带来的颤栗,这让我错觉终于不是独自一人,活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上。
这个夜晚,摊开的书停在托马斯和特蕾莎灵肉合一的地方,清晨就要来了,我知道我该睡了,可我却久久没能如愿,闭上眼,我甚至能清晰听见身体里漾起陌生的潮水的声音,接连的浪几乎要把灵魂都冲出去。在那个毫无戒备仅剩不多的夜里,我第一次有了探寻的冲动。
风在窗外呼啸,将我变成了一块在汪洋上空打转的海绵,也可能是树叶,随便什么都好。第三次了,飞翔的感觉还是那么让人上瘾,漂过海与天交接的尽头,我张开沉重的双臂,抬头望见了一轮火红的太阳。我从不敢直视太阳,它总让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可那天不一样,那天不一样。
它慈悲的眼神让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哪怕是堕落与罪过,都会被宽恕。我想起了儿时不舍离去的温软怀抱,心跳得飞快,全身上下都绷得紧紧的,一股热流沿着脊背往上窜,又顺着身体滴下。刹那间,我的大脑空了,这种感觉既尴尬又陌生,身体里却涨满了原始直白的快乐——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早已销声匿迹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