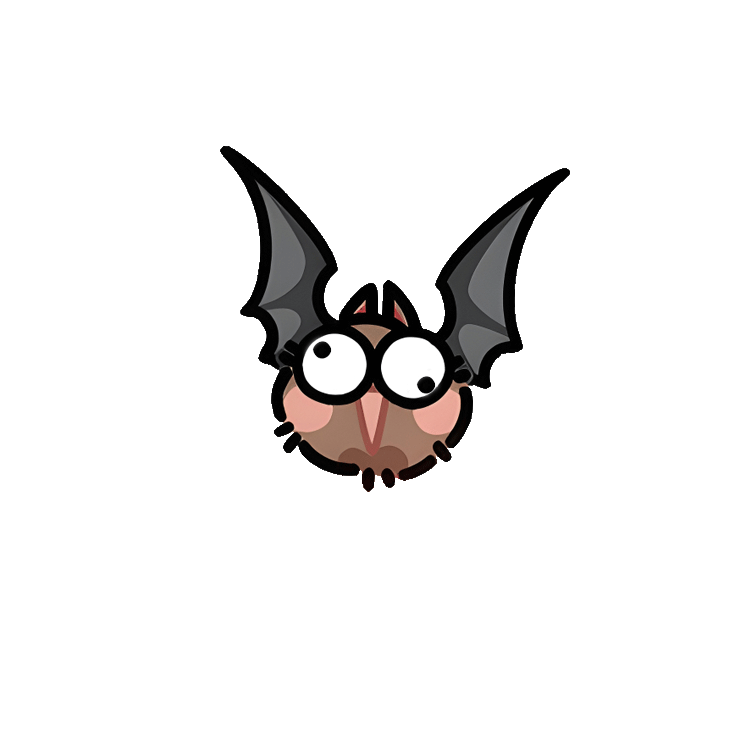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灵柩❈
HSA执行官陆沉发表演讲,近日来,部分组织以重启Kepler计划为口号,妨害月球家园计划进度。
中央塔将对相关人员进行抓捕。再次重申……
投影出的新闻定格在中央塔武装闯入Kepler计划秘密基地的混乱画面上,在那些被押送离开的人中,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他们都是我预备学校的校友,和我一样怀抱着寻找新家园、拯救人类的理想。
只不过,他们毕业后没有选择进入中央塔,也没有交代自己的去向。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们与我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重启Kepler计划。
自那之后,我便在暗地里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而不知何时,陆沉也掌握了这一行动,并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谋划了对策,给予对方精准一击。
似乎是预料到了我此时的沉默,眼前西装革履的秘书长脸上,露出了笑容。
秘书长:“自从升任后,我们的陆执行官似乎做了很多事情。”
秘书长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我明白他话里的含义。
五个月前,地面矿场的补给没有及时发放,在当地引发冲突,陆沉派遣人员前往“调节”,造成了数名平民伤亡。
三个月前,宣传部得到了一份来自于执行官的文件,半个月后,人们习惯了不去议论中央塔未曾说明的事情。
秘书长:“到了今天,陆执行官甚至不再找其它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是直接针对Kepler计划下手——
为什么?因为Kepler由中央塔主持废止。任何重启该计划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人类文明的背叛。
中校,正如你所见,我们认为中央塔如今的决策者已经走入歧路。”
我:“他走入歧途,你们应该去劝告他,为什么来找我?”
秘书长:“我此行的目的,是代表中央塔秘书处,邀请你加入我们,共同挽救HSA。”
秘书长并未多做迂回。加入秘书处,意味着同意他们对于执行官的观点,我也坐直了身体,直视着他。
我:“陆沉是我的导师。”
秘书长:“但你们关系似乎也没那么融洽。我听说,当初你之所以离开社理会……就是因为和他在一次会议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意见分歧。”
我没有说话。他说的,是在陆沉升任之前、我也还在社理会的时候,一次关于申诉通道调整的会议。
那顿在陆沉家的晚饭之后,我继续留在中央塔工作。
我们不再吝惜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那次会议上的意见分歧,或者说争吵,不过是无数次办公室交锋的缩影。
我有过不能保持冷静的时候,陆沉也有过。我认为他有过。
他的失态很沉默,像是一座不会爆发的火山,只有看着我的眼睛里,流淌着混杂无数情绪的岩浆。
有时候,我会以为那是痛苦,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是高兴的。
事后,我们会向对方道歉。然而,大多数争吵最终还是以执行陆沉的决策作为了结。
那次会议后不久,我借着职级调整,申请从社理会调走,陆沉也在我离开社理会后去了安理会,又很快升任了HSA执行官。
不过,我和陆沉的关系并没有像传言里说的那样彻底闹僵,与此相反,我们之间的相处反而更加平和。
我们很少有工作上的交集,因此有更多时间用来说闲话,还有回忆往昔。
在这两年里,我逐渐做到了中校的位置。那时在资料库里没有打开的秘密文件,我也遵守承诺,凭借自己的能力了解了。
从愤怒、难以置信,到麻木、司空见惯,我对末日世界的认知在一个又一个秘密的暴露中不断被打碎又重组。
陆沉也许看出了我的变化,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更加频繁地提起以前的事情。
跨年时在学校篝火旁的低语、生日时一起偷溜出学校看到的日出、实践课上去污染区调查时在废墟里找到的一朵盛开的花……
他似乎是在用这些尚存温度的回忆,来帮助站在深渊边上的我保持最后的微妙平衡。
我也逐渐知道,中央塔并非固若金汤,人们各怀心思,发展着自己的利益和势力,希望这台强大的机器能为自己所用。
新一届秘书处有与安理会争权的心思,陆沉自然也明白,因此他刚升任,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令他们顺从——至少表面上如此。
陆沉从来没有向我发来任何代表安理会的邀请,或者是拉拢我,一次都没有。
我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他的举动,并且最终承认自己已经越来越看不清他。
秘书长:“如果你仍有迟疑,请看看这份文件这也是我们的诚意。是目前中央塔全力实施的月球家园计划的真相。”
说着,秘书长将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我低下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熟悉的封面。
我用自己的方法见过这份文件,也已经知道月球家园计划是一个谎言。
实际上,这个计划是为了将一些所谓的精英人士送上太空,放弃大多数人的生存可能。
于是我没有翻开它,而是看向秘书长稳操胜券的神情。
我:“你们把这份资料带出来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拉拢一个并不确定会加入你们的人,值得吗?”
秘书长:“我们希望你能继承Kepler计划第一代主理人——也就是你外祖母的意志和理想,帮助HSA延续全人类的文明。”
我:“你们的意思我了解了,但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
秘书长:“当然,在这个地方,信任并非易事,我们会等待你的答复。”
秘书长笑了笑,很干脆地站起身,离开的时候轻轻带上了办公室的门。
我望着眼前投影上的混乱画面,任由大脑自行运转。
秘书处选中我的原因,恐怕是他们现在急需一个有身份的代言人,而且不仅只是有身份。
好比从前的摄政者挑选继任者,有能喊出口号的身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位代言人必须孤立无援。
这么一看,我这个前任Kepler计划负责人的直系亲属确实要比那些出身世家的上层子弟好掌控很多。
我:“信任吗……”
刚开始实习的那段时间,有一次快要下班,陆沉拿着一块银币,让我猜猜在哪只手里。
我选中的手心里什么也没有,可当他摊开另一只手时,银币也不在那里。
我:“啊,你明明说的是,猜猜在哪只手里!”
陆沉:“但也有两只手都不在的可能性。这位小姐,你太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了。”
说完,他笑着从袖口掏出银币,放到了我的手心。
我:“不是容易相信别人,我相信你。”
陆沉:“那你现在知道了,谁也不值得信任,包括我在内。”
我:“可不是嘛,所以,今天的晚饭是不是应该由陆学长来请啊?”
陆沉失笑,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陆沉:“是该补偿你。我们走吧。”
我们随意地聊着天离开了办公室,那句信任和不信任的话,那时我只当作玩笑来听。
我感到一阵头疼,站起身来,拧开了办公室的门。
而刚刚脑海中的那个人,就等在门外。
陆沉穿着那身笔挺的执行官军装,胸前的勋章绶带在灯光下反射出冰冷的光泽。
他一手拿着军帽,一手垂在身侧,偏头看着门上的金属铭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职级。
他站得很直,我看不出他在这里站了多久。
我:“陆沉,今天怎么过来了?”
陆沉:“来找你。”
我:“等很久了吗?”
陆沉:“没有。刚和秘书长说了几句话,正好你就出来了。”
原来他们在门口碰到了,那他知不知道秘书长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陆沉的嘴角有一丝笑意,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那难得碰到了,要不要一起去吃饭?他却摇了摇头。”
陆沉:“不了,我把这个交给你就走。”
说着,他递过来一张纸。
我:“LeoLee先生,享年23岁……遵照Leo先生遗嘱,丧事将于……”
这是一封讣告。LeoLee,是陆沉的同班同学。
脑海中掠过一群飞鸟,过往那间硕大校园中的种种悉数重现眼前。
陆沉的社交往来很频繁,但如无必要,却并不喜欢与别人呆在一起,我去找陆沉时,如果他身边有人,基本上都是Leo。
有时是在篮球场上,Leo因为对面的犯规动作而和对方吵成一团,陆沉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在冲突升级的时候恰到好处地介入。
有时是在教室里,Leo嬉皮笑脸地求陆沉把预测出来的考试重点分享给他,陆沉给了,换走了两张新城天文台的准入票。
印象里,Leo是一个好像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十句话里有六句半是插科打诨,剩下的三句半里有哪些真话,还得看他当时的良心。
那时他一看到我,就会吹声口哨,问我是不是又来找陆沉啦,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并不常见的棒棒糖递给我。
说这是贿赂,问我下次能不能帮他向陆沉借笔记啦、借餐卡什么的,省得他每次都做赔本买卖。
他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上一次看到他的名字,似乎是在……对了,是在重启Kepler计划的人员名单上。
现在,Leo死了,而陆沉最近发动了针对Kepler计划人员的搜捕行动……
头疼在这一瞬间更加剧烈而尖锐地淹没了我,我的眼前泛起虚无的重影。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彻底陷入黑暗时,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了我。
陆沉:“怎么回事?”
我抬起头,在逐渐褪去的黑影中,看见陆沉紧皱着眉,像是在担心。
陆沉:“你的脸很白。你连续工作了多少个小时?”
我:“没多久……”
我用力地揪住了他的袖子,就算已经站稳也没松开,我想我手里抓住的,是即将被淹没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陆沉,Leo的死,和你……和中央塔最近发动的搜捕行动,有没有关系?”
陆沉:“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
我:“作为Leo的朋友,也不行吗?”
陆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片刻,他点了点头。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我:“但你知道他参加了Kepler计划。”
陆沉:“他告诉过我。”
我:“可你什么也没有做。”
陆沉:“我应该做什么?”
陆沉的眼神一点点冰冷下去。
他的右手握上我的手腕,将我的手拉开,拉开的时候,攥得很紧。
陆沉:“提前给他通风报信,还是用特权将他赦免?Leo违背了中央塔的意志。”
我:“我也违背过中央塔的意志!”
我说得很大声,陆沉看向我的眼神里,有一瞬间近乎悲伤。
陆沉:“那看来,只是他的后果有些不幸。”
说完,他平静下来,不再有多余的表情,我看着他,就好像在看一处无光的深渊。
Leo也是你的朋友。我想要这么说,却说不出来。
我们用回忆那些美好而轻快的岁月来粉饰太平,却有属于那段岁月的人,因为我们的错误再也不会归来。
陆沉没有再说话,转身离开,不知从何处传来,我听到了裂痕的声音。
长久以来努力维持的平衡终于破裂,可这一刻
我却十分平静,就像陆沉所表现出的那样。
我低头看向手里的那张讣告,它的一角已经发皱,似乎曾有人很用力地握着它,也是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忘了说一句话。
我忘了叫陆沉不要悲伤。
即便他说了那样不带感情的话,即便我已经学会不去信任他,可我仍旧认为,他很悲伤。
浑浑噩噩过了几天,某天晚上,我久违的做了一个梦。
梦里是太空葬场,在这漂游在太空中的寂静空间里,层层叠叠堆放着许多亡者的棺椁。
他们大都是为了人类的未来而牺牲的人,死前追寻着宇宙的星辰,死后才终于得以归向宇宙的怀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直到眼前的漆黑中亮起星点蓝光——是这里的机器人正在识别最新进入葬场的灵柩。
怀抱着某种已经预料到结局的恐惧,我看向那躺在透明玻璃罩下的人。
——是陆沉。
他穿着一身笔挺军装,紧闭着双眼,在失去了所有的生动声色后,那苍白沉寂的脸几乎要消融在周围的白色百合花里。
这幅画面经由屈光系统的折射聚焦在我的视网膜,当它们沿着视觉通路传递到我的大脑时,破碎成了空白的意义。
我茫然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几乎不能分辨现在攫住我心脏的,是痛楚、还是悲哀?
我听到了在宇宙深处突然奏响的寂静哀歌,几乎忘记了呼吸。
下意识地,我想要走近一些仔细看看他,可似乎有什么将我困在了原地,使我寸步难行。
于是我挣扎起来,也正是在这挣扎间,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沾满了鲜血
周围的一切开始倒塌,它们裂变成锋利的碎片
试图将我脑海中那些茫然的意义——剜去。
我只能在崩裂中奋力抬起头,最后一次看向那似乎预示着什么的场景。
终于,我还是睁开了眼。
日出时熹微的晨光笼罩了房间,我慢慢坐起身,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它们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睡衣的布料黏在后背,一旁设定好的机器人开始播报今日的事务提醒。
梦也是一种潜意识,可那个曾经耐心将潜意识解释给我的人,已经不在我的身边,我似乎也因此失去了解读这些意义的能力。
机械女声:“最后一项:“今日重要事务——参加Leo的葬礼。”
我回过神来,那封讣告上标注的时间就是今天。
于是我只能暂时抛却那个莫名的梦,匆匆换好黑色的服装,出门赶往教堂。
很快,我就抵达了教堂,在与leo的亲朋打过招呼后,我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是最靠右边的那一排。
今天来到这里的大都是预备学校的校友和老师
自从毕业后,我一直没有回过学校,也很久没有见过他们,没想到再次见面,却是这样的场合。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看了一圈四周。
满堂的白花、前来吊唁的人群,虽然科技飞速发展,但人们用来送别的仪式却仍未改变。
教堂的最中央,是Leo的黑白照片,用的是预备学校的毕业照,他的脸上满是对未来的期许和理想。
同学A:“他……陆沉怎么来了?”
同学B:“哼,注意点你的称呼,这可不是我们从前的同学了。现在,他是能大义灭亲的陆执行官。”
不远处传来一阵骚动,我抬头往争议的中心看去。
陆沉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胸前别着一朵白花面色平静无波,看起来并不哀伤。
人群窃窃私语,向他投去的目光里大都是畏惧或是不满。
一个穿着黑色裙子的女人挡在了陆沉身前,她直挺着脊背,抬头看着陆沉,声音颤抖,但一字一顿十分清晰。
Leo姐姐:“我没有邀请杀人凶手来参加我弟弟的葬礼。”
周围骤然安静了,只能听到教堂里哀哀流淌的音乐和人们极力控制的呼吸。
我认出,这位面色憔悴的女人是Leo的姐姐,姐
弟两人关系很好,听说她经常来学校看Leo。但我只见过她一次,是在学校食堂。
她做了两人份的便当送来,见到我时她有些抱歉,又和我约定好,下次见面会带上我的那份
那时候,她还与我们玩笑,请陆沉好好照顾自己这个没什么志向又过于自由的弟弟。
在她的阻拦下,陆沉停下了脚步。他不卑不亢地看向对方,然后微微低下头。
陆沉:“作为Leo的同窗,我理应过来吊唁。请您保重身体,Leo不会愿意见到您过于悲伤。”
听到这句话,Leo姐姐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Leo的其他亲属围上来。
一些人凑在她身边小声安慰,而另一些人则簇拥在陆沉身边,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不住给陆沉鞠躬道歉。
陆沉只是摇了摇头,离开了那里。
看着那些穿着一样的黑色丧服,却神色各异的人们,眼前的一切让人感到无比荒谬可笑。
风波很快过去,人们重新说起话来,有一个熟悉的脚步声十分清晰地、一下一下落在我的耳边。
我知道陆沉在往我这边靠近,但我执意低着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终于,那双黑色皮鞋进入了我的视野,停在了我身前。
陆沉:“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我:“我旁边没有位置了。”
陆沉:“没关系。”
他从旁边拿来一把椅子,放到了我旁边,坐下。
陆沉:“这样可以吗?”
呼吸间,昨夜一直缠绕梦中的苦艾香重新攫住了我的心脏,我只能抬头看向他。
在这样近的距离中,我才发现他眼下的青黑。
我没有办法说出拒绝的话,也没有办法对这样的他狠下心来,即便是在知道了那些事情之后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如果不能坚决地站在他的对立面,那我们的今后也许只是重蹈覆辙。
看着他的侧脸,我又想起了昨晚的那个梦。
我:“你昨天睡得好吗?”
陆沉:“还好,你呢?”
我:“我没有怎么休息好,做了个很长的梦,和你有关的。
他眸光一暗,像是已经预感到我要说些什么。
我:“我梦到你……不在了,躺在太空葬场的灵柩里,周围放着很多白色的百合花。”
我紧紧盯着陆沉,想要捕捉他脸上神情的任何一丝变化,而陆沉只是朝我露出又一个恰到好处的平和笑容。
陆沉:“听起来是种很平静的死亡。”
我:“就这样?你没有其他想说的吗?”
陆沉微微偏了头,看着我的眼睛,像是在仔细思考着。
陆沉:“那在梦里,你有为我的死掉眼泪吗?”
我一愣,下意识却又诚实地摇了摇头。
陆沉:“那就好。人总是会死的,没有必要感到悲伤。”
我:“你不在意死亡吗?”
陆沉:“嗯,不太在意。”
我:“既然不在意,那你今天又是为什么来这里?”
陆沉:“因为Leo是我的同窗好友,我理应过来吊唁。”
我:“我想听的,不是这个你已经使用过的答案。”
陆沉看着我,笑着抬起手,似乎是想要和以前一样摸摸我的头发,但最终还是把手慢慢放了回来。
陆沉:“我想来看看,被人造海水困住的牡蛎是否真的能创造出一片本不存在的、属于自己的海。”
我:“那你看到答案了吗?”
陆沉:“他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完整了自己的死亡。”
他看向周围前来吊唁的人。
教堂里的人不多,大部分都不知道Leo做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而死,而那些小部分知情的,也都战战兢兢,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陆沉:“但很可惜,最终他没能把这份意义具象出来。这是一场失败的牺牲。”
陆沉的语气很冷酷,现在我已经不再因此感觉到强烈的失望或者愤怒。
我:“我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和你坐在这里,点评一位朋友的死亡。”
陆沉:“你想到过什么?”
我:“我以为如果真的有朋友走在前面。我们会一边回忆着和他有关的往事,一边给彼此擦眼泪。尽管他不在了,但那些往事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陆沉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在想象那样的场景。
陆沉:“那样也不错。”
我:“陆沉,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样害死曾经的好友?
陆沉:“为什么?这个问题你问过很多次。为什么保守秘密,为什么不通过那些提案。我想我已经回答过你了。”
我:“这次不一样。”
陆沉:“哪里不一样。”
我:“以前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出自你的意志或是双手,你只是知道而已。”
陆沉:“知道了,然后认同了,与做了没有差别。与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也没有差别。
也许你会觉得残酷,但对于任何意义的追寻和斗争,牺牲是必然的。”
我:“当这个意义是践行中央塔的意志时,也是如此吗?”
陆沉垂下眼,太阳已经开始西沉,稍长的睫羽遮去了所有路径,周围的光不再落在他眼里。
陆沉:“尤其如此。它需要的是更为庞大的牺牲。一直以来我都这样想,未来的许多年,应该也不会改变。”
原来是这样。居然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我放在膝上一直紧握的双手慢慢松开,这双手早就该松开了,在梦中的葬场,在黄昏的露台……在所有故事启幕的起点。
远处的晚钟敲响了广阔的回声,我想我已经得到了最后的答案。
—我和陆沉已经,或者说一直以来,我们走上的都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道路,不论我如何犹豫迟疑,我们还是要分道扬镳。
我朝他笑,可嘴角扬起的时候,又有眼泪忍不住掉出来。
就像那个夜晚在露台上一样,陆沉抬起手,为我轻轻拭去了那些眼泪。
陆沉:“至少你的想象,我们实现了一半。”
我:“嗯。”
哀痛的音乐仍在流淌,葬礼来到了献花的环节,黑色的人群站起,在泪水中向台前涌去。
很快,轮到了我和陆沉。我在照片前放下一枝白色的花,陆沉则放下一枚预备学校的校徽。
牧师念起祈福送别的祷文,夕阳的光被撕扯着拉长,铺满教堂的地面,又攀爬上那一簇簇洁白花丛,落在了那枚校徽上。
我站在人群里,最后一次想起了从前的片段。
那也是个黄昏,我和陆沉并肩坐在图书馆门口那高而长的阶梯尽头,轻声念着一首和黄昏有关的诗句。
我几乎要忘记手里的书上写着的是什么,但我记得,那天是很幸福很圆满的一天。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葬礼结束了,夕阳也几乎快要完全落下去了。
人们慢慢往那扇彩色玻璃的教堂大门走去,我和陆沉也跟在后面。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我原本想默默离开,但还没走出一步,陆沉就喊住了我。
陆沉:“要送你回去吗?
我:“我……”
犹豫中,我看到了远山,最后一抹光恰好落进群山身后,世界变成泛紫的暮色。
忽然,我想起了那首诗的内容。
我/陆沉:“我们甚至也失去了黄昏的颜色。”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我不由自主地看向陆沉,也正好对上了他的目光。
几百年前的诗句,几亿年前的牡蛎,我们之间的东西怎么总是那么古老。
如果我们真的在几百年前相遇,我们是不是就能够——
陆沉的眼中映出我的影子,是如今的我,也是十几岁时的我。
晚风吹动假的树林,枝叶在无序中相撞,我又听到了那曾经铺天盖地而来的心跳。
为什么当我哀伤且感觉到你远离时,全部的爱会突如其然地来临呢?
但我还是摇了摇头,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算啦。太阳落山了,我们也应该告别了。”
陆沉:“但太阳也会再次升起。”
他想说的,大概是我们会再次重逢。
我们确实会重逢,只是那时候,就要以对立的身份相见了。
在逐渐退去的心跳声里,我想至少留下一个像从前一样愉快完满的结尾。
我没有反驳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这不是当然的嘛,明天见。”
陆沉:“明天见。”
与陆沉有关的过往,埋藏在我的心脏、奔涌在我的血管,它们曾经撕扯着我,叫嚣着不舍和软弱的爱意。
现在,它们都不见了。
它们酝酿了一场风暴,又在平静中消亡,而那些回忆里的陆沉,那些基于过去、又从我的想象中诞生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