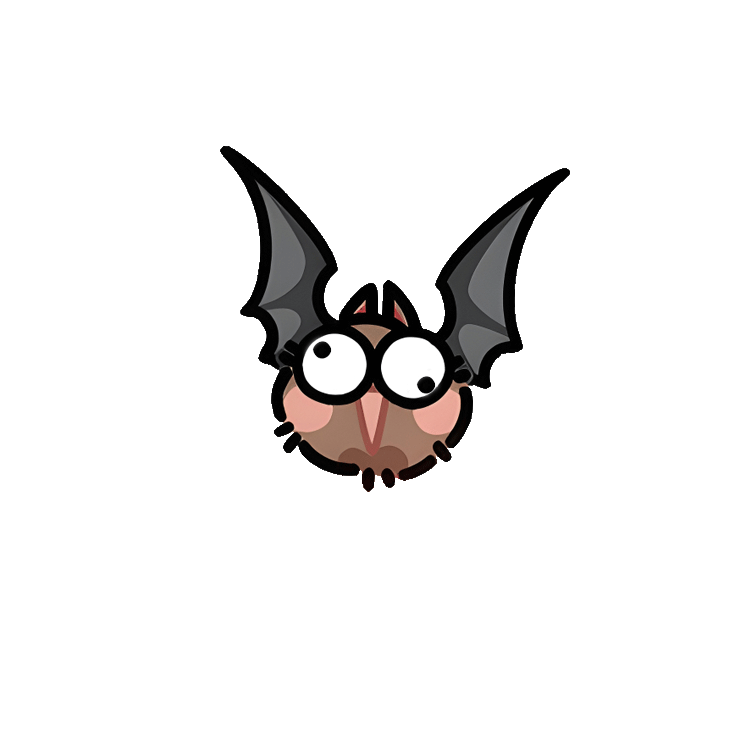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审判❈
Leo的葬礼结束后,时间行进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
新元44年伊始,新旧年的交接夜,大家聚集在中央塔前的广场上,新年钟声敲响,掀起人群中热切的欢呼声。
在这充满期待的氛围里,我远远地看到了陆沉他也用目光找到了我,嘴唇开合,口型依稀是“新年快乐”。
新元44年7月,我接受秘书处的邀请,成为了新一任的秘书长。陆沉出席了任职会议,他恭喜我升迁,也祝我前程似锦。
新元44年11月,全球气温断崖式下跌,地球迎来了新纪元以来最寒冷的冬天。
同年12月,陆沉在贵族以及安理会的拥护下,以压倒性优势成为HSA最高执行官。
会后,我将那句恭喜还给了他,他没有回答,只是在冷风里解开了自己的围巾,放到我手里新元45年3月。
Leo的父亲——同时也是HSA的前情报科主任实名发表了关于中央塔对现存人类实施电子监听计划的详细陈述和相关证据。
世界各地因此产生了不同规模的动荡和冲突
中央塔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还是不够。
在这场可以预料到的混乱里,我去了一趟Leo的墓地,却在那里意外见到了此时身处风暴中心的陆沉。
我没有上去打招呼。这一次他也没有注意到我,只是站在墓碑前,沉默地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那之后不久,中央塔方面发表了正式声明,电子监听计划被列为谣言,Leo的父亲也被列入抓捕名单。
新元45年5月,由秘书处主持的,历时9个月的针对Kepler计划的调查结束,结果显示,产生变异体的污染源来自IFF的实验。
趁此机会,秘书处首次弹劾陆沉,同时要求中央塔公开相关文件,而在几次会议中,陆沉均未提出反对意见,只是保持缄默。
中央塔开启了对最高执行官陆沉的审查程序,
但得到的结果并不如人意,弹劾无疾而终。
然而,此后陆沉并未对秘书处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偶尔几个瞬间,我会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
陆沉似乎并不反对这次弹劾,他只是在反对这次弹劾发起的时机和方式。
当然,这个臆测没有根据,它更像是我仍旧懦弱的证明,于是我保留了这个怀疑,并且将它当作时刻警示自己的工具。
新元45年9月,陆沉在演讲中遭到袭击,我去了医疗中心,但他在睡。
我没有久留,最后只是以预备学校的名义送去了鲜花,希望他早日康复。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看望他。
新元45年12月,秘书处收集到周密的证据,针对包括电子监听计划在内,一系列由陆沉决策的、违反了人类基本公约的行动。
秘书处决定在月内正式向军事法庭提出公诉,陆沉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些行动,并未作出反应
但又一次,我有种直觉,陆沉一直知道我在做什么、想要做到什么,而我也知道他在做什么、想要做到什么。
我们像是坐在show hand的牌桌前,在玩一个明牌的游戏。只是可惜,这场游戏的赌注是人类未来的命运,我无法享受与他的胜负。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想法错得有多么离谱。陆沉确实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却并不完全知道他的谋划。
但此时此刻,我走到了这一步,不论如何,我只能把事情推进下去。
在诸多的证据中,有一项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预备学校的战略模拟器。
工程师在虚拟世界里发现了一段奇怪的代码,用于生成被称为暗区的特殊场景,对学生行为产生诱导并记录其反应。
经过初步判定,战略模拟器是中央塔测试学生服从性的工具,需要被批量销毁。
在销毁前,我想再去看看。于是时隔4年,我又回到了母校。
这里还和从前一样,没有变化。我来到战略模拟教室。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陆沉。
那身军装严丝合缝地包裹着他,在教室的灯光下,他的身躯像是一道笔直而锋利的阴影。
他正站在教室后的毕业生照片墙前,似乎在看着上面一个个曾经年轻的面孔。
我记得,我和他的照片,也挂在上面。
我的脚步有些犹豫,他注意到了我,转头朝我看来。
我们默契地坐在机器前。
我:“来了很久吗?”
陆沉:“没有。你进来的时候,我也刚刚到。”
我:“骗人。”
我摸了摸他放在桌上的咖啡,是冷掉的。
我:“毕业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回学校。你呢?”
陆沉:“第二次。”
陆沉看着窗外,像是陷入了回忆。
陆沉:“上一次,应该是41年的秋天。”
41年的秋天……是我毕业的时候。我装作不在意,试探地问。
我:“都回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陆沉:“只是出席一场科创生态的研讨会,来去都很匆忙。”
我:“原来是这样。我记得那个研讨会年年都办,年年都请你。但你好像一直在忙中央塔的事务,所以每次邀请都会被你婉拒。
不过,其实每一年,我都很希望你能来。”
陆沉:“是吗,这件事我没有听你说过。”
我:“那时候我给你说了,你就会来吗?大概也不会吧。”
陆沉:“嗯,大概也不会。”
我和陆沉对上了视线,两人一时无话,我无意纠结于此,换了话题。
我:“再回来看看也不错,工作了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说怀念在学校的日子。”
打开战略模拟器,在初始页面上,仍留有积分排行榜,上面已经有新的名字刷新了纪录,我和陆沉早就不是第一和第二了。
我:“要不要来比赛?”
陆沉点了点头,和从前一样,我们一起进入了模拟器的虚拟空间。
也与从前一样,在追逐和战斗中,我们来到了海边的港口。
厚重的云层堆在与海交际的天边,光线阴沉而凝滞,充满着一种山雨欲来的预示。
曾经,我在这里进入暗区,接触到了那些被掩埋的真相,是陆沉将我从幻境中解救出来,并引导我走上了今天的道路。
而现在,我却拿着枪,把陆沉逼到了绝境。
我:“看来你退步啦。”
陆沉:“是你进步了。”
黑洞洞的枪口指向眼前的陆沉,模拟器里的他穿着校服,海风呼啸着掠过他的额发,露出那双暗红色的眼睛。
陆沉:“怎么不结束?”
我:“我在想,很多事情是不是和游戏一样不止一种解法。”
陆沉:“但是现在,你唯一的解法,就是打败我。否则,就是同归于尽。”
我:“是你告诉我的,要打败的不是你,而是这个游戏本身。除了决出胜负,我还有别的选择。
我马上可以销毁掉这个模拟器,投影会显示Game Over,Evan和我之间没有输赢。”
陆沉:“或许我应该说得更明白一点。现在我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销毁它,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项。”
他好整以暇地看着我,像是在挑衅,又像是在旁观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决定。
我:“你不是。”
陆沉:“我为什么不是?”
这是陆沉喜欢的说话方式,我也喜欢听他这样说话,迷雾里藏着一个崭新的世界,等待我去探寻。
但今天不行,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谈话。
我:“你应该很早就知道。战略模拟器里的暗区,是中央塔用来测试学生忠诚度的工具吧?”
陆沉:“知道,那又怎么样?”
我:“那时候,外婆在诱导我,如果你没出现,我可能没办法通过考验。就像中央塔的入职测试一样。亲自把一个反对派招到身边,甚至带着她、帮助她走到了现在,你是不是很后悔?”
陆沉:“不。”
我:“为什么?”
陆沉:“因为那时,我对你抱有幻想。”
错觉一样的,陆沉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深邃而热烈,连带着他说的幻想都带上了别的含义,就比如……沉默的爱恋,寂静的倾慕。
在这样的眼神里,我几乎无法动作,再开口时声音都跟着颤抖。
我:“你说的幻想——”
陆沉:“是个玩笑。我还以为秘书长会更有幽默感一些。”
说着,他轻巧地收敛了神色,只在嘴角留下一个冰冷的笑容。
陆沉:“我只是相信,与民众不同,在中央塔工作的人需要一定的自由意志来发挥其能力。仅此而已。
如果你想用它来证明什么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无论是对我以秘书长相称,还是评论民众的口吻,眼前的陆沉让我本能地感到不舒服。”
我闭了闭眼,退出了模拟器的虚拟空间,陆沉也跟着我离开了那里。
然后我从口袋里拿出随身携带的通讯器,默默地把它放在桌上,关闭了它。
我:“来这里之前,我已经把学校里所有的通讯设备关闭了,这是最后一件。
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对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聊聊天了。”
陆沉看了我片刻,表情有些许松动。
陆沉:“即便聊再多次,我也给不了你期待的答案。”
我没有反驳,只是看向远处,有许多证据,只有与陆沉共事多时的我才能够确证真假。
我:“就算放我的水不算什么,那么诺亚伤员的慰问礼金呢。在我结束走访诺亚伤员的工作后,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感谢信。
上面说,感谢我送来的慰问礼金。起初我很奇怪,以为是寄错了。直到这段时间着手调查才发现,这笔钱的发起人是你。
发起的用途虽然借用了其他名目,但最终,这笔钱还是到了诺亚伤员手里。那这个呢,能够作为你并不是这个游戏,也并不是中央塔一部分的证据吗?”
陆沉:“你似乎搞错了什么。中央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获得许可的上层阶级离开地球。
我所做的这些事也一慰问也好,资助也好,不过是担心高压政策下会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在陆沉口中确凿无误地听到这些。
我:“陆沉!”
陆沉:“我在。”
他坦荡地看着我,脸上的神情似乎在告诉我他刚才说的并无半句谎话。
模拟器上跳出了销毁程序的提醒界面,留给我和陆沉自由交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陆沉,我们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很快会向军事法庭提起对你的诉讼。
法庭……现在与秘书处站在一起。你不会有时间去周旋操作,也不会再有转圜的余地了。”
我越说越快,也说得有点混乱,那么长时间的磨练,我在这个人的面前,仍会这样。
我:“但是、但是如果你愿意主动供认并揭发一部分其他内容——我知道,有很多事情实际上并不是出于你的意志,而是你家族还有贵族的决定。”
所以,如果你能够指认他们,军事法庭会对你从轻判罚。甚至未来,你还能留在中央塔继续工作.
陆沉看着我,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幼稚又偏要孤注一掷的小动物。
然后他轻轻笑了起来。
陆沉:“这是秘书长的最后通牒吗,请恕我拒绝。”
我:“这不是通牒,而是事实,再这样下去——”
陆沉:“最终我会得到终身监禁,或者死刑。但现在还不到最终,所以,恕我拒绝。”
陆沉俯身帮我按下了模拟器的按钮,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瞪视他,而他不为所动。
陆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将我供认罪行以及未来留在中央塔工作,作为赦免我的唯一条件吗?”
我:“我……”
当然是了,我想这么说,毕竟即使很多事情不是你做的,也是你给予了他们行动的权力和可能。
更重要的是,为了推翻现今的统治、建立新的秩序,陆沉必须亲口供认罪行。
但是随即,我可怕地意识到,并不是的。哪怕陆沉拒绝,也许,不,是一定……我一定仍旧想要保住他。
我肯定不知怎的泄露了真实的想法,有一瞬间,陆沉眼中出现了悲伤的神情。
陆沉:“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做。”
销毁程序的进度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70%。
陆沉将一把枪放在桌上,我条件反射地向腰间看去——是我的配枪,不知什么时候被他拿去了。
我:“……这是我的枪。”
陆沉低头摩挲着银白的枪身,从枪管、扳机到握把。他再次看向我时,眼睛微微弯着。
陆沉:“你带着枪来见我,我很高兴。但下次要保管好它,别再轻易被人拿走。”
说完,陆沉将枪交还到了我的手上。
销毁程序的进度走到了尽头,战略模拟器被彻底摧毁了。
灯光下,他的轮廓变得很暗,大门渐渐合上,而他也彻底被埋进暗影里。
那之后,我和陆沉再也没有见面,他也许通过我给出的信息,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也许没有。
无论如何,秘书处针对陆沉的行动迅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提交资料后的第七天,检察中心对陆沉发布了限制令。
陆沉的经济、政治、社会活动都被暂停,安理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需要接受问询,中央塔日常事务交由秘书处暂理。
半个月后,检察中心正式对陆沉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逮捕。
在陆沉等待审查期间,我多次要求与他会面,但一直遭到拒绝。
这场调查延续了整个冬天,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的那天,已经是春分。
在审判前夕,我突然接到消息,陆沉想要见我。
于是我来到了中央塔的禁闭室。
这里通常被用来关押特殊的犯人,完全密闭,除了一个需要手动打开的窗口,从外面并不能窥见里面的情形。
警卫按规定搜查了我的身体、检查了我的配枪
确认无误后,他打开了陆沉所在房间的门。陆沉坐在房间中央,手脚都有电子的镣铐。
他脱去了那身沉重的军装,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衣,戴着黑框眼镜,有些消瘦下去。
我在他对面轻轻坐下。
陆沉:“好久不见。”
我:“好久不见。”
说完这句话,我们像是心有灵犀般,一起沉默了片刻。
我忽然想到,如果……或许这是我和陆沉最后一次自由的聊天了,复杂的酸涩堵住我的喉咙,而我只能努力把它们咽下。
我:“之前好几次想来看看你,不过你都没同意。这次叫我过来,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
陆沉:“没有重要的事,就不能见面了吗?”
我没想到陆沉会这么回答,微微一愣。
我:“这也是个玩笑吗?”
陆沉:“是。”
陆沉笑了笑,抬起手指了指门牌。
陆沉:“想让你看一看这里一一对你而言,我想这件事应该很重要。”
我顺着陆沉的目光打量着这间房间,可除了周围那灰白的墙壁,这里什么都没有。
被冰冷金属框出的四方天地,是这个宇宙里最狭窄又最广阔的放逐的荒野。
陆沉:“3321,你的外婆,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嗯。多谢你告诉我。”
酸楚迟了几秒才漫上来,我才发现外婆竟离我已经那么遥远,她怀抱着理想离开了,看到如今的我,会说些什么?
感到满意吗,还是痛斥我深陷于政治的漩涡?
陆沉温和地看着我,仿佛看透了我的思绪。
陆沉:“我想在她离开前,应该很挂念你。在这间空荡荡的禁闭室里,需要不断想起重要的人,才能让自己维持清醒。”
我:“那你呢……是在想谁,还是已经不需要维持清醒?”
我没有期望听到他的回答,陆沉也果然没有作答。
陆沉:“时间充裕的话,有没有兴趣听我说一个故事。”
我:“不着急,来这里之前,我已经把今天的工作全部推掉了。”
陆沉笑了笑,抬起手似乎想做些什么,可手腕间的镣铐阻止了他的动作。
他把手收了回去,抚过自己衬衫上的纽扣还有褶皱。
陆沉:“最近,我时常梦到过去的事,偶尔会想起小时候过生日,父亲总将礼物提前放在我床边。
在众多礼物中,我最喜欢的是一架空间望远镜。也是收到它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真正抬头仰望宇宙。”
陆沉微微仰起头,他的目光落在苍白的天花板上,可又似乎越过了那片限制,投向了更远处的广袤天地。
陆沉:“当所有星星排成一线——一条10万光年的银河汇聚在眼前。6000颗星星肉眼可见,20多个星座分布在暗黑天际。夜空除了银河的光源,再无其它把世界撑亮。从那以后,我迷上了观星。”
是啊,从前在预备学校的时候,陆沉经常去天文台。而我在陆沉的影响下,也渐渐喜欢上了这项活动。
那真是一段很好的时候,我不自觉地这样想着也不自觉地背弃了自己心里再也不去追忆过往的诺言。
我:“我第一次观星,也是你带我去的。”
那是——那是多久以前了?我只记得是一个无人的深夜,陆沉带着我走进天文台,四周静悄悄的,而我们并肩躺在地上。
天文台穹顶的玻璃是最好的观影仪,透过它,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真实夜幕上的每一颗星星或者说,几乎每一颗星星。
那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全部的世界都是为我们而来,即便是无垠的宇宙,也会在造物主轻轻的叹息里,一分不差地落入我们的眼睛。
而那刻耳畔陆沉的声息,也同宇宙的频率融合在一起,牵引着我的心跳。
我:“那个时候你还对我说,这样辽远的天幕中,一定会有人类的新家园。”
陆沉:“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说过。”
陆沉:“是吗,我已经忘了。不过我想,这就是Kepler计划成立的初衷。”
提到Kepler计划,我的思绪又被拉回到现在。
陆沉:“为了这个美好的期待,一代又一代人在漫长的探索中默然消亡。宇宙是如此宏大,以至于我们所能触及的,不过是时间维度上的微弱尘埃。
计划推进了很久,却始终没能有所收获。直到在你外婆的带领下,探索进程终于出现了转机。”
我:“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被我打断了,陆沉只是微微停顿片刻,依旧继续说了下去。
就像这房间里还有其他不明真相的听众,陆沉的故事,似乎不只是说给我听。
陆沉:“新纪元初,她带领的小队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该星球处于“适居带”,与地球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了勘探行动,通过无人飞船采集了部分样本运回地球。IFF作为中央塔首屈一指的科研机构,垄断了样本的研究权。”
我:“陆沉,别说了,这些我都——
陆沉:“听我说完。”
陆沉平静地打断了我。
他的面色没有波动,就仿佛他并不知道此刻正在说出的一切,外婆的死、谎言,对我而言是一场已经反复无数遍的凌迟。
陆沉:“实验过程中,样本遭到了污染,意外泄露到地表。而地表求生的人类,只能全盘接受这个荒谬的“成果”。
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变异体就这样诞生了。中央塔为了掩盖IFF的失误,为了维持公民的忠诚。选择将错误归咎于Kepler计划,将其取缔。”
我看着眼前的陆沉,心中满是茫然和痛苦,但除此之外,仍有清明的念头从脑海中划过。
他为什么又要将这些惨痛的过去再重复一遍。他在期待我做出怎样的反应?他又要借此达到什么目的?
我深深呼吸着,强迫自己压下心中的感受,我的目的不是更多的疑惑,而是眼前的这个人。
我:“可是陆沉,你看,探索宇宙的路,永远不会有停下的一天。尽管你忘了,但那时候你对我说的话,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
仿佛是我的话让他有所动摇,陆沉偏开目光,低头思考了一会,最终赞同地点了点头。
他的认可几乎让我高兴了起来。
陆沉:“所以,计划秘密重启了。在Leo的坚持下,他们对这颗类地行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探索。勘探显示,在距离地球50光年外,也有绵长的河流和高耸的山岩。”
这是关于重启后的Kepler计划,我从未听闻的信息,笑意凝固在脸上。我听到自己的心跳逐渐加快、加快——
我:“也就是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家园?”
陆沉:“也是踏上远航的诸位精英,未来将要抵达的终点站。”
话音落下时,陆沉抬起了头,以一种近乎倨傲的目光看向我。
陆沉:“这是最优解。按照目前的生产资源无法支持全人类离开。”
我确信了,这绝对不是我认识的陆沉会说出来的话。
太多的事实、暗示和预感……纷乱的头绪缠绕在我心里,我无望地思考着,最终只能凭借本能追问我最关心的问题。
我:“你见过那些照片,对吗?”
陆沉:“哪些?”
我:“山川、河流、岩土。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想到第一次仰望星空的那个夜晚?”
陆沉:“不,我没有。”
陆沉淡淡地看着我,对我、对我们,宣告了最后的审判。我没想过。我想到的是中央塔外那些没有资格延续文明的普通人,不应该享用这些。
陆沉:“如果这个回答伤害到了你,我只能说抱歉。”
陆沉从来没有像这样,激烈而尖锐地表达过什么。
从谈话开始,他一直很温和平静,让我错觉这次谈话也许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久违的,我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仿佛有无数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明明在这个房间里,只有我们面对面坐着,没有其他人。
一声扯断丝线的轻响,陆沉拿下了他刚刚抚过的、衬衫的第一颗钮扣。
这时我才看清,那是一枚小小的引爆器。他摩挲着它。
陆沉:“并且我想,作为普通人,是没有机会了解命运全貌的。按下这枚按钮的下一秒,Kepler计划就会变成一段历史,几个音节组成的文字。这个世界上,只会存在一个知道坐标的人。”
我很清楚,如果他按下引爆键,外婆、Leo、那些为了Kepler计划牺牲的人们,他们想要带全人类离开地球的愿望,都会化为泡影。
而且,如果只剩下陆沉知道坐标,那我只能放了他,让他重新主导中央塔。
我的理智已经做出了决定,可我的心却仍在迟疑。
我咬牙看着陆沉,他等待我的反应。我们谁都不愿意退后,这是一场漫长的、无声的拉锯。最终,我在这场对峙中败下阵来。
我掏出了腰间的配枪,指向陆沉。
而陆沉只偏过目光看了一眼黑洞洞的枪口,就重新望向了我的眼睛。
他看着我,露出了这次谈话中,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
陆沉:“这样对峙的时刻,我设想过很多次。只是没想到,站在我对面的那个人,会是你。”
我:“我想终结的,只是这场不公平的游戏。”
然后,就算你在里面、就算你已经成为游戏的一部分,我也会把你拉出来。
我没把这句话说出口。
这是我瞒着所有人,包括陆沉和秘书处做出的决定。因此在一切完成前,我不能告诉任何人,不能容许任何人破坏它。
我已经安排好了,通过我积攒的所有东西,人脉、渠道、威逼和利诱,我不会让陆沉被审判死刑,他会活着等到三个月后我的保释。
而在那之后,就算他仍旧固执己见,我也会有很多时间,说服他改变观点。
只要他活着。
我握紧枪,手心有些出汗,心情却意外地平静下来。
这时,陆沉的眼神柔软了下来,他做了一个嘴型。
那个嘴型的样子似乎在说:这样很好。
随后,他放在引爆键上的指尖微微屈起——他准备按下引爆键。
我转过枪口,对准了陆沉的胳膊。
无端地,我想到了陆沉第一次教我开枪的画面。他的手覆在我的手上,呼吸落在我的耳边。
他说,扣动扳机时,要用指节,而不是指尖力量。
在他的声音里,我扣下了扳机。
枪声破开空气,子弹穿透血肉,陆沉的胸口出现了一个黑洞。
他倒在地上。
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
我看到他倒地前露出的微笑、看到他的身躯砸在地上时溅起的尘埃、看到他的胸口涌出鲜血。
看到死亡的阴翳正一点一点爬上他的眼睛。而他仍旧笑着看我,告诉我,这样很好。
我:“为…….为什么会这样……陆沉……?”
我叫他,但已无回音。
外面一阵骚动,大门打开,我看到了许多的警卫、医生……许多人涌进了房间。他们一拥而上,围在陆沉身边,将他的面容淹没。
我浑身冰冷,站在原地,好似时间也已经停滞。
??:“ 小姐。”
我转头看见警卫脱下面具,露出了周严的脸,他是我走后,陆沉的秘书。
他捡起我的配枪,交到我手里。
周严:“节哀。”
我看着他,又去看房间外墙上的屏幕,上面应该写着日期,此刻还在播放着什么画面。
可我眼前迷蒙一片,除了画面上苍白的墙壁已经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但我记得、我记得在出门前看了一眼日历,今天的日期上被我画了一颗星星,而那上面的数字是……1月22日。
所以你选择了在今天和我见面。是吗,陆沉?
接下来的许多天,宛如梦境。
狱中发生的一切,都通过连接全球网络的监控被直播了出去,大概是陆沉授意周严做的。
也是这场直播,划定了中央塔最后的结局。
陆沉亲口说的故事,使民众清楚地知晓中央塔的阴谋和Kepler计划的真相,任何势力都无法再对其加以任何矫饰。
民众们相信我是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新未来的那个人,因为我只为大义,对曾经的上级、校友也是好友,拔枪相向。
陆沉在当政期间没有提拔任何家族成员,安理会和陆氏家族也因为陆沉的死亡一蹶不振。
秘书处取代安理会成为了中央塔新的掌权者,
我知道,不久后,我将被推选为新任执行官。作为罪人,陆沉的葬礼也只是草草了事。
葬礼结束后,我收到了配枪的送检报告。这时恰好,又是一个黄昏。
借着夕阳的光,我打开了那份报告,报告显示,我的枪支被植入了不常见的程序,用声纹选择目标,瞄准胸口,务求一击致命。
陆沉:“你带着枪来见我,我很高兴。但下次要保管好它,别再轻易被人拿走。”
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又或者不是那个时候,是更早……
一步步走到了我的对立面,又在暗中不动声色地为我清扫了所有的阻碍,让我在众人的信任中走向权力的巅峰。
他甚至把自己的死亡也算作其中一环。
此时已是深春,人造的树林按照时令设定呈现出葱郁的绿色,在夕阳余晖的包裹下,这末日中的世间万物竟然充满了欣欣向荣的生机。我忽然很想他。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他。
E,陆学长,最年轻的执政官,他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走动,每一个笑意,我都想了很多遍。
我唯独不去想陆沉,不去想这个死去的名字。
终于,在太阳落下去之前,我走进了陆沉的办公室。
我迟迟没有搬入这里,只是让人锁上门,不要动里面的东西。
因此,房间里的陈设和从前一样——放满了珍贵纸质书的高大书架、柔软的供人小憩的沙发一张宽阔整洁的书桌。
桌上放着几本书、一摞文件、一支钢笔、一盏台灯,还有一个花瓶。
花瓶里没有鲜花。
我在椅子上轻轻坐下,想象着陆沉从前坐在书桌前低头批阅文件的模样。
他是不是就在这个座位上,独自一人为自己谋划了最后的死亡?
忽然之间,麻木的心像是刀绞一样的疼。
明明我也用尽了全力。
明明我也在纸上计算了千万遍他活下来的可能。
明明他也对我的营救计划毫不知情。
如果再给我一些时间、如果我开始得再早一些——
这也许会是我唯一胜过他的地方,到那时我会笑着调侃他,要他夸我进步了许多。
但是太迟了。这一切都太迟了,从数年前起,从我们遇到而又分离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太迟。
我在陆沉坐过的位置上呆了很久,直到西沉的落日光线逐渐铺满这间房间。
琥珀色的光线落在我的身上,带着些微暖意,像是谁半环着我,给了我最后一个拥抱。
我痛得没有力气,趴在办公桌上。
终于,如我这几个月来一直暗自祈求的那样我梦到了陆沉。
那是七年前,那个我曾错过的,陆沉的毕业典礼。
陆沉:“不要难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哪一天?”
陆沉:“等到玫瑰再次盛开的那天。”
说完,他凑近了我,最后的尾音含混着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线,消融在我们互相交错的呼吸里。
我似乎真的闻到了他身上的苦艾香,在这温柔又冷冽的气味里,我睁开眼。
太阳彻底落下,眼前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冷白色的拟造月光。
说完,他凑近了我,最后的尾音含混着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线,消融在我们互相交错的呼吸里
我似乎真的闻到了他身上的苦艾香,在这温柔又冷冽的气味里,我睁开眼。
太阳彻底落下,眼前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冷白色的拟造月光。
但那股香味却没有消散,隐约中,我看到了桌上空荡荡的花瓶里,盛开了一朵蓝色的玫瑰。
那一朵,正是陆沉毕业的时候,我送的花。
它将永远盛开着——在一切终结之后,在我与他重逢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