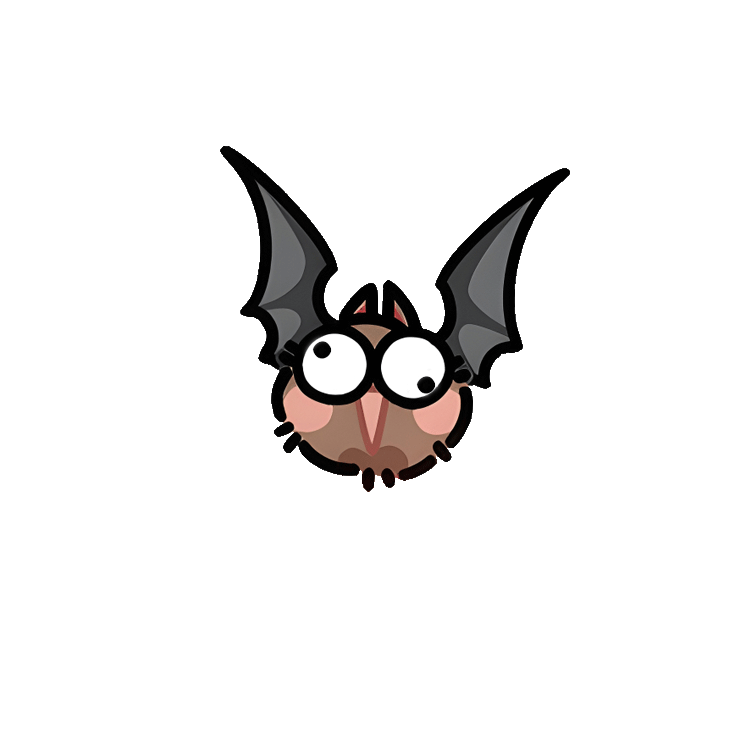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新元46年-初夏❈
我所见过最丑陋的东西,是一个鱼鳍般的胸腔。
属于人类的皮肤被无限制地撑起,直到纹路不再可见,微薄得能透过中央塔顶昼夜不息的灯光。机械装置从里面破出,延展开来,湿漉漉的,遍布鳞一样的亮斑。但那不是血,只是一些组织液。创口被精密地设计过,这是HSA的工作,一如它精密地让那对鱼鳍卷起狂风,承托着我。
我本不必要见到那东西,至少,本不必要在我的身上见到它,只要我未曾在那一次跳伞运动中于半空割断伞绳。但我又理应要坠落,要见到它,也理应在我的身上见到它,不是为了迎接死亡,只是唯有如此,才能再一次证明我的判断并无差错——这世间没有第二条路。
我不知道为何要大费周折,一遍遍验证已然赤裸的事实,也许是因为在那场关于意义的谈话中,我也有了潮汐的涌动。
流亡空间站的准入资格,中央塔最高层的席位,从获得它们的那一刻起,我不再拥有自由意志下的死亡。他们,他们为我植入的这对鱼鳍,甚至于民众,不会让我死去。
即便我不幸又不慎地坠落大地,变成早已干涸的海床上一滩看不出形状的血肉,他们也会用冷库中的血样和细胞,本应用于月球计划的建材,以及更多的言论控制,让“陆沉”重返人间
他将与我说同样的话,传达同样的意志,做同样的事。几乎同样的事。除了摆起笑脸,为一个在病床边抽泣的女孩擦去眼泪,期待她的厌憎,又暗叹她的软弱,虚伪至此。
我在医疗中心住了很长一段日子,最初拖着胸前破袋一样的皮肤,后来那块皮肤被切除了,留下淤黑的伤口。我没有掩藏这丑陋的形貌,而她每天都来。我们用它开了很多玩笑。
她说这是一个会泄露心声的洞窟,并煞有介事地将其中泄露的内容一一说了出来,每一条我都认可,每一次认可都让她更加欢欣。直到她问,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她,对吗,直到我仍旧微笑着认可了她,这个游戏才戛然而止。大部分时间里,我只是远远看着她。
在学校蔓延不绝的草坪上,在中央塔冰冷坚硬的窗边,也在被切割成无数方块的全息投影里。她时常抬起头,每一次抬头的时候,我的胸腔似乎都能感知到。那双眼睛很透明,好像所有不幸与灾难都能从中穿过。
我在她面前,总是平静的,几乎分不清这是计划的一部分,还是,因为她默然的注视,才有了寂静的银河。然后某一天,那道目光化为脐带,连入无数人的鱼鳍,而我也坦然露出胸膛向她走去,相信那便是人类的未来。
我记不得那晚的开始,也记不得那一句话是真实的,还是谎言,也许它曾是真实的,也许它将是谎言,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我仍记得那晚的结束,她站在门边,祝我早日康复。我们都挣扎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里,她无法从黑洞里读到任何东西,否则便会明白,它是一种侵吞了太多的沉疴,就连伤口里落下的纱线上,也沾附着呜咽的声音。
那声音断断续续,是宴会上推杯换盏的谈笑,是抓捕时求地无门的呼救,也是新闻里虚构出的激昂宣言。我听了很久,从里面分辨Leo的叹息,带着些许颤抖,哼着模糊的曲调,就像是他在课题上遇到难处时那样。
最后一根线,它不肯脱落,我感到难以忍耐的痒,用手去拽,拽出一连串欢声笑语,那是个少年,初出校园,仍以为中央塔的污垢能够被涤荡,也仍以为他在那里的意义结束之后,便可以再次找到她,两人在对方的眼眸中与业已凋落的玫瑰重逢。
笑声停止的时候,一切的声音也停止。我在一片寂静中想起一场应当发生的对峙和一把万无一失的枪,它们早被准备好了。
筹谋一场无法被证伪的死亡,究竟需要多久?一年、两年、十年抑或为之付诸一生?无论如何,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没有准备好的东西,我为之肆意延宕的东西,一直以来都仅仅与她有关。
如果她将打碎夜色视为痛苦的来源呢?但天幕已经很深很深。她许久没有向我诉说她的生活,离开葬礼时只留下单薄的背影,在会议上发言,眼底的余光也不再笼罩我的阴翳。我应该安心,她会把枪拿得很稳,就像当初我握住她的手那样。
但如果……她在硕大无朋的黑洞中迷失了自己的意义,如果我的选择最终是错的,她没有成为新的秩序,如果她也拥有了与我一样的胸腔一一我想象着那个画面。
她的胸口长出一双淡红的鱼鳍,柔软的身躯游弋在天空、森林、干涸的河床,甚至无垠的星空,地球上也许还有人,也许已是一片荒芜。她生动地活着,丝毫也不丑陋,美丽一如往昔。
我睁开眼,我的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