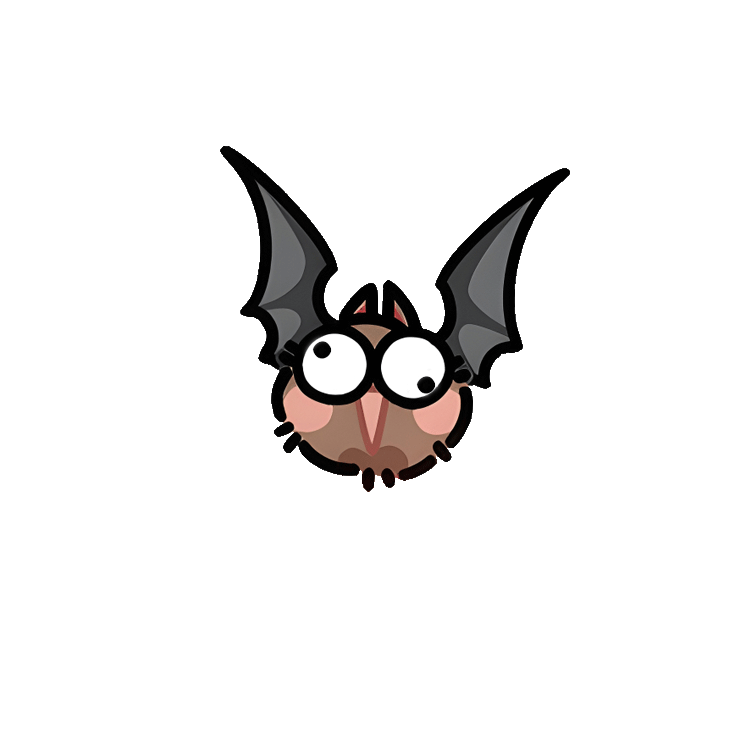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洁净世界Ⅰ❈
不远处的钟声敲响第四下时,神圣裁决所的审判庭上,陆沉也恰好念完了手里的裁决结果。
手上握着数百性命,却因为未成年身份与绝对豁免权的双重保障而逃过一劫的加害人表情平静,甚至隐隐带笑,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而痛失亲朋好友爱人的被害者家属伤心欲绝,他们看着陆沉,声泪俱下地抗议,要求申请再决。但陆沉只是摇了摇头。
陆沉:“抱歉,本次裁决为终局裁决。后续将不再接受任何再决申请。”
第五声钟响,陆沉手里的木锤也跟着落了下去。与这场裁决有关的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被害者家属情绪激动起来,在绝望和愤怒中,他们的眼睛逐渐变成危险的血红,但那颜色只存在了一秒,就很快灰暗下去。
陆沉转头,看向坐在最上端的人。此时在审判庭中,只有他的眼睛亮着血红——神圣裁决所最高裁决官,Forseti。
二人目光相接,一阵令人难受的威压油然而生。陆沉忍下心中不适礼貌一笑,朝对方点头示意后离开了这里。
直到走出几十米远,心头那沉重的坠落感才慢慢消散。日光透过中庭的窗户投落下来,一场漫长的裁决过去,也不过一个上午。
这时,有同僚从身后赶上来,他一路小跑到了陆沉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裁决官A:“Evan,怎么样,裁决还顺利吗?”
偏头看到对方的脸,陆沉几乎下意识在脑海里反应出了对方的身份。
英国某贵族的继承人,被家族送来历练,有一半光启血统,所以对他还算亲切。也许未来会与他产生不少交集。
想法不过转瞬,陆沉笑了笑。
陆沉:“当然。今天Forseti也到场了。”
裁决官A:“我想也是,有Forseti在。就算他们想在庭上做些什么动作,也会被那双眼睛压下去。”
陆沉点了点头,还想再应和几句时,正好午休钟声响起,黑压压的人群从审判庭与裁决室中鱼贯而出,像是压抑的漆黑浪潮。
正好,他也乐得轻松不用再开口。望着眼前人群陆沉分了神,他伸手进口袋里,轻轻摸了摸里面藏着的一朵柔软得几乎一触即碎的花。
不知名的白花,是他上庭前在门口雕像脚下发现的。从来完美无瑕的雕像不知何时裂开了一条细缝,而这朵花就是从其中生长而出。
裁决官A:“要是我下午的裁决,他也会来坐镇就好了。”
正分神时,同僚忽然提起了下午的裁决。陆沉手上动作顿了一顿,他看向同僚。
陆沉:“弗朗西斯军工案?”
裁决官A:“没错。”
陆沉:“没记错的话,他们偷造军火的罪名应该已经确凿了吧。”
同僚看了陆沉一眼,笑了。
裁决官A:“哪里,你忘了那个弗朗西斯是北部的啦?虽然是偷造军火,但如今他们的力量对于血族很重要,不能重判。最后应该还是赔点钱,罪不至死。”
说完,同僚摊了摊手,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解决方式,自然也就没有兴趣再继续谈下去。
裁决官A:“对了,今晚的宴会,你来参加的吧?我和你说……”
比起早就注定结果的案件,同僚明显对宴会更感兴趣,他逐一给陆沉介绍起了今晚的与会者,而在这絮絮声音里,陆沉有些出神。
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了他刚来到裁决所的时候。
神圣裁决所,诞生于血族的第一次内战之后基于那时战后的协定,由双方共同创办。
它类似人类的法院,是审判血族内部罪与罚的地方。为了让审判和裁决结果相对公正、能够服众,裁决所的裁决官基本都来自各大家族。
也就是说,不论血族势力如何交错复杂,只要没人想发动又一次内战,那至少从流程上,所有关乎血族整体的重大决定都要通过裁决所。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里是整个血族权力的最集中处。
三年前,陆沉用那个废弃承诺换来了离开光启来到这里的机会。
他告诉家主,以拉塞尔事件为鉴,陆氏似乎有些远离英国太久,他们依旧需要多结交光启之外的血族。而裁决所就是最好最高效的地方。
因此他向家主请命,希望能作为陆氏与光启的代表去到裁决所。家主没有反对,甚至鼓励了他。
那天晚上,他离开书房经由走廊回到自己房间时,脚步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
只有他知道,藏在那冠冕堂皇借口之下,自己的真实目的。
十二岁时的梦一直如影随形,它变得越来越大,以他的魂魄血肉为养料,而从中生长出的,是越来越膨胀的破坏欲、越来越膨胀的仇恨。
他已经迫不及待。他在期待着,如果有一天这个家族分崩离析。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抱有了这样的期待,但——
陆沉:“这会是个很好的开始。”
一遍遍地,他这样反复告诉自己。
于是在家主的安排下,他离开了陆氏与光启,来到了这座总是阴雨连绵的西方岛屿。
咬着那一句话,反而要比从前活得要更加“用力”。白天时,他是谦逊又努力的学生;夜晚时,他是试炼场中的怪物、宴会上的东方人。
因为在温德米尔的学业之外,他还必须为了通过裁决所的考核而努力。
终于,作为新人加入裁决所的时候,他是记载中最年轻的一名裁决官。
而来到神圣裁决所的第一天,他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门口的雕像。
一条盘旋在石树上的巨蛇,几乎与裁决所的大门同高。它首尾相衔,庞大身躯紧紧缠绕着树干,几乎深陷其中,显得密不透风。
在这座雕像面前,所有人——甚至它面前的世界都显得渺小,似乎无论怎样,都没有什么能将它撼动。
也是那天下午,陆沉第一次见到了Forseti。
裁决所的最高裁决官,来自更遥远极寒北方的血族,他的天赋是蛇触,主要以目光为介质,能够压制一定范围内一定数量血族的天赋。
而这个天赋,几乎可以永远维持,能够完美适配审判庭场合。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称作是为裁决而生的天才。
中庭的大树下,按照惯例,新人裁决官要在Forseti的带领下通读协定内容并且宣誓。
浩荡天光透过顶部的玻璃笼住中庭,在这一刻,眼前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洁净。
Forseti:“在悼亡的钟声之后,一切罪业将与魂灵并同消弭……”
陆沉:“在悼亡的钟声之后,一切罪业将与魂灵并同消弭……”
他站在人群中,跟着众人一字一句念着,漫长的条款令人有些分神。直到某个瞬间,他发现Forseti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持续了几乎半分钟,却像一场忽然的漫长对峙。是他露出了什么异状?又或者,是他与这里太过格格不入?陆沉不清楚。
但他知道,自己只需要等着。果然,在仪式完成之后Forseti走到了陆沉面前,他朝他点了点头,示意他跟自己走。
Forseti的裁决室里,陆沉与他隔着一张书桌的距离,但都没有说话。
就这样,房间里安静了很久,直到窗外夜幕落下、繁星又起,Forseti慢慢抬起了眼。
永不黯淡的血瞳,冰冷的、审视的目光,这目光就像是那条蛇,将会紧紧缠住世界的一切,于是一切也都无处遁形。
Forseti:“我会看着你的,Evan。”
Forseti的脸上忽然露出一点笑容,但那笑意冰冷又远离,像是蛇蜕下的皮。
没等陆沉回答些什么,他的后脖颈忽然传来了一点刺痛。
这种疼痛没有持续太久,一晃而过,几乎要人觉得这只是幻觉。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点幻觉似的痛感却格外令陆沉印象深刻。又或许,是因为Forseti脸上那点笑的缘故。
而第二天,他就立刻投入了工作。
负责带他的前辈裁决官给他介绍了裁决所的一系列工作。
可即便是陆沉,那精确到分钟的流程、每个流程环节中繁琐复杂的名词命名,仍让他有点头大。
似乎是注意到了陆沉的表情,前辈裁决官了然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前辈裁决官:“听起来很难是不是,其实很简单,之后你就知道了。”
他说的没错。在裁决所,一切看似复杂,但实际操作起来十分简单。
不过一周陆沉就发现,那些看似复杂繁琐的流程的背后,实际上是最简单原始的实行方式。
——在每一个节点,都会有钟楼的钟声作为提示。
比如在审判庭的裁决时,第四下钟声,裁决官就应该宣读完裁决结果。
第五下钟响,裁决将要结束、一切都应当尘埃落定。
再寻常一点的,还有一天开始时的协定宣读、结束时的沉默祷告,也都有钟声作为提示。
那些繁琐复杂的名词都被简化为一声声钟响,再最终构筑了复杂又简单的秩序。
其实甚至连裁决审判的案件内容都不需要怎样仔细研看。
毕竟在这庞大繁杂的权力网里,审判从一开始就已经能够看到结果。
裁决官和站在审判庭上的人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裁决时,更多依靠和参考的,也是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比起研究调查案件,裁决官更重要的职责是喝酒与参加无止尽的宴会。
在这些宴会上,裁决官能够最快、最广地认识最多的血族,并借此完善和梳理权力脉络,避免在案件裁决上犯错。
犯错。对。在裁决所审判结果并不依靠所谓正义或是公序良德。根据协定,一切裁决结果的最根本准则是“血族的稳定”。
但这对那时的陆沉来说,还是有点难以适应和融入。
一方面是在他心里仍有一些所谓的正义感;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急切希望的是对血族结构的破坏而非维护。
直到后来,在度过了作为助理裁决官的“新手期”之后,他开始被允许独立地处理案件。
而他经手的第一个案件,就正好,让他不得不理解并且接受了这份规则。
陆沉知道这名被告,大约几年前,他和陆氏有过肮脏交易。
更重要的是,这名被告是人类与血族的混血。
看到那份文件时,他是真心实意地觉得,这是一次可以让他一试的机会。
那天,他站在审判庭上,无视了判决书上模棱两可的文字,宣判了对方有罪。
对方愣住了。
那愕然震惊的神情只让陆沉觉得快慰,可与此同时,他的脖颈处又一次传来似曾相识的疼痛。
眼前又一次闪过那血红的眼睛与蛇蜕一般的笑意。他也再次伸手朝那里摸去。
但毕竟裁决官在审判庭上的权威是不容动摇的,这件案子就这样结束了。这点刺痛和幻觉,那时他想,不过是一点无关紧要的插曲。
可在当晚的宴会上,异状出现了。
原本多少也会冲着陆氏名气来同他交际的同僚们忽然对他不理不睬,就连一直带着他的前辈裁决官都没有再来找他。
没有迟疑,在宴会之后,他敲响了前辈裁决室的门。裁决室里聚集了很多人,见陆沉进来,忽然又都鸦雀无声。
无视了他们的沉默与目光,陆沉径直走到了前辈面前。
陆沉:“是下午的那个案子,对吗?”
前辈看着陆沉,良久,还是轻轻叹了口气。
前辈裁决官:“Evan,你很聪明。但你不应该自作聪明。”
陆沉:“按照我们的法规,他确实有罪。”
前辈裁决官:“如果他的父亲恰巧不是这个国家的某位大臣。为我们赚取人类的财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帮助。裁决所很少出这种岔子,孩子,你让Forseti失望了。
失望。陆沉心里一动。
但现在这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是——
陆沉:“现在我有什么能做的?”
前辈裁决官:“如果你还想要践行某种正义感,我会建议你回家去。做个天真的少爷,你的家族会为你安排个好去处。这里不适合你,你也不适合这里。”
可他不是为了正义感。恰恰相反,他需要的就是这一点可供操作的不正义。
只是这次,他做得不够隐蔽,以至于被发现了。
周围的人都在看他,像在看一个异类,目光几乎凝成实质,让人窒息。而陆沉依旧坚持地站着。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离开了这里,这条路将从此对他关闭。而就目前而言,他找不到另一条能够独立于陆氏的道路来接近血族核心。
这里有他想要的东西,他不能回头。
这也是第一次,陆沉发现,做出取舍和选择,原来这样容易。
陆沉:“我不想离开。告诉我,应该怎么补救?”
前辈裁决官笑了笑,他没有回答,而陆沉已经明白了其中含义。
于是在第二次庭审的时候,他当众推翻了自己的结论。
第五下钟声落下的时候,审判庭上愤怒的受害者躁动起来,他们掏出了血瓶,将其中腐败的血液都泼洒在了陆沉身上。
他被砸了满头满脸,可回到裁决室时,脸上却平静非常。
陆沉:“我没想过,这样的一个案子,他们也会为我颁发勋章。”
大家都笑了,而前辈递了块毛巾给他。
前辈裁决官:“Evan,欢迎回来。”
陆沉接过毛巾,却又在同一时间感觉到了什么。他回过头去。
是Forseti,和他的那双永不黯淡的红色眼睛。
直到这时,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后脖颈那时不时的刺痛与眼前幻觉是来自何处了。
他的一举一动其实早就被人掌握,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他没有任何捣鬼的空间。
在那之后,陆沉开始稍稍“安分”下来。他开始参加那些他原本觉得无趣甚至恶心的宴会,开始试着从他的角度建立和梳理的关系脉络。
毕竟要破坏一个结构,最重要的,是先了解它。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越来越明白裁决所究竟是什么。表面上是裁决血族之间的争端,其实是为了维持血族的稳定与不朽。
为了所谓血族的不朽,所以要清除一切不利于血族的要素,而究竟怎样才算不利?就又回到了一开始,要借助血族的权力脉络来判断。
它们环环相扣、互为保护,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百年来的卷宗里,真正做到了撬动其中某一层的裁决少之又少。
他感受到了血族的庞大与错综,就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有精密得像是仪器一样的解决方式为之庇护。
可是越明白,他就越显得那么渺小。就像是站在雕像前一样。
他真的可以吗?他开始怀疑自己。
在这样密不透风的体制下,一切似乎无懈可击。
成为机器一部分的麻木和他的反抗与破坏欲互相拉扯。
他时而挣扎,又时而沉沦,过去的任何经验与回忆都无法拯救他。他又一次迷失。
就像今天白天时的那次庭审。他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这天晚上,陆沉没有去参加宴会。
穿过两个街区,他的脚步停在了一家自由搏击馆前。
坐落在贫民区与富人区交界处的搏击馆,外立面上被喷满了各种标语涂鸦。
推开那扇脏污得几乎看不见里面情形的玻璃门,搏击馆里的击打与呼吸声便会淹没他的听觉见陆沉进来,老板和他打了声招呼。
俱乐部老板:“Hey,东方人,好久不见。”
陆沉:“好久不见。”
点头示意后,陆沉走进更衣室,轻车熟路打开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储存柜,换上了衣服。
他用了很多方法防止自己的异化,也同时,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渺小。
比如他的口袋里,总是会放着一朵花。
在他感觉到窒息或是沉沦时,他会轻轻摸一摸它的花瓣。
指尖那几乎一触即碎的柔软触感,反而会提醒他要记得控制住自己。无论是动作还是心中的痛苦或焦躁。
再比如,眼前的自由搏击。
他是在一次宴会上,因为社交的缘故第一次接触了自由搏击。
他喜欢上了自由搏击时,控制着身体每一寸但又并不会因此束缚反而更加纯粹、自由的感觉。
而为了避开那些同僚,他找了很久,才找到了这家那些自诩高贵的血族绝对不会来的搏击馆。
这里几乎成了他的安全屋。几乎每结束一次审判,他都会来到这里。
而今天,他下手尤其狠。
其实说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已经好久没有发泄过了。
也可能是因为今天审判庭上的眼泪太多,而那站在庭上的被审判者的笑,又更让他烦躁。
于是下手更狠,就好像面前的沙袋就是裁决所门口的雕像,而他只要挥拳,就能把这个庞然大物直接打烂。
有人注意到了陆沉,提出要和他对决。平日里他总是拒绝,但这回,他只是朝对方抬了抬下巴。
挥拳、躲避、再挥拳,对方被打得节节败退,甚至有温热液体飞溅到他的脸上。
这时,不远处的老板才终于注意到了陆沉的不对劲,连忙跑来制止。
俱乐部老板:“Stop,Stop。你怎么了,心情不好?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可不想看到谁在我店里毁容。”
陆沉于是停下手来,他喘着气,看向俱乐部老板。
但他心底那躁动的兴奋仍未散去。
于是他转身,径直又走向沙袋区。
可老板又一把拉住了他。
俱乐部老板:“那个沙袋一百万英镑,你看着办。”
陆沉只是看了他一眼,浑不在意那些钱似的继续往前走。
老板急了,干脆自己拦在了陆沉身前。
两人这么对峙着,莫名其妙的,陆沉心里的那阵躁动的兴奋好像还真的平静了一点。
老板对陆沉一直挺照顾,据老板说,是因为陆沉特别像年轻时候的他。
陆沉看了老板年轻时候的照片,对此表示保留态度。
正这么出神着,就在这时,老板竖起一根食指神秘地在陆沉面前摆了摆。
俱乐部老板:“别这样,我是为你着想,也不一定要盯着那些嘛。”
这么说着,老板递给了陆沉一个打乱的魔方。
陆沉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接过,而老板努了努嘴,用眼神请求陆沉帮他恢复魔方。
于是陆沉低头看了看手里魔方,抬头看了看老板,脸上忽然露出一个难得真心觉得有趣的笑容。
下一秒,他直接掰开了魔方上的塑料色块。
一旁的老板愣住,而陆沉动作反而更快,他逐个掰下了上面的塑料色块,按照颜色分好,再飞快安了回去。
装好了,又有些意犹未尽。于是他又自己打得更乱,再重复着刚刚的动作。
在这样周而复始的打乱与整理中,心里最后那点躁动的兴奋,也都跟着消散了。
老板看着他,慢慢笑起来,神情像是就在看自己的孩子或是年轻时的自己。
俱乐部老板:“其实也挺爽的,对吧?”
这天晚上,陆沉做了个梦。
他梦见了小时候,自己的一次恶作剧。
他偷走了警卫的对讲机,并且模仿了家主的声音,将他们远远地调离了陆氏城堡。
长大之后,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恶作剧过了。
不知不觉,他从梦中醒来,坐起身看向窗外时,夜幕下裁决所钟楼的影子格外清晰可见。第二天,陆沉很早就去了裁决所。
兴奋、紧张、期待……
他等待着。
虽然尽力遮掩,但前辈见到他时,似乎还是察觉出了一点他今天格外积极高昂的情绪。
前辈裁决官:“Evan,又了结了一桩大案子?”
陆沉:“不,只是昨晚睡得不错。”
陆沉按捺住内心的情绪,摇了摇头,继续着手上整理记录的日常工作。
但又因为那点隐秘的期待,这一切都变得有点不一样。
终于,在那个他计算好的时间,陆沉离开了裁决室,去到了裁决所北面、位于钟楼对角线的塔楼顶端。
他俯视着脚下的裁决所,和匆匆行走其间的同僚们。
一如既往,安静、缜密、死气沉沉。
陆沉:“五、四、三、二……”
铛——
在他的声音数到一时,钟声跟着敲响了。有远处的鸟群被惊起,这钟声仍是这样平常。
可这声钟响带来的后续变化,却十分不一般。先是负责提示案件审判的助理裁决官的忙乱。
紧接着,是更多人的混乱和失误。
有人在错误的时间推开了审判庭的门。
裁决官C:“抱歉,Redfield,我以为这一场已经结束了。”
也有的审判庭的秩序变得十分混乱。
裁决官B:“请坐下,我说,请坐下!在宣判之前,你们还有时间发表看法……这钟声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发动了天赋,听力直达远处他的裁决室,有人在钟声的催促中推开了房门。
裁决官A:“午餐时间到。Evan,你想吃点什么吗,虽然我不怎么饿。Evan?人呢?”
当然无人回答。
自那声本不应该在那时敲响的钟声起,裁决所最终陷入了一片混乱。
可明明,这群人本来都应该是所谓的精英。
而这一切……可又因为太习惯、太依赖钟声,反而因此招架不及。
陆沉:“只是因为扳动了一根时针。”
是他做的。
在半夜的时候,是他跑到了钟楼上,扳动了那一根时针。
他还记得当时的感觉,那时他只是想试试。试一试一个小小的、在常理之外的恶作剧,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他可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漏洞,就足够撬动这台看似规整严密的机器。
不由自主地,陆沉笑了起来。
他没有离开,而是继续欣赏着眼前的混乱场面。
也是在这时,他忽然体会到了那些案件中的凶手,为什么总会在案发现场徘徊。
终于,管理员姗姗来迟,为了维持秩序,他把大家都赶回了各自的裁决室。
大家也都慢慢缓过神来了,开始配合着努力重新找回秩序。
裁决所重新平静又井井有条起来。
有些可惜。他想。不过快乐好像从来都不长久,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快慰。
但他还是没有急着回去。因为他看到了Forseti。
Forseti几乎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把管理员叫到了钟楼。
管理员:“抱歉,先生,我很快就能让它恢复原状。真奇怪,裁决所的钟从不出问题,该不会是谁在做恶作剧……”
听到这三个字,陆沉心情颇好地挑了挑眉。
但Forseti却不一样。他看着管理员,脸色微。
Forseti:“聚集在这间裁决所的,是血族各个家族的精英。”
管理员看了一眼Forseti的眼神又连忙避开,唯唯诺诺地应了声是。
也是这时,Forseti好像发现了陆沉的存在。隔着在裁决所内几乎最遥远的距离,他看了过来。
血红的眼睛,冰冷的目光。陆沉能肯定他看到了自己。但这一回,他没有再慌张,而是遥遥地,向对方行了一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