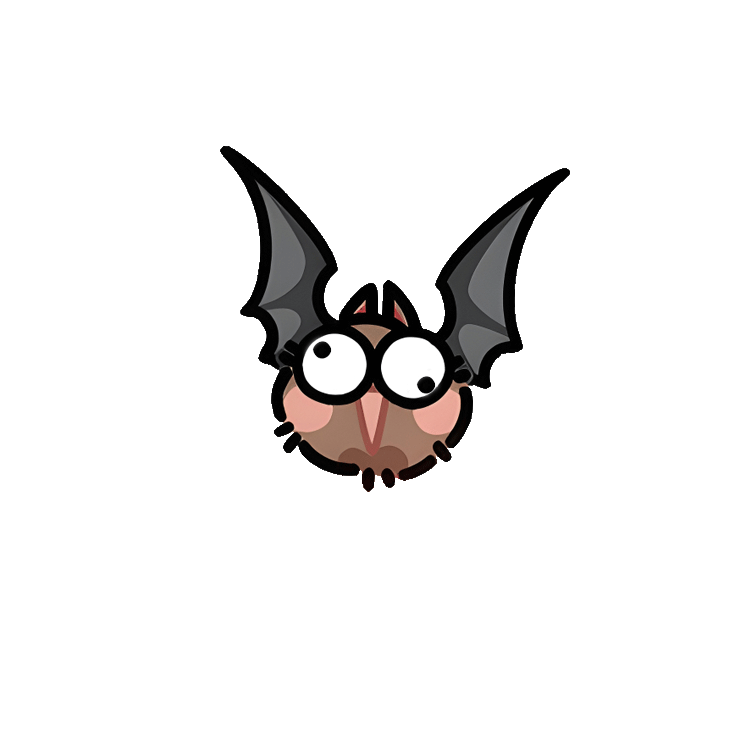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谭平村❈
我:“我想去看看谭平村。”
陆沉:“想看一座空城?”
“嗯。”准确来说,是想去看看刻在这座岛屿上的旧时光。
据说那里曾经是整个离屿最热闹的地方,后来为了避难,村民陆续搬迁,如今只剩下一片荒废的石屋。
我和陆沉登上观光缆车,一路坐到西角沙滩,剩下的路则需要徒步到达。沿着青苔石阶往山上走,被爬山虎缠绕的无人村渐此引入视野,远远望去,漫山的苍翠欲滴。
我:“这也太美了吧!”
整座山峦在盈盈日光的笼罩下,没有弃置多年的荒凉,反而呈现出一股静谧姿态。
我:“陆沉,你来过谭平吗?”
陆沉:“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里是我除了光启,待得最久的地方。”
我:“那你在岛上,都会干什么呀?”
陆沉:“嗯……散步吧。”
我:“散步?”
少年时期的陆沉,经常一个人在岛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吗?
我:“那岂不是整个离屿都被你逛完了?陪我来玩,一定很闷。”
“不会,和你一起,都算第一次。”陆沉的目光落在我肩头,海风从远处拂来,吹散了他轻然的尾音。
转过山弯,一幢彩色树屋跃入眼帘。
我:“陆沉,你看那边!”
午后的阳光从层云中渐次透出,错落叠置的碧色中,墙壁上斑斓的涂鸦格外显眼。
“这间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个有趣的人。我们去看看!”我扯着陆沉的衣袖,他却顺势牵住了我的手,包裹在自己的掌心里。
陆沉:“路有点陡,慢慢走。”
我微微弯起嘴角,也伸手握住了陆沉的微热暖意,“你也是。”
我们顺着小径一路前行,来到树屋门口。几经风霜的墙面蒙上了一层灰霭,但仍旧掩饰不住原本明艳热烈的图像。
水泥漆勾勒的两个小人,在海边牵手奔跑,放肆欢笑;也在沙滩上燃起篝火,互相依偎。剥落的石壁像印有划痕的胶卷,将过往的画面逐帧展开。
我:“好久没看过这么有生活纪实感的涂鸦了。虽然粗糙,却很温暖。”
陆沉:“嗯,我想,这大概都是画作主人,最想记住的美好回忆。”
推开树屋大门,并没有闻到料想中的霉味,相反,迎面而来的是树叶涩涩的香气。
客厅的陈列十分简单,只有两个柜子、一张餐桌,以及角落里整齐摆放的渔具。
我:“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挺干净!”
陆沉:“有人来打扫过。”
我:“诶?这里不是废弃了吗?”
陆沉的手指略过桌台上的罩纱台灯,“只有一层浮灰,不像废弃了很久。
应该是有人想留着这间屋子,但平时并不生活在这里。”
陆沉的揣测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走,上楼看看。”
我们顺着木质楼梯拾阶而上,意外发现采光不错。
我:“不住了真的好可惜。”
二层是一座低矮的阁楼,阁楼尽头连接着空旷的外阳台。
午后的阳光洒进屋内,在地板上切割出温暖的光斑。过道上横着一张吊床,金属架子的隔层里,随意搭着几本泛黄的旧书。
陆沉:“是俄国小说。”
我:“讲什么的?”
陆沉:“战争。”
我随手翻了几张,流风将书本哗啦啦地吹起。
“啊——”
陆沉:“怎么了?”
我:“没事,书签掉了。”
那枚夹着书里的小纸片,在空中打了个转,不知飞向何处。我立刻蹲下身子,四下寻找。
陆沉打开手机照明,手臂轻轻抵在桌角边,“小心撞到。”
书签掉到了柜子的夹缝里,在幽暗的光线中,我努力伸手,却次次扑空。我扭了扭发酸的胳膊,熟悉的温热声息从背后传来。
“帮我拿着手机。”陆沉侧身蹲下,修长的手臂从我肩头越过,轻松拾起了掉在角落的书签。
“谢谢……”我转身从他手里将书签抽走,正巧陆沉也微微低头,散落在他额前的碎发从我湿润的唇角轻轻擦过,带起一丝暧昧的潮湿。
温热的鼻息洒在脸上,我身体微微一颤,重心不稳向后仰去,“!”
陆沉迅速揽住我的腰,领口传来熟悉的苦艾香,我就这样被他圈入怀中。
“……谢谢。”我动了动身体,陆沉环在我腰际的力量收了几分。
“说谢谢的时候,应该看着对方,为什么不敢看我?”逆光下,暗金色的镜框后面,是陆沉温和而深敛的眉眼。
心脏骤然紧缩,我抓着他的衣角,缓缓抬起头与他对视,“我没有……”
还没等我看清楚,陆沉一下子压了过来,身上的气息愈发明显,占据我全部呼吸。
“是吗?”
我下意识地微微后退,不小心撞到了书架。
哐当——像是金属砸在地上的声音,继而扬起一阵细碎的粉尘。
我:“咳咳……”
陆沉:“没吓到吧?”
我摇摇头。陆沉稍稍拉开距离,我才看清落在地面上的,是一只陈年失修的铁盒。
锈迹斑斑的盒身敞开着,挂锁已经摔断,存放其中的明信片四散而落。
我:“看邮戳是从国外寄来的。”
陆沉伸手将我拉起,又俯身将掉落的卡片悉数收好,拂去沾染的落灰,“是圣彼得堡。”
我凑上前翻了翻,这些来自北俄的明信片不在少数。看字迹倒是十分清秀,只不过所写的内容,翻来覆去都是些寻常问候。
‘见字如面,最近过得好吗?’
‘见字如面,希望一切平安。’
这些老生常谈的话语后面,还附上了同一句俄文。
我:“这是……?”
陆沉:“我爱你。”
我:“啊?”
陆沉微微弯腰,侧身俯在我耳边。他见我满脸错愕,无奈地扬起嘴角,“我是说,这句俄文的意思是‘我爱你’。”
意识到自己会错了意,我迅速低头,假装自己正在认真整理明信片。
忽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中。
我拉了拉陆沉的衣袖,“你看这里!”
印着冬宫博物馆的明信片,其落款处赫然写着一个“瑛”字。
我:“和游艇上的奶奶名字一样!但会不会是重名?”
“我想不会。”陆沉将另一沓明信片放在桌台上,抽出其中一张翻转到正面,钢笔墨渍浅浅晕开,依稀可辨写着苍劲有力的“彦”。
我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又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寄信人,“等一下,彦写的这张,根本就没寄出去啊……”
我迅速浏览了剩余的明信片,也全部无一例外,没有邮票,更没有邮戳。
我:“为什么?”
陆沉:“也许他想把一切交给时间。”
风缓缓吹进来,瑛寄来的明信片已经很久了,道道折皱泛出岁月的黄痕。
我:“难道什么都不说,就能变得更好吗?”
吊床随风晃了几下,或许很多个孤单的夜晚,彦就躺在上面。就着昏黄的灯光,一遍遍地翻看和摩挲这些被战火分隔的思念。
陆沉没有回答,他沉吟了片刻,随后斜靠在吊床上,牵过我的手让我坐在一边。
陆沉:“靠近点。”
吊床又被压弯几分,阳光轻柔地洒下,半边铺满他的身体,半边投影在彦的手书。陆沉举起明信片,低沉的声音从喉头泄出,如同午后浮动的尘埃。
‘我一切都好。明阳山上的合欢花开了,很漂亮,可惜没找到我们一起种的那棵。’
‘我一切都好。又到了打年糕的季节,你现在还喜欢吃红豆年糕汤吗?我学着做了几回,但总是没你的味道。’
‘我一切都好。下午出海回来,拿剩下的珍珠串了条手链。本来想寄给你,不过还是算了,你大概也用不到吧。’
陆沉顿了顿,指节移到明信片的右上角,贴邮票的空口还残留着胶水的痕迹。一封接着一封,他的声音仿佛有特殊的魔力,能够穿透时空的洪流。
‘我一切都好。上次收到你的来信,还是半年前,那天路过你家门口,芒草已经长到窗边了。’
‘我一切都好。最近台风,在家里待了很多天,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无聊。’
‘我一切都好。你走之前送我的小说,还差最后一本没看,这段时间视力变差了好多。’
‘我一切都好。前段时间向船工要的水泥漆终于到手了,准备在外墙上画点东西,只是……’
我:“怎么了?”
陆沉将明信片微微拉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消散在寂静的阁楼里,“‘只是最近越来越看不清了,写的字有点难看,你一定会笑话我吧。’”
我的呼吸微微留滞,不祥的预感就像一滴墨,在清水里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我一切都好。这个月和大家待在防空洞,暂时安全。但光线太暗了,写废了一张纸,有点心疼……’
‘我一切都好。今早起床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相框,盯着合照看了会儿,始终瞧不清楚。不过还好,你的样子早就刻进我的脑海里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心口却被某种酸楚狠狠缠住。
陆沉:“还要继续吗?”
我点点头,陆沉见我心情低落,撑着吊床半坐起身。温暖的声息从背后笼罩而来,他从背后环住我,将我松松圈在怀里,拿明信片的手绕到了最前面。
‘我一切都好。很久没有照镜子,昨天去理发才发现,居然长了好几根白头发!你呢,会不会偶尔偷笑,庆幸自己在我心里永远是年轻的样子?’
‘我一切都好。今年又是暖冬,现在圣彼得堡的雪,应该很厚了吧?你最爱下雪,一定很开心。’
‘我一切都好。最近开海了,我想趁自己还没完全失明,再去一次小凉横。希望回程的时候,你已经结束了挪威的短途旅行。’
我:“小凉横?是不是瑛奶奶要去的地方?”
“嗯。”陆沉将明信片搁在一边,我转头望向他,他却将目光投向远处碧波翻滚的海面。
我:“在小凉横……发生过什么吗?”
“海难。”陆沉的声音淡淡的,在静谧的空间里却尤为清晰,“四十年前的秋天,从小凉横出发的顺昌号,在返程的途中遇到了暴雨。出海的20多为船员,无人生还。”
一股酸胀的感觉从心里涌过,我努力抑制住泛起水雾的双眼,将铁盒里剩余的所有明信片悉数倒出。然而无论怎么翻找,再也没有哪一张的日期,在这之后了。
“……”
彦永远留在了海底深处,和传说中那只海鸟一样。所以……瑛奶奶才会说这趟旅程的目的地是小凉横。
喉头微微发涩,我下意识地靠向陆沉,只觉得他的怀里无比温暖安全,“我在船上,好像问了很多让奶奶伤心的事。”
他摇摇头,温热的手指穿过我指间缝隙,与我的手轻轻相扣,“你问的,都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陆沉任由我不安地拥着,带着我又翻开了一张明信片。
‘我一切都好。离开海岛,你会不会不习惯?这个问题听上去有点傻。又不是鱼,怎么会不习惯呢。’
‘我一切都好。昨天在港口坐了一下午,以前每次出海,你都会来等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我从来没有等过你。’
‘我一切都好。虽然视力退化了不少,但听觉好像比以前敏锐了。海浪拍打礁石,苍鹭掠过头顶……以前怎么没发现,有这么多好听的声音?’
我:“陆沉。”
明媚的日光倾泻在身上,可心里却像掩着一块厚重的幕布。幕布后面,是夜晚无边无际的深海。
我拿起明信片,又放下,反反复复几次,最后起身走到阳台上。从高处望下去,礁石沿海面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和天空交汇成线。
陆沉:“想不想感受下他的世界?”
“诶?”惑然间,陆沉的手从我身侧穿过,掌心盖住了我的双眼。
我下意识地抓住他的手腕。
“听到了吗?”
“嗯,有海浪声。”
“还有呢?”
“树叶的沙沙声,好像有书被吹开了,哗啦啦的。”
陆沉的声音带着一丝被砂砾蹭过的低哑,又带着一点点淡淡的温柔。海浪的声音很像白噪音,混合着各种频率缓缓袭来。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被浸到了海水里,一股抓不住却无处不在的温暖气息将我包围。
陆沉:“我想死亡不是失去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
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所有的烦闷,就让它永远留在这里吧。”
浪花一阵接着一阵,以一种广大的包围推送过来,又以一种温和的宽容往后退去。
微微睁开眼睛,光线立刻从指缝间漏了进来,也驱散了蔓延在胸口的阴霾。
“好。”我顿了顿,趁陆沉不注意,转身抽掉了架在他脸上的金丝边眼镜。
望着陆沉眼中一闪而过的微诧,我缓缓漾开浅笑,“这样看风景,对眼睛有好处,你也一样。所有的烦闷,让那个它永远留在这里吧。”
陆沉终于反应过来,嘴角弯成无奈的弧度,溢出一声极轻的笑意。他斜倚在阳台边看了我一会,毫无预兆地,忽然伸手将我拉近。
“诶?”
失衡的身体向前倾倒,压皱了彼此的衣衫。
“没戴眼镜,看不清楚。所以,只好离你近一点。”
温热的气息被轻轻吹散,那只停在陆沉肩头的蝴蝶煽动翅膀,从我们之间缓缓飞离。
忽然,我觉得身体里有许许多多的蝴蝶振翅飞舞,要从嘴里飞出来。
“让你看风景,又不是看我……还给你还给你。”我胡乱将眼镜塞回陆沉怀里,陆沉低头一笑,将它重新架回鼻梁。
阳光开始西斜,在山海交汇的地方缓慢沉坠下去。
我:“下楼吧。至于这些明信片……”
陆沉:“你想带出去交给瑛?”
吊床上的卡片零零散散的,像暴露在空气里还未愈合的伤口。我收回短暂流连的视线,最终摇了摇头。
我:“物归原主吧。”
离开树屋的时候,我们将明信片整理好,重新放回铁盒。木门被轻轻阖上,一切与我们来时别无二致。
我和陆沉并肩而行,静静地走了一段下坡路。
陆沉:“还在纠结吗?”
我:“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如果不把明信片带出去,奶奶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她认真等待的人,也在认真等待着她。”
陆沉:“我想,这不能用对或者错来区分。你只是选择了尊重他的决定。”
或许陆沉说得对,彦不想瑛知道自己即将失明,而瑛也从未在明信片里提及当年的不告而别。
陆沉:“就让他们在彼此的记忆中,都能拥有幸福和圆满吧。”
一颗石子从我脚边擦过,又簌簌滚落,我不由地放慢了速度,“陆沉,如果是你,你会觉得遗憾吗?”
“这个问题,我暂时没办法回答你。或许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陆沉牵住我的手,斜阳落在他身上,泛起极浅的金辉。
我最后一次回头,在橙色的云霞中,那间树屋变得越来越小,隐没在交错相生的藤蔓中。
不知为何,想起了彦写在书签上的话——没有一种不幸能与失掉回忆相比。
于是我轻轻叫了一声陆沉的名字,反握住他的手,“陆沉。”
“嗯,我在。”
陆沉淡淡的笑意,是将暗天空下最后的柔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