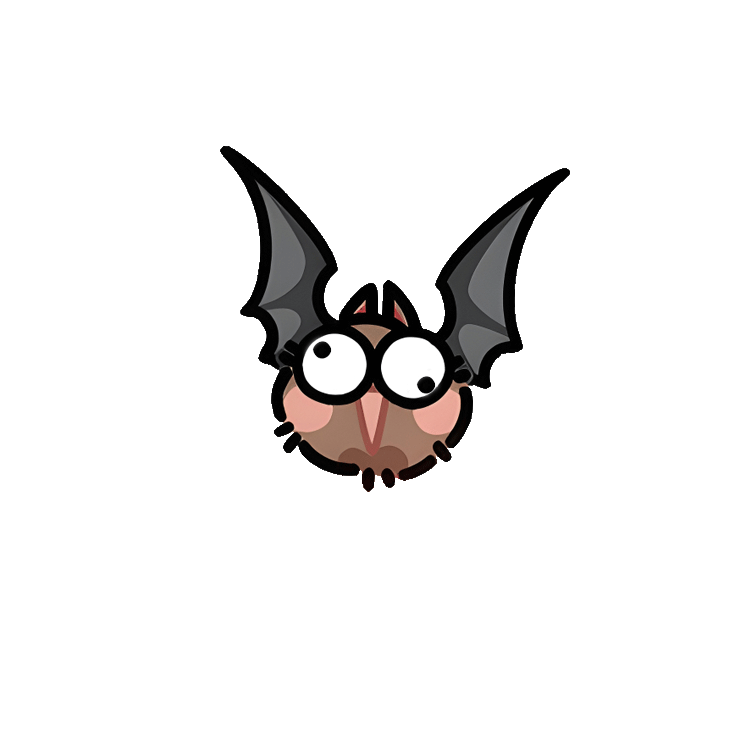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绝不宽贷Ⅰ❈
刀锋没入脊骨与皮肉,血液喷溅在身上眼前,他后退一步,那似乎从来高大的身影便直直摔在他跟前。
是他杀的。是陆沉。
他的手里还握着那把沾血的匕首,握得太用力了,铁质纹路在他掌心留下泛白印痕。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表情。
月光惨白,世界也空阔,远方响起浩荡钟声,此时此刻,天地间只剩下陆沉一个人。
他平静地在尸体旁坐下,忽然觉得有点疲惫。
少年陆沉:“这是必须的,这是为了……”
老家主:“为了什么?”
身边的尸体忽然睁开了眼。他盯着陆沉,嘶哑着逼问,那原本暗红的瞳孔已经覆上了一片浓黑。
陆沉回答不上来。他看着那双全黑的眼睛,半晌,又将目光移向了远处。
就这样安静了好一会儿,不知何时,从不知何处,渐渐响起一阵窸窣声响。
他找了一会,才迟钝地低下头。他看到他的皮肤在簌簌脱落,地上长出荆棘透穿骨骼取而代之。可没有疼痛,就好像它们本就与他一体。笃笃笃——
在那像是从远方传来的敲门声里,陆沉慢慢睁开了眼。
没有匕首与尸体,也没有什么丧钟和月亮,他正躺在自己的卧房里,而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初春早晨。
少年周严:“少爷,你醒了吗?赵医生已经等在书房了。”
少年陆沉:“……嗯,我知道了。”
他坐起身,低头盯着自己的右手,上面没有任何血迹或是印痕,于是他又试着举起它,像是手中仍握着那把匕首,向前刺去——
刀刃没入肌肤、皮肉翻出花白与猩红,刮过骨头时会有令人牙酸的刺耳声响,洁整西装将要变成爬满蛆虫的裹尸布……
而他只是看着。平静地、面无表情地、无谓地。
他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反胃。呕吐的冲动,从胃部弥漫起的厌恶与排斥感直直刺穿大脑,眼前甚至因此渐而眩晕。
这是第二十二次,陆沉在梦中亲手杀死了家主。
赵医生:“……Evan,你还在做那个梦吗?”
阳光丰沛的书房里,陆沉捧着杯子的手顿了一顿。
坐在他对面与他闲聊的是赵医生。自从母亲去世后,外婆一直很担心陆沉,在家主的特别允许下,她请了赵医生每周准时来和他说话。
这叫心理疏导,陆沉知道。他并不排斥,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确需要一个倾听者。更何况他也没有从赵医生身上感觉到任何的恶意或目的。
因此,陆沉也曾对赵医生提起过这个诡异的梦。
但他没说在梦中被他杀死的是谁。他也一直仔细着相关话题的回答,确保自己没有流露出任何“过头”的异样。
似乎是察觉到陆沉的防备,赵医生叹了口气。
赵医生:“也许你外婆忘记说了,我曾是她的学生,也是你母亲的旧友。”
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孩子,但我也想尽我所能地帮助你。
这么说着,她在茶几上轻轻放下一张旧照片。
年轻一些的外婆、母亲,还有穿着学位袍的眼前的赵医生。三人站在陆沉再熟悉不过的那栋小楼前,笑得很真心。
可梦境——梦境带来的那股恶心的感觉依旧挥之不去。于是陆沉扫过一眼便不再看,他不得不抬头看向对方。他想说点什么。
少年陆沉:“她的葬礼,您应该没有来吧。”
赵医生:“是的,我本想来悼念,但……抱歉。”
赵医生很抱歉地笑了笑,一只手下意识轻抚过茶几上的旧照片。这让陆沉放松了一些。
少年陆沉:“这不怪您。那天来了很多人,唯独没有母亲的朋友。因为是陆夫人的葬礼。只有与陆氏有关的人,才被允许出席。”
更准确来说,是那些家主需要的人。那些陌生人走进教堂、走到陆沉面前,说一些节哀遗憾的话,而陆沉必须低头听着,再鞠躬道谢。
走完了这一趟流程,这些陌生人便会簇拥到家主身边,带着千篇一律的嘴脸,谈那些所谓的比一个人的死更重要的大事。
少年陆沉:“那天,从葬礼开始到最后结束,我都没能流出一滴眼泪。直到我回家,回到她生前的房间里。”
已经很久没有对陆沉打开的房间,在主人离去后,他才终于得以轻轻推开那扇早已无人应答的门。
色彩与构图都混乱的画、干涸凝固的颜料、落了灰的折纸、还有被正面扣下的相框。都是他十分眼熟的陈设,唯一他不太熟悉的是——
少年陆沉:“我看到了地上的光盘,那段时间,她似乎看了很多电影。所以我也坐下来,把那些电影全部看了一遍。类型很多,其中有一部,是关于杀人的。”
影碟机读碟时的细碎声响浮动在昏暗房间,荧幕的光明明灭灭,在某个回神时,他才发现窗外已经落起大雨。
爱情和亲情,悲剧与喜剧,冰冷的世界末日或是终于再无可能抵达的乌托邦。
而在这些光盘的最后,是一部讲述复仇的黑色影片。
黑夜、庭院、雪地与鲜血,滚烫的鲜红液体溅落在地上消融冰雪,却又在下一秒再次被大雪覆盖。
借由复仇的名义,死亡反而带来新生。
少年陆沉:“看完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能够流出眼泪来。但也是从那个晚上起,我开始做梦。一直到昨天晚上,也还在做。”
摔落的尸体、被匕首截断的骨骼,花白与鲜红就如影片中的雪地和鲜血……梦里的画面随着陆沉的思绪又一次出现在他眼前。
而梦里的他只是平静又疲惫地看着,等待着自己的皮肤再次剥落、地下的荆棘再次透穿他的躯体——等待着,自己再次变成一个怪物。
又是一阵恶心反胃的感觉。陆沉竭力冷静,他咽了口口水,试图平复那阵呕吐的冲动。但无济于事。
这时,一颗糖递到了他眼前。红蓝白的糖纸,上面画着一只兔子。是赵医生。陆沉抬头看她,半晌,他伸手接过了那颗糖,慢慢吃了。
赵医生:“梦里的那个人,是你认识的人吗?”
赵医生温和地看着陆沉。犹豫片刻,陆沉点了点头。
赵医生:“让我猜猜看,你是不是有点讨厌他?”
少年陆沉:“他总是有办法让我做那些,我不情愿的事情。大多数时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也许是这个家……所以我想过要走,走得远远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了他,因为我并不……”
赵医生看着他,轻声开口补充。
赵医生:“恨他?”
少年陆沉:“嗯。恨才会主动想要去伤害别人,不是吗?还是说,我对他其实是……”
陆沉还是没能说出“恨他”。十二岁的小孩,对爱迷茫,对恨也惶惶不安。而恨看上去要更沉重,可世上已经没人能告诉他要怎样判断。
赵医生合上手里的记录册,轻轻叹了一口气。
赵医生:“仇恨是很具体的东西,它会稳定地、长久地指向某个具体的人或者团体。偏执地对仇恨所指采取报复行动。但你呢,尽管讨厌他,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伤害他人的行动。”
少年陆沉:“所以,这不是恨?”
赵医生:“嗯,这不是恨。这个梦,可能只是因为你当时太过悲伤,又受到了电影情节的影响。”
听到这句话,陆沉似乎终于得以松了一口气。
少年陆沉:“可是,它出现得太频繁了。如果我吃些药,可以让它停下来吗?”
赵医生:“只是做梦而已,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你想得没有错,远离这个人,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没有用,也许你可以试试……”
那天,陆沉和赵医生聊了很久。赵医生说,人与人之间并不像电影里那样能用单纯的爱恨定义,家人之间更是如此。
亲情,或者说家庭,就像是一捧藏着无数尖锐钢针的棉花糖,治愈和伤害总是并行,但又捉摸不定,因此让人很难彻底原谅或是彻底裂决。
于是大多数的人就总是含混地活着,带着不断愈合又不断新生的伤口,直到最终某一天,累积的伤害推着他走到了必须选择的分岔路。
也许,陆沉只是比普通人更早地走到了这个分岔路口而已。
夜半时分,窗外炸下惊雷,滂沱大雨随之倾盆。在几乎与世界共同震颤的雷声雨声中,第二十三次,陆沉从梦里惊醒。
他坐起身,望向窗外雷雨,月亮被层云遮去了,只有花园里的灯在暴雨中飘着一点白,像是一轮虚假的月亮。
第一次,他没有沉沦梦里血腥画面的可怖与不适,而是想起了白天时候医生说的话。
少年陆沉:“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清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试试在看清楚之后再最终决定,在这个必须选择的分岔路口前,选择是或者否、爱还是恨。
他觉得医生说的确实有道理。因为他见过很多那些所谓的苦衷,不论是小说、电影,还是现实里。
看上去自私凶狠的妇人,是因为有着一个生病的孩子;表面上严厉到吹毛求疵的老师,实际是为了那些孩子能有一条相对公平的出路……
成年人似乎总是因为各种千丝万缕的原因不得不隐藏起一点善良的好心,而通常,这样的好心就被称为苦衷。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
回过神来时,陆沉已经站在了走廊上,而走廊的尽头,家主的书房仍旧亮着灯。
鬼使神差的,他走了过去。家主一如往常坐在书桌背后翻阅文件,似乎是注意到了陆沉的脚步声,他停下手、抬起了头,看向门口。
老家主:“这个时间,你应该已经睡了。”
光线太昏暗,让家主的脸显得有些模糊,甚至在暖光与窗外雷雨的衬托下,带上了一点让他看起来温和一些的疲倦。
看着眼前的家主,陆沉挣扎了一会,最终,他攥紧了睡衣袖口,试探着开了口。
少年陆沉:“我做了个噩梦。”
老家主:“噩梦?”
家主轻轻哼了一声。就在陆沉以为他要责备他的软弱时,家主却合上了手里文件。
老家主:“先进来吧。”
陆沉愣了愣,又很快回神,走进了书房。
白天时来书房,要么是受罚,要么是不得不接受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站在家主面前时,他也总是忐忑。
而现在,明明是相同的书房,不知道是因为不同的光线,还是因为医生的那番话,他变得轻松了一些,注意到的东西似乎也跟着变了。
左侧书架上的书看上去都被翻了很多遍,而其中磨损尤为严重的是第三排第五本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右侧窗台上花瓶里一直放着的,原来并不是什么珍稀物种,而只是一截枯死的菟丝花。
书桌上家主刚刚放下的钢笔,笔身已经有许多磨损,笔帽面刻着LU,线条稚拙,看上去似乎是小孩子的手笔。
还有西装的褶皱、胸针上的斑驳旧痕、眉间已经无法舒展的刻痕……有许多从前不曾注意到的细节,忽然都清晰起来。
老家主:“从小你就比你的父亲更懂事,更有分寸,但心性上也少了点坚强。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害怕噩梦。”
换作平常,陆沉只会垂头沉默,听着不作回应
但这一次,他忽然想,自己也许可以试着说点什么——
少年陆沉:“那要怎么做,才能让心性坚强起来?”
老家主:“看看自己手里已经拥有的东西。”
这么说着,家主朝陆沉摊开了手掌。
已经渐渐苍老的掌心,深刻锋利的纹路横亘其上,随之纵横交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家族的命途走向。
老家主:“你是陆氏的血脉,生来就应该掌控。”
如今的血族比起以往,要庞大得多却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弱点。
家主慢慢收拢手掌,他眉间的沟壑也随之深刻。陆沉头一次发现,原来家主要思虑的事情,是这样多、这样重。
老家主:“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引导,分崩离析只会是迟早的事。总有一天,你会扛起这样的责任,而且要比我做得更好。”
少年陆沉:“总有一天……”
老家主:“我不在的那一天。”
陆沉愣住了。虽然在梦中他一遍遍地杀死了家主,但在清醒时,他从没有一秒会将家主与死亡、逝去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
可家主就这样毫不在意地说出了“我不在的那天”。昏黄光线中,陆沉注意到,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甚至带上了一点笑意。
而那个晚上的后来,家主又和陆沉说了很多事情,也给他看了更多他从前不曾见过的东西。
战争的长剑、和平的协定,血族如何在火焰与白骨中分裂重生,传说中那枚能够借之与神对话的戒指又是如何被各个家族分割藏匿。
甚至,家主和他说起了他的父亲与叔叔。被寄予厚望诞生的继承人是怎样迷失了一开始的心,最终走向扭曲和决裂。
陆沉几乎觉得那天晚上书房里发生的一切才应该是一个梦,从前的严苛、逼迫、惩罚好像真如那些所谓苦衷一样,背后都藏着理由。
他依旧不知该如何分辨真假,但至少在这一刻,他分享着这个家族和姓氏的所有,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命令再执行的机器。
这么思索着,最终,他鞠了一躬。
少年陆沉:“晚安,爷爷。”
老家主:“之后睡觉前,除了Hereafter,也可以让周严准备牛奶。”
带上门的手微微一顿,陆沉看向爷爷,这时他的脸上才终于露出了一点小孩子应该有的欣喜。他点了点头,离开了。
也是在那天深夜书房之后,陆沉开始刻意暗示自己用新的目光去看周围的一切。
抛却厌恶偏见的、注意着那些好的部分。在这样的目光里,他看到了在书房之外的更多细节。
餐桌上放在红酒旁的热牛奶,花园中安神的薰衣草,深夜时总是漆黑的走廊上亮起烛火……在外出时,保镖也不再那样恼人地紧跟自己。
不只是爷爷,甚至连一向不在乎他的叔叔陆霆都开始会有意无意的关照他。
他开始问起陆沉的学习、生活与任务,在走廊上遇见时也不再视而不见地擦身而过,甚至有时陆沉执行任务,还会得到来自陆霆的援助。
一切似乎正在变好。于是陆沉也开始试着对爷爷和叔叔示好,想要再更进一步改变这个原本阴沉寂静的“家”的氛围。
努力地学习,拼命地参加试炼执行任务,除此之外,他也不再抗拒、甚至主动提出去参加那些曾经在他眼里无聊又反胃的宴会。
他开始不断告诉自己,他是血族,和爷爷和叔叔一样,这是他生来的、不应逃避的、必须履行的责任。
陆沉的“听话”也渐有成效,他开始能从家主和陆霆那收到一些好的回应。
比如一套来自叔叔陆霆的西装。
陆霆:“你的西装不合身,丢的是陆氏的脸。下次出席宴会,至少穿得体面点。”
西装的布料确实很好,但很明显,送的人不清楚陆沉的尺码,衣袖裤腿腰身都大了不少。
陆沉自己默默去改合身了。但也反而是这种“不合身”让他感觉到一点安心。
又比如一块爷爷给陆沉的怀表,金属表壳上刻着双盘蛇的浮雕。
老家主:“从前你父亲的事,都已经过去。你与他无关,这只表是属于你的。”
除此之外,还有袖扣、衬衫、匕首等诸如此类的物件,它们无一例外全都有着陆氏的图纹。而这些图纹也头一次让他感到了一点归属。
但,也并不全是这样的好事情。
依旧会有矛盾和摩擦,尤其是在家主和陆霆之间。
陆沉开始学着去看那些有关家庭、有关亲情的书。
和赵医生说的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书上也说,家人之间总是会有摩擦、有隔阂。
而不一样的是,书上说重要的其实不是论出对错,而是互相体谅,走过去就好了。
可也许含混的路也可以一试呢?这么想着,陆沉开始试着想要找出症结、缓和矛盾。
不过在缓和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的第一次尝试。如果成功了,也许之后他甚至可以改变陆氏、改变整个家族的行事风格。
于是在叔叔又一次和爷爷不欢而散、摔门离开书房之后,陆沉偷偷跟了上去。
穿过长长的走廊与偌大花园,在一番七拐八弯后,陆沉发现对方的脚步停在了禁地前。
他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那扇爬满焦枯藤蔓的铁门前,抬头望着终年不散的浓雾和浓雾中高高的钟楼,站了很久。
头一次,陆沉在他这位从来傲慢的叔叔脸上看到了一点混杂着思念、茫然、痛苦、痛恨等诸多复杂情绪的……近乎脆弱的神情。
与此同时,陆沉忽然想起在爷爷书房的那一扇放了花瓶与枯死菟丝花的窗户,从那里望出去似乎也正好能看到禁地中的这座钟楼。
在傍晚钟声响起时,陆霆离开了。陆沉等了一会,也转身离开,可就在那瞬间,他似乎听到
了隐藏在钟声底下的、一声长长的嘶哑啸叫。
关于禁地与钟楼,资料室的记载并不多。直到有一天陆沉找到了老园丁,他是从前最早跟着陆氏的那一批仆人之一。
少年陆沉:“您知道那座钟楼里发生过什么吗?”
老园丁:“钟楼啊……”
苍老的园丁望着远处的钟楼,慢慢回忆起来。
老园丁:“我只记得,钟楼是家主与第二位夫人的定情之处,就是诞下两位少爷的夫人。夫人病逝,家主过于悲伤,便将钟楼圈入禁地,不许人接近。唉,陆氏这一路走来,真是颇为不易……”
讲着讲着,老人又开始感慨起陆氏的变迁,而陆沉抬头看着那座钟楼,思绪已经飘远。
第二位夫人的事情陆沉从没听说过,但回想起陆霆神情,似乎老园丁所言也不假。也就是说,叔叔是在缅怀他的母亲?可那声啸叫——
陆沉下定决心,决定自己去一探究竟。终于,在某个夜晚,陆沉找到了机会。
在禁地西边有一处缺口,而他得以从这处缺口钻入了禁地。长时间无人照看,禁地中杂草丛生,钟楼伫立在月光与荒草中显得十分伶仃。
又因为无人涉足,所以没有路。陆沉只能用力拨开眼前杂草,朝着勉强能看到的钟楼方向行进,头顶时不时还有乌鸦飞过。
小时候,陆沉听过禁地的传说,说乌鸦是食腐鸟,而禁地有很多故去血族的尸体与灵魂,所以它们才总是盘旋于此。
这时,一只乌鸦忽然俯冲向陆沉,他惊险避开,这动静又引来更多乌鸦。这些乌鸦很不正常,陆沉也赶不走,只能狼狈往钟楼奔逃。
可越靠近钟楼,乌鸦越疯狂。终于一个翻滚进钟楼里,陆沉用力关上门。鸦群在门外盘桓尖叫,他靠在门上,衣服破了大半,气喘吁吁。
少年陆沉:“糟了。”
陆沉忽然想起什么,急忙摸进怀里。还好,怀表没丢。
打开怀表检查了一下,内部也没有受损。
他稍稍松了一口气,而就在这时,从钟楼顶部又传来一声长长的嘶哑啸叫,似乎是因为离得近了,所以听得更加真切。
他定了定神,站起身,打量起眼前钟楼。
钟楼里没有烛火,只有月光从狭小窗户透进来作为光源,在黑暗中,陆沉勉强看清有一圈一圈台阶绕向最顶端。
他踏上台阶向上走,凑近了才发现钟楼每一层的墙壁上都画着壁画,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斑驳脱落,但仍能够分辨出其中内容。
一层一层上去,绘制的是以家主为首的陆氏血族的大事记。对于这些故事,陆沉已经耳熟能详,但还是仔细一段段看了过去。
一直到最高层,在一幅画着一处烟雾弥漫的峡谷、一座高塔的壁画之后,后面就都是一片空白了。
陆沉停下脚步,摸了摸空白墙壁,那里应该曾经画上了些什么,但后来被铲掉了。
当啷——当啷——
正当陆沉回忆着是否在哪里见过这高塔与峡谷,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奇怪声响。
他迅速收回了手,身体飞快转向声音传来的方位,摆出待战的姿势,眼底瞬间掠起的一抹红色又被他强制摁灭。
这时,一鼎巨大铜钟出现在月光里,刚才的响动似乎正来自铜钟背后。陆沉正准备绕过铜钟,黑暗深处却在这时再度响起刺耳的锁链声。
少年陆沉:“您是血族吗?没有人让我来,我的家人似乎对这里很在意,所以我想来看看。”
女声沉默了一会,再开口时,情绪似乎已经稍稍平静。
???:“家人……你是陆氏的孩子吧?你说在意的那个人,是陆霆吗?他和你是什么关系?”
听起来,她对陆氏很熟悉,甚至在提起陆霆的时候,声音也变得柔和了一些。
陆沉思索了片刻,选择了如实回答。
少年陆沉:“他是我的叔叔。”
声音又沉默了很久。再开口时,其中的愤怒与焦躁已经全数消散,只剩下一点叹息。
???:“竟已经过了那么久了。孩子,你上前来吧,让我看看你。绕过铜钟,陆沉依言走上前去。”
直到这时,陆沉才终于看到在钟楼顶部、月光都照不到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人形阴影,还有几根粗长锁链。
锁链一端在地上蜿蜒着连接在铜钟上,是焊死的,而另一端……
另一端,直接穿过了那个人形阴影。
陆沉的脚步因此迟疑了一下。又似乎是注意到了陆沉的迟疑,人形阴影拖着那粗长锁链上前几步,走到了月光里。
横生的獠牙、灼伤留下的伤疤、常年不见太阳的苍白皮肤,还有横亘其上的苍老斑纹——陆沉在书里见过,这是一名退化严重的血族。
更糟糕的是,这名血族已经形销骨立,而那条粗长锁链直直穿过了她的锁骨。
陆沉不由得停住了脚步,脸上露出一丝愧疚。但老人并不在意陆沉的神情,只是盯着他看,嘴里喃喃着。
???:“真像啊……”
少年陆沉:“您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出现?这个钟楼的故事,你听过吗?”
少年陆沉:“我听说过,这个钟楼是家主与第二任夫人定情的地方。她死后,家主就把这里锁闭了。”
???:“是吗……原来他是这么告诉你们的。”
这么说着,老人那张满是伤痕与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一点怀念般的神色。
陆沉仔细观察着眼前的老人。
在消退了激烈情绪之后,她的一言一行之间反而显出一点生动与落落大方来。
一个大胆的猜测浮现在他的心头。
而老人笑了笑,神色反而有些哀伤。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猜得没有错,我就是那位第二任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