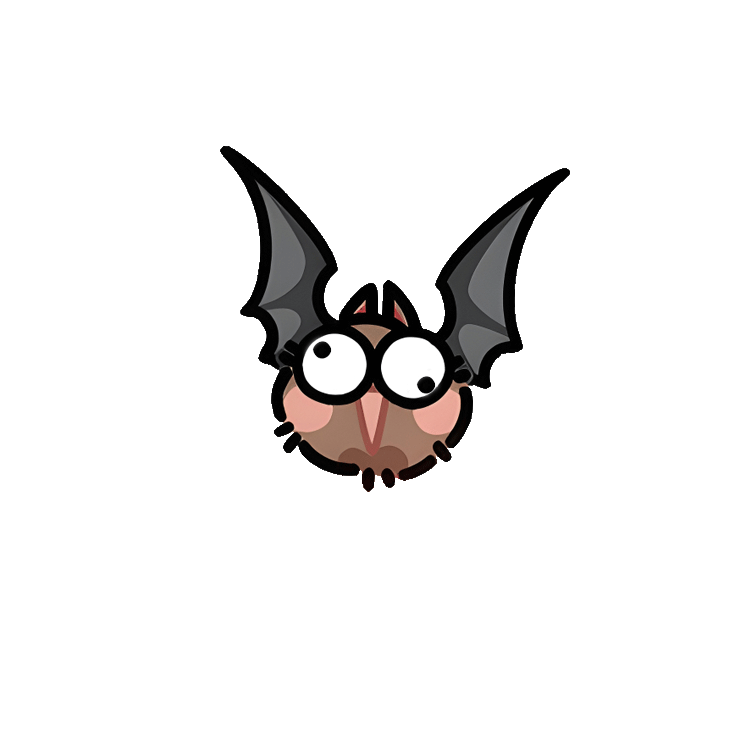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G弦上的咏叹调❈
厚重的低云倾轧着城市的天空,急雨滂沱而下,将整个视界冲刷成迷蒙的灰色,仿佛迫不及待地想要掩盖那些罪孽的印记。
陆沉慢慢地走出巷口,微弱的喘息、痛呼与咒骂从身后传来,片刻,又在雨声中湮没。
鲜红血色被冲淡了,在青石板的缝隙间流淌空气中杂糅着铁锈与暴雨的气息,陆沉抚了抚胸口,忍下干呕的冲动。
一辆通体漆黑的车停在了巷口,车门在他的面前打开,陆沉抬起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周彭:“少爷,任务完成了吗?”
陆沉:“嗯。”
车无声无息地驶入了雨幕之中。陆沉摇了摇头,拒绝了管家递来的毛巾,转头看向窗外。
车窗中映出了他的瞳孔,仍是发亮的血红色,他刚刚制造了一场屠杀,因此没有那么容易平复。
忽然,倒影发生了变化,一张与他相似的面孔出现在了那里一一冰冷、丑陋、高高在上,只是更为苍老。那是家主的脸。
麻木的心脏骤然一紧,陆沉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眼的时候,玻璃上的影子已经消失了。
车在一栋古典华美的小楼门前停了下来,管家恭敬地为他打开了车门。
周彭:“少爷,下午是陆霆先生的婚礼,到时我会再来接您。”
周彭少有起伏的语气带上了些温和的意味。陆沉点点头,弯起嘴角。
陆沉:“谢谢你给我的两个小时,我会准时到达的。”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陆沉背起半人高的琴包下了车,敲响了面前的门。
门开了,头发花白的老仆人看清了来者,惊讶地睁大了眼。
老仆人:“哎呀,陆沉少爷,您身上怎么都淋湿了?快进来吧!”
于叔没事,雨下得突然,我只是忘记带伞了。
于叔接过陆沉手中的琴包,仔细放在一边。客厅里的老人看起来等候已久,看到陆沉便快步走上前来,拉住了他的手。
外婆:“你是自己过来的?你这孩子,怎么不说一声,外婆叫人去接你。”
老人让于叔端来热毛巾和姜茶,又按着陆沉坐在整洁的沙发上,看着他擦拭被雨水打湿的发丝。
房间中,炉火静静地燃烧着,发出“哔啵”的声响,阻绝了屋外磅礴的雨声。
车里也没有多么冷,然而,此时陆沉才感到身体重新变得暖意融融,失温的血液也重新开始流淌。
这种天气怎么还出门练琴,万一淋雨生病了怎么办?
她一边说着,一边像是想起了什么,叹了一口气。
外婆:“是不是你爷爷要求的?”
陆沉:“跟爷爷没有关系,是我自己要求的。”
陆沉端坐着,捧着热气腾腾的姜茶,笑着摇了摇头。
陆沉:“那首《G弦上的咏叹调》我怎么都拉不顺,很快就要比赛了,我还要多练练。
希望到时候能拿个第一名回来。”
今天老师还夸我进步很大,让我比赛不要紧张。
陆沉:“老师说去年比赛的时候,有人居然紧张得连谱子都忘了一半”
他看着老人,眉眼弯弯,语气轻快又活泼地说着编造的见闻。
陆沉:“外婆,我还想听您再拉一次咏叹调,您的演奏技术最厉害了。”
外婆:“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我老了,早就拉不好了。”
外婆拍了拍他的手背,目光投向墙上的照片,一张张光彩夺目的舞台照,都是她年轻时演出留下的回忆。
然而老人的视线却从那些照片上一一掠过,落在了末尾的那张照片上。
照片里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寂静的幕布前,她抱着大提琴回望镜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老人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苍老的脸上露出悲伤和怀念的神情。
外婆:“其实你妈妈在大提琴上的天赋比我还要好得多。
《G弦上的咏叹调》,这首曲子,她十来岁时就演奏得出神入化了。”
老人还想说些什么,却被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
老仆人:“请老夫人和小少爷用餐。”
外婆收敛起情绪,点了点头,拉着陆沉的手一起走向餐厅。
老仆人:“按照老夫人的吩咐,今天准备了小少爷爱吃的菜。”
陆沉:“谢谢于叔。”
陆沉向老仆人礼貌地笑了笑。
长桌上的菜肴放得满满当当,好几样菜式都是陆沉儿时常吃的,如今连他自己都忘了,外婆与老仆人还一一记在心上。
其实,他并不饿,甚至还不想看到食物。
但这是难得的与家人一起吃饭,因此他没有停下手中的餐具。
甚至,比平常还要多吃了些。
老人却没有怎么吃,她看着外孙吃得急切,眼底渐渐泛起酸涩,抬起手摸了摸陆沉的头。
外婆:“陆沉,妈妈走了之后,你过得还好吗?”
陆沉夹菜的动作微微一顿,轻轻点点头。
陆沉:“没事,不用担心,我只是练琴练得有点累了,需要补充一点体力。”
他放慢了用餐的动作,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夸奖起于叔的手艺,夸得老仆人心花怒放,又给他添了一道点心。
饭后,陆沉帮忙收拾着碗筷,沉默半晌的外婆突然开口问他。
外婆:“陆沉,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一起住?
虽然这里不如陆家,但也能让你衣食无忧的生活。”
陆沉放下手中的东西,垂眸掩盖住讶异,只是抿了抿唇。
陆沉:“您怎么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您以前不是让我听话懂事,好好地跟家里人相处吗?”
老人轻轻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外婆:“以前我觉得你在那边会过得更好。
我老了,没办法长久地照顾你。
万一哪天我突然离开,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浑浊的眼中流露出无奈的情绪。那双眼睛与妈妈如此相似,只是已经如此苍老。
外婆:“可是我今天突然觉得,我的孙子过得并不开心。”
老人深沉的目光仿佛完全看穿了他的伪装,陆沉没有回答,他沉默了很久,最终只是看着外婆沧桑的面容轻轻摇了摇头。
他还是松开了这唯一一根脆弱的绳索,任由自己重新落入黑暗的深井之中。
从心脏传来的刺痛感让他难以呼吸,但他的神情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陆沉:“外婆这么舍不得我,那我以后每周就多来看看外婆吧。”
外婆的嘴唇嗫嚅了一下,话还没有说出口,刺耳的门铃声骤然响起。
不用刻意去看,陆沉就能猜到来者是谁,并且他已经习惯不去抱有猜测错误的侥幸。
那辆再熟悉不过的车在窗外停下。
灰姑娘听到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情吗?陆沉茫然地看向空中,眼神难得地有一瞬失焦。
但很快,他回过神来。
陆沉:“抱歉,外婆,管家来接我了,我还要赶着去参加叔叔的婚礼,就不打扰外婆了。”
老人一时失言,末了,她只能淡淡地叹了口气
外婆:“我送你到门口。”
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老人拉着陆沉的手,迟迟不肯松开。
外婆:“陆沉,你要注意身体,有什么不顺心有什么不顺心的,就来这里和外婆说说……
照顾好自己,哪怕是为了外婆,为了妈妈。”
站在车门旁的管家看了看怀表,犹豫一下,轻轻咳嗽一声。
周彭:“少爷,时间不早了。”
陆沉:“外婆,您也要照顾好自己,下周我会再来的。”
陆沉把手从老人苍老的手掌中抽离,向外婆挥了挥。
车窗慢慢上升,伴随着扬起的烟尘,老人佝偻的身影逐渐变小,直至完全消失不见。
陆沉回过头去,他咬着唇,将提琴紧紧地抱在怀里。
刚才的两个小时是一个美好却又虚幻的梦,而现在,该是醒来的时间了。
在车停下之前,陆沉已经收敛起那些沉静的悲伤。
它们像是窗外被风穿梭而过的流云,轻飘飘地被撕裂、消散,没有在陆沉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到达婚礼的现场,成群的仆人们引领着陆沉去更换礼服,然后将他带到大厅的角落里。
仆人们将换好礼服的陆沉带到大厅的角落。一切都只为了婚礼开始后的演奏而准备,没有人关心陆沉这个人的存在。
深红的宴会厅完全按照血族的习俗布置,暧昧的灯光浮动在同族那些交缠的身体上,恰到好处地掩饰着绅士淑女们那一层倨傲的表皮。
鲜红的酒液从透明的杯壁上淌下,恰如宴会上无处不在的流动的鲜血。
陆沉清晰地闻到了这些杂糅的气味,令他作呕,但同时又引诱着体内某种猎食的本能。
陆沉急切地想要寻找些什么来抵御眼前这些几近疯狂的颓靡,思绪如同泡沫一般晃晃悠悠地浮起,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那个转瞬即逝的幻梦。
但当外婆满脸皱纹的笑容浮现在眼前时,陆沉反而充满恐惧地晃了晃脑袋,努力地想将那些温暖的图景挥出脑海。
那些片刻的、仅存的温暖,不过是又一次地提醒他,你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
他已经松开了那唯一一根绳索,只能心甘情愿地堕入鲜血的陷阱之中。
“啪”的一声,泡沫般的梦境破灭了。
陆沉只能低下头去,沉默地调试着手里的提琴动作细致而耐心,就像眼里只剩下了怀中的这样东西。
所有的欲望、欢愉、贪梦都撕去了伪装的表皮肆无忌惮地展现在这场鲜红色的婚宴上。
陆沉:“我出去走走。”
陆沉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喉头黏腻的恶心感,放下提琴,站起了身。许多探究或是轻讽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但陆沉并没有放慢脚步。
灰色的天空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但雨势比起先前略微减轻了一些。陆沉并没有在意这些,径直走入了雨中。
飘零的细雨滴落在蓝紫色的绣球花瓣上,冲淡了视网膜上残留的鲜艳的红,陆沉这才发现自己走到了花园里。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树丛背后传来了动静。陆沉警觉地放轻了脚步,转过拐角之后,他看到了声音的来源。
一个女人坐在小路尽头的凉亭中,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凝视着天空,眼神中流淌着深深的落寞,就好像是一只笼中的鸟儿无望地看着彼岸的世界。
陆沉不由得滞住了脚步,那仿佛是一个来自于过去的幻影。母亲的神情,也曾经是这样的。
听到靠近的脚步声,女人如同受惊的动物一般慌张地转过头来。似是认出了陆沉的身份,她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勉强的微笑。
看着新娘落寞的笑容,陆沉顿了顿,鬼使神差地抬起了手,指向了一个隐蔽的角落。
陆沉:“酒店在那个方向有一扇侧门,你可以从那里逃出去。”
看着新娘将信将疑的眼神,陆沉忍不住补充了一句。
陆沉:“不是什么人设下的陷阱,是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发现的。”
新娘注视着陆沉,似有一瞬的恍神。她据了据唇,始终没有应声。正当陆沉不知该如何是好她突然抬起手擦过陆沉的耳廓。
陆沉的眼睛微微睁大,看向她白净的指腹,那里躺着一滴尚未干涸的血珠。
他已经想不起来那滴血是何时沾上的,也许是在小巷里,也许是在宴会上,无论如何,那都是他不可能干涸的罪恶。
新娘用手帕抹去了指尖的血迹,向陆沉轻轻点了点头,准备转身离开。在那一瞬间,陆沉突然产生了一股拉住她的冲动。
然而那滴血珠再次在他的眼前闪现,仿佛是提醒他作为同族共犯的身份。他早就选择了与他们一起坠落到黑暗之中,又有什么立场去做一个无辜的祭品的拯救者。
陆沉的嘴角扯出一个自嘲的笑,收回了手。他看着新娘离去的背影,长长的白纱在她的身后飘扬,如同无声的悼唁。
灰蒙的天空变得越发暗沉,陆沉回到了室内,这场既定的盛宴仍然有条不紊地按照血族的仪式进行了下去。
司仪:“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宏大的乐声中,新娘挽着陆霆的手缓缓走上了红毯,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对璧人。可是陆沉早已明白,这一切不过都是表面的假象。
听说在人类的婚礼上,新娘走上红毯的时候,会有亲人为她送行,但在血族的习俗里,新娘的任何亲人都不被允许出现在这里。
新娘只要选择出嫁,就会完全成为血族新郎的所有物。
陆霆的面孔冰冷而倨傲,他总是高高在上的阴鸷目光扫视过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的新婚妻子。
朦胧白纱之下,新娘的神情格外平静,如同一口无波的枯井,既无喜悦,也无悲恸。
陆沉再也无法如之前一样稳住手指,手中的琴弦不受控制地轻颤。
恍然间,他仿佛看见了十四年前如出一辙的旧事,那个熟悉的、年轻的身影踏上红毯,走向了原本可以逃离的悲惨命运一—
回忆如海潮一般涌来,咸腥而痛苦的气息几乎将陆沉吞没。他的嘴唇微微颤抖,艰难地咽下了这个即将冲口而出的称呼。
陆沉:“……母亲。”
很小的时候,每当自己无法入眠的夜晚,母亲总会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在月色中,她抱着大提琴缓缓走来,就像拥着自己的爱人。她在床边坐下,温柔地为他拉上一曲舒缓的安眠曲。
那时的父亲还不那么忙碌,他也会来到陆沉的房间,坐在一旁,深情地看着母亲拉琴的身姿——他曾说过,那是他最爱的母亲的模样。
每当陆沉快要入睡的时候,朦朦胧胧间,他会感觉到一个轻轻的吻落在额头。有一次陆沉偷偷地睁开眼,看到了父亲高大的背影。
在陆沉的记忆里,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爱”,它是即将入睡时,那个柔软而又温暖的晚安吻。
年幼的时候总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安安稳稳地延续下去,却不知道骤变的时刻大多是如此的猝不及防。
五岁那年,父亲变得越来越忙碌,时常夜不归宿。提琴的弦音少了一个人的倾听,骤然显得有些寥落。
从那时起,父母开始不断地爆发争执。
起初还是在深夜陆沉入睡后,那时小小的陆沉在房间里听着他们越来越拔高的嗓音,只能担忧地揪住被单。
渐渐地他们也不再掩饰,一件小事都能让他们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
他们尖锐刺耳的声音不分白天昼夜地传到陆沉的耳中,如同生锈枯涩的琴弓在弦上谱出的变调噪音。
慈眉善目的母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一脸冷漠的母亲,无休无止地命令陆沉不间断地练习大提琴。
无论陆沉觉得自己练得有多熟练,得到的永远是一遍又一遍重来的命令,直到他的手指磨出血又长好,最终长出了茧。
只要父亲回家,母亲便要求陆沉在他的面前演奏。第一次的时候,陆沉正在书桌前埋头完成课业,却一把被母亲拉了起来。
母亲把他拉到一脸阴沉的父亲面前,把琴弓塞到他的手上。
陆沉母亲:“拉琴。”
陆沉看了看手表,有些犹豫地看着母亲。
陆沉:“我还有作业没有写完。”
陆沉母亲:“就现在,先拉琴。”
母亲的眼神里是全然冷酷的不容反抗与不由分说。当陆沉不得不架起提琴的时候,感觉自己仿佛就是一个音乐盒上被钥匙操纵的木偶人。
钥匙在母亲的手里,而大提琴便是她操纵陆沉的方式。
因此,大提琴一度成为了陆沉最厌恶的事物。他越是抗拒,就越是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母亲对待他也就越发严厉。
就像是陷入了一个噩梦般的循环。陆沉被迫一次一次在父亲面前演奏,但无论他演奏的顺利还是艰难,父亲永远都对此无动于衷。
他总是一脸冷漠地看着这对仿佛在表演的母子,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地拂袖而去。
陆沉父亲:“够了!我不想再听到这该死的大提琴!你这都是在做什么,简直不可理喻!”
母亲披散着头发挡在父亲面前,近乎疯狂地拦住了父亲离去的脚步,他们因此爆发了最严重的争吵。
父亲重重的摔门声为那个夜晚的争吵画上了休止符,但母亲的琴弓和陆沉被迫的练习仍然没有停止。
此后,母亲身体里的乐声变得愈发细弱、干涩而尖利,在她日渐消瘦的躯体里回荡,将她的灵魂割裂得支离破碎。
陆沉那时候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对于父亲那份沉重的爱已经变成了一根紧绷的琴弦,脆弱得随时可能彻底断裂。
母亲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过去那些温柔美丽的神情完全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她经常突然地哭泣,满面的愁容让她看起来尤为可怜。
但每次陆沉想要上前安慰她的时候,都会被她尖锐而疯狂的嗓音喝退,冷漠地命令他继续去练琴。
母亲身体里的乐声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她苍白地倒在冰冷的地面上,那一瞬间,一切骤然安静了下来。
她住院的这段时间里,父亲很罕见地重新出现了。陆沉本以为他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但此后的每一天,他都能在医院看到父亲的身影。
父亲开始在医院和工作之间来回奔波。母亲病情最重的时候,他经常留下守夜,蜷缩起高大的身躯,和衣睡在那张小小的家属陪护床上。
陆沉早上来探望母亲的时候,经常能看到父亲帮母亲梳理长发。
在那个时刻,他竟有些恍惚,仿佛父亲与母亲真的都发生了改变,他们又回到了过去那段充满爱意的时光之中。
但陆沉很快就意识到这不过是一种错觉,他再也没从母亲的脸上看到从前那般的欣慰和满足。大多数时候,她的神情依然如同冰封一般冷淡。
对于这个即将支离破碎的家庭来说,过去的一切,终究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陆沉一直记得母亲对过去进行宣判的那个日子。
那天下午父亲不在,母亲忍着疼痛走下床,陆沉想要搀扶她,却被她冷淡地挥开了手。
于是陆沉只能看着母亲缓缓地走向她的大提琴,步履虚浮。
母亲在此时迸发了一个病人身上难以想象的力量,她举起了那把一直视若珍宝的大提琴,扔进了走廊尽头的垃圾桶里。
伴随着提琴落下的巨大轰响,母亲仿佛耗尽了全部的力气,她轻轻颤抖着,眼中的光霎时黯淡了下去,仿佛生命力即将从她的身上流失殆尽。
陆沉忽然想起来,这把精致的大提琴,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第一个礼物。
在陆沉还能听父亲讲睡前故事的年纪,父亲曾经悄悄告诉过他,在一次演奏会上,自己对那个一袭白色长裙、温柔地拉着大提琴的女子一见钟情。
当这把价值连城的大提琴被埋进了医院的垃圾堆之后,母亲和父亲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谈判。他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站在角落的陆沉,又或是默契地将他完全遗忘。
陆沉母亲:“我累了,这些事我已经完全厌倦了。不管你是出于良心还是什么感情,我都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她望向窗外,整个人笼罩在惨淡的天光中,苍白得像是透明了一般。他们之间的空白在空气中停留了许久,最后父亲沉默地点了点头。
陆沉母亲:“谢谢。”
这次母亲没有再哭泣,她终于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母亲仿佛变回了几年之前的模样,只是她的眼睛里再没有了曾经拥有过的光芒,反而像是一个垂死的老人终于接受了一切,坦然地走向了死亡。
陆沉陪着母亲办好出院手续回到了家,他习惯性地去拿起琴,这次却被母亲阻止了。
陆沉母亲:“对不起,陆沉。”
母亲突如其来的道歉让陆沉微微睁大了眼睛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迎着陆沉讶异的目光母亲罕见地向他露出了微笑。
陆沉母亲:“我知道你不喜欢大提琴,以后我不会再逼迫你去练习了。”
在她温和的目光中,陆沉放开了握着琴弓的手
他却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母亲的身上曾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今天,她再一次完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她终于完全地放弃了爱吗?
那天夜晚,反复思索的陆沉失眠了。
寂寥的夜空中,那轮清冷的月亮散发出朦胧的光芒,月光轻柔地沿着窗外连绵的冷杉倾泻而下,映照在他的床前。
陆沉注视着窗外,耳边仿佛回响起了母亲曾经在月色中为他演奏的那首安眠曲。事到如今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再听到了。
“爱”究竟是什么呢?它能让人在某一刻失去理智和自我,也能让人在放下它的瞬间变成另一个人。
它拥有的力量,足以让一个人产生彻底的改变。这是比任何力量都更为强大、更为可怕的存在。
思及至此,年幼的陆沉忽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畏惧。
一阵尖锐的刺痛从指尖传来,陆沉回过神来,才发现手下的琴弦不知何时完全断开了,在他的指尖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红痕。
他完全不记得自己究竟拉了一首什么曲子,全部的注意力都停留在了那位无辜的新娘,和她那可以预见的悲剧命运之中。
陆沉想起刚才在花园中的相遇,她最终还是拒绝了逃离的可能,如同陆沉一样,松开了那根绳索,落入到了深渊之中。
在这场奢靡血腥的盛宴上,除了陆沉以外,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位新娘本身。她只是一个被钥匙操控的木偶人,一个只有能指却没有所指的空洞符号。
台上的新娘与陆霆并肩而立,没有微笑,也没有泪水。陆沉最后看了他们一眼,收起他的琴,一个人离开了婚宴。
细雨夹杂着凉风迎面扑来,陆沉站在屋檐下,看着寂静无人的花园,轻轻地叹了口气。
爱是什么?
是如同火焰一般燃烧的亲密、激情与欲望,抑或是需要以全部的生命对另一个人生命的承诺?
然而承诺会扭曲,欲望会吞噬,烈火会燃尽,以生命捆绑的亲密关系终有一天会走向失控。
如同他和母亲手中的琴弦,不论演奏过怎样美妙的乐曲,都会在临界的那刻遽然断裂。
陆沉:“呵。”
陆沉自嘲似的低笑了一声,他忽然庆幸,那些灰色的过往让他认清了爱和婚姻的本质。
在他像其他人那样,盲目地追逐“爱”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