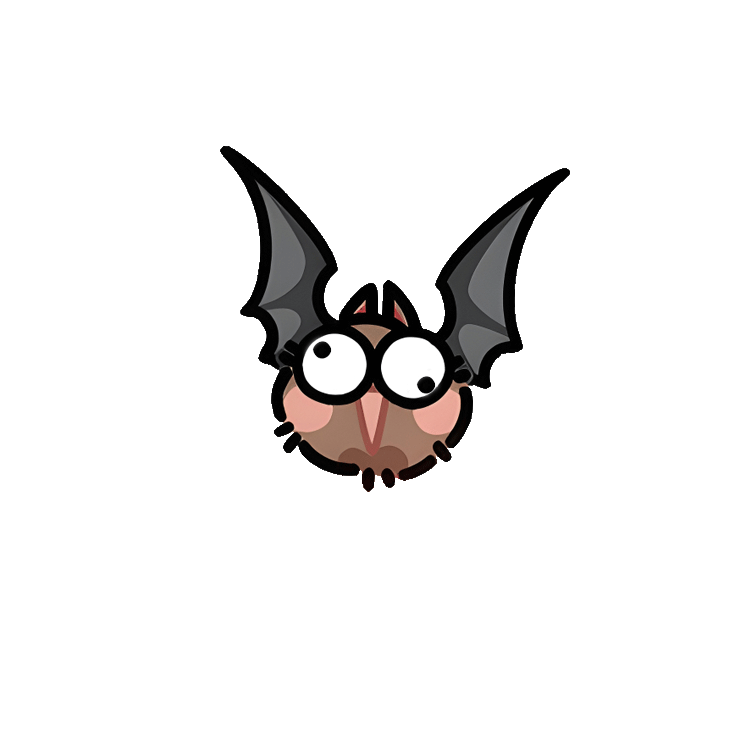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死生同状❈
刻下最后一字料峭的笔锋,弥漫的石尘染在我的指尖上。这是今日最后一个名字了。
巨大的碑石已有两面又一半刻满了名字,还空着一面半,不知道何时才能填满。
这无字碑一刻便是九十九年,而我在这地府,也已经待了九十九年。
仰头望去,每个名字都是我亲手所刻。纵横交错的笔画逐渐消失在穹顶垂下的阴影中,仿佛没有尽头。
陆沉:“既然已经完成了,怎么还不离开?”
声音自背后响起,带着些许熟稔的笑意。不必回头,我也知那是陆沉。
我:“你怎么来了?”
陆沉:“这是明天的名单。”
他像往常一样递给我一卷名册,循例仍是九十九个名字。
我:“不能再多给我一些名字吗?这样刻下去,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陆沉眸色微暗,于是灯烛和风也跟着一起沉默下来。
陆沉:“还是很想离开这里吗?”
我顿了顿,忽然间发觉,其实我已不像初来时那般急着离开了。或许是因为习惯,又或许是地府的日子并非我想象得那般无聊。
孟婆会和我分享她最新配出来的汤谱,黑白无常时常拿萝卜和我来交换话本故事,奈何桥上不时有情人惜别的戏份可看……
还有陆沉,他始终陪伴着我,并给予我在地府最大的自由……这段在地府修无字碑的生活,可以称得上自在和快乐的。
只是这样的自由,对于我来说,或许还不够。
大概是我沉默得太久,让陆沉会错了我的心意,他望着石碑笑了笑。
陆沉:“你不属于这里,想离开也是人之常情。”
我:“我在地府过得很开心,只是仍不知晓自己的来路与去处。被动留下和选择留下,终究还是不太一样。”
陆沉点点头,目光落在我手中的名册上。
陆沉:“这九十九个名字已经耗费你不少心神,再多一些,我担心你耗损太多。”
我捏了个指诀,静寂的四周忽然吹来一阵清风,将名册翻过两页,又牵了牵陆沉的发丝,将他头上的珠冕轻轻摇响。
我:“你看,连你教的“控风术”,我都已经学会了。我的仙骨在你的帮助下,也已经修复了大半,多刻几个名字不成问题。”
与陆沉相处日久,我的修为大为增进。他不仅会帮我修补仙骨,偶尔也会教我一些地府的法术。
这些年间,值得他动用法术的时候实在不多,大半都是为了教我。
陆沉:“我承认你天赋异禀,但无字碑的力量不容小觑,还是慢慢来为好。”
我:“好吧,听你的。”
远处隐隐传来数下钟声,我这才意识到亥时已至。
每日这个时辰我都会去找陆沉。只要能握住他的手,地府的空寂与寒冷便近不了我的身。今日迟了些,他大概是因为这个才找来的。
我:“嘿嘿,不小心就忘了时辰。你是特地来找我的吗?”
陆沉抬起手臂,我很自然地挽了上去。这九十九年里每日如此,于是生疏也变得亲密,亲密也成为习惯。
而他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单调,不是处理地府事务,就是阅卷、修炼。余下的便就是与我在一起了。
陆沉:“如果我说是来监工的,想看看你有没有偷懒呢?”
我:“这可是在地府,你阎王大人的地盘,我怎么敢偷懒。”
陆沉:“昨日有人答应黑白无常收集忘川上发光的幽魂……却躲在树上睡了一整天,随便找了几只萤火虫打发了。上个月的某天晚上自告奋勇来帮我研墨,其实是为了逃避判官安排的晚课,不想修炼心术。去年……”
我:“好了好了,哎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还记得这么清楚?”
陆沉:“我的记性很好,想忘都忘不掉。”
我:“你既然都发现了,怎么没拆穿我?”
陆沉:“偷懒不算坏事,何况这些都无伤大雅,更没有必要为此去破坏你愉快的心情。”
我:“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地府发生的每一件事,你都这么清楚吗?”
陆沉:“那倒也没有,我只关注想关注的事情。”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关注之一吗?
心口忽然有些混乱地躁动,这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
前几天练习法术,风刃不小心将我的手指割破,陆沉轻吮过我的伤口的时候,它也跳得如此刻这般快。
还有我在忘川旁看噬魂鲤吐泡泡转头撞进他的眼波的时候,在古桐树上观星却失足掉入他怀中的时候……这种异样的情愫似乎愈发频繁起来。
耳边的扑羽声扰乱了我的思绪,黑鸦落在陆沉的肩膀上,脚上系着一卷信。
我:“发生什么了?”
陆沉:“人间有异常。”
陆沉将信交给我,是某位判官写来的。
信上说,人间的汴京城内近来有许多孤魂野鬼作乱,搅得人心鬼心两处惶惶,不得安宁。
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陆沉一贯主张人界与冥界泾渭分明,为此还推行了“有悔令”,让那些怨灵野鬼也可以在修罗道中修行历练。
“有悔令”让意志坚定且修行成功者拥有不坠入地狱道的机会,而失败者则被彻底剥夺意志归于阴兵。此令之后,魂魄作乱的事便鲜少发生,更别说是“大规模”的。
陆沉:“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想要扰乱冥界。”
事情似乎并不简单,好似一团交错缠绕的浓雾,让人摸不到头绪。
想来如今的人间,也与我记忆中的不太一样了。
我:“不如我们一起去人间看看,也好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陆沉:“所以,你是想去调查事情,还是想去人间看看?”
我:“当然是去将此事调查清楚了,肯定不能任由他们败坏地府的声誉。与其道听途说,还不如亲自去眼见为实。”
陆沉:“你似乎很想去人间。”
我:“哪有哪有,人间也不过是比地府更热闹一些,好吃的点心多一些……”
我每说一句,陆沉脸上的笑容便多上几分,暗红的眸色深邃如渊,似乎早就看破了我藏在言语里的那点小小私心。
引诱的法子行不通,还好我仍有其它的办法。
我:“我都九十九年没有离开过地府了,出去放放风也不过分吧?好不好嘛,嗯?”
我撒娇般地摇了摇陆沉的手臂,他的广袖随着我的动作飘曳,似乎那颗心也跟着松动了几分。
陆沉:“既然人间这么好,那便去吧。”
我:“真的?”
陆沉:“如今你的仙骨已经修复了大半,简单的化形,出地府应该不成问题。”
我:“太好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陆沉:“再等几日,我找到合适的人选陪你一同前往。”
我:“你不就是合适的人选吗?还是,你不想陪我去?”
我还想带他看看人间的热闹,坊市上如星萼流火般的花灯,茶楼里最受欢迎的话本子,还有雕着团花的糕饼和裹着蜜糖的果子。
陆沉:“不是不想,是不能。”
我:“为何不能?”
陆沉:“阎王终生都要待在地府里,无法离开。”
他轻描淡写,我却有些愕然。他法力高深,统御有术,比天界的那些上神都要强上许多,却要受困于此吗?
思及此,心口莫名多了几分酸涩和心疼。
这地府虽楼殿鳞次,山旷川行,可若这就是他全部的天地,那未免还是太小了一些。
我:“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陆沉:“你很想让我陪你去?”
我:“当然想了。人间虽然热闹,但若是只有我自己去终归是少了很多乐趣。”
陆沉:“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把我的五感六识附在一个纸人身上,你便可以将我带出去。”
我:“这个办法好像不错,带着纸人的话应该也会方便很多。”
陆沉:“不过,我只能在纸人的身上待三个时辰。一旦超过这个时间,我的元神就会开始消散,直至寂灭。”
难怪他一开始没有提起这个方法。我现下也犹豫了起来,况且,想来他也不会愿意把性命交在我的手里。
我:“算了算了,这太危险了。”
陆沉:“你会保护我吗?”
我:“当然。”
陆沉:“那我就不会有危险,不是吗?”
我:“你当真这么相信我?就不怕我趁机携阎王潜逃了吗?”
陆沉:“不怕。”
当然,我也不会置他于险境。如今陆沉是唯一能引我去业镜台看前世记忆的人,我还要倚靠他来修复仙骨,我在心里同自己这样说。
可那颗如悬丝上、不时凌乱的心却又似乎在告诉我,在这些缘由之下,还藏着别的什么。
还没等我理清思绪,一只小小的纸人已跳到我的手心上。不过是简单的用墨线勾画的嘴巴和圆眼睛,竟也变得格外可爱。
想来我是修为之人,好歹会些仙法。如今只是去民间走走,保管妥当的话,应当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将附了陆沉神识的小纸人藏在胸前的衣襟里,那是我所能想到最妥帖的保护他的位置。
陆沉:“还是换个地方吧。”
我:“为什么?这里最安全。”
陆沉:“你是不是忘了,我是有五感的。”
是哦,怀中的毕竟不是普通的小纸人。我有些慌乱地将他取出来捧在手心,脸庞微微有些发烫。
陆沉:“我看你的衣袖就很不错。”
最后我把他放在了袖中,就像初见时他也将我藏在袖中那样。想起他那时含笑的眼,心底便有一处柔软地陷下去。
我与陆沉步入人间之时,正值落日熔金,暮云合璧,暖光软尘被风吹动,徐徐铺满整条长街。
几乎整座城的百姓都聚在长街上,阳气鼎盛,铺面林立。人声和笑语生出羽翼,盘旋在霞色余晖之中。
我点了点木桌上泥塑的小动物,又看看竹架上造型各异的花灯。巷口变幻术的摊位前挤着许多人,我护住袖中的陆沉,伸着脖子张望。
人群中隐约有苦香袭来,我仔细地辨认,才发觉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的腕间都系了用艾草编制的手环。
我:“他们为什么要戴艾草环?”
陆沉:“今日是端阳节,戴艾草环是传统,寓意趋吉避凶。”
是人人都会喜欢的好兆头。我寻了个最近的摊铺,也想给自己买一条。
只是那艾草环也有许多讲究,编了莲纹的,添了琉璃珠的,还有混了彩色锦丝的…我的手悬在半空,一时不知该伸向哪个。
陆沉:“怎么了?”
我:“艾草环居然有这么多样子,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个好了。要不你来帮我看看?”
窸窸窣窣的声音飘入耳畔,陆沉自我的袖口探出头来,纸片摩挲着我的手腕,传来些微痒意。
陆沉:“沉香木珠的气味,你或许会喜欢。”
我循声嗅了嗅,果真好闻,于是掏钱将它买了下来。
我:“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陆沉:“一种猜测。离魂香里掺有沉香,你既然喜欢我的离魂香,我想,或许也会喜欢这个。”
其实那不过是个能多待在他身边的借口罢了。离魂香固然好闻,但更多地是因为那香气总是和陆沉一起出现。
他替我选的艾草环很好看,苦艾与沉香萦绕在我的腕间,仔细闻闻的确有几分像他身上的味道。
我忍不住看看袖中的小纸人,汴京城人人都戴着艾草。如今我也有了,只剩他的腕间还是空空如也。
我:“可惜你的原身不在此处,不然也可以选一条来戴。”
陆沉:“这些外物对于我来说,本身也没什么意义。”
艾草环或许是外物,可想要祈求的平安与福佑,人间与地府也不应当有什么差别。
我借来一支笔,仿着我的艾草环在他的手腕上画了一个,又蘸了少许朱色在正中点了朵小花。
陆沉:“谢谢你送我的艾草环,我很喜欢。”
我:“有画为凭,这是欠条。等回到地府,我便亲手给你做一枚。”
陆沉:“好,我很期待你的礼物。”
我们又往前逛了很久,新出炉的花瓣果子纸人没办法品尝,但我会为陆沉描述那酥香的口感,他也点点头,像是真的吃到了那般。
这样走走停停,直至星河渐明,花灯流转,我几乎快要忘记了来人间是为了调查鬼魂作乱之事。
我:“不是说人间如今很混乱,今日看下来倒是一片太平祥和。”
袖子里的纸人动了动,没有应声。
我正要同他再说些什么,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吆喝声。不远处的小摊上摆着一把把造型材质不同的发梳,泛着柔美的光泽。
脑海中渐渐浮现起我与陆沉的初遇。那时我接住了他快要滑落到炉中的长发,他为我梳开发辫上的结。
我记得那把乌木梳已经很旧了,样式也很普通,与他不太相衬。今日遇上了,正好可以为他换把新的。
在小摊上挑挑拣拣,我选了个和他锦袍与眸色都颇为搭配的檀木梳子。
摊主:“要买把梳子送给心上人吗?”
我:“送给心上人?”
摊主:““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送心上人梳子,寓意着会白头偕老。”
原来在人间,只有亲密无间的人才会为对方梳发啊。我将梳子揣进怀中。
行至巷角无人处,袖口里忽然传出了陆沉的声音,被衣料掩得有些闷,辨不清情绪。
陆沉:“梳子是想要送给谁的吗?”
我:“是有一个想送的人。”
陆沉:“谁?”
本是要直接送给他的,但方才摊主的那些话他定是听见了,于是,说出他的名字就变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我:“不告诉你。”
小纸人歪了歪头,我竟被那墨笔点出来的眉眼看得有几分心虚,连解释的声音都乱了几分。
我:“买梳子,不就是为了梳头的。怎么男男女女间,还有这么多讲究。”
陆沉:“在人间,只有亲密的人才会为对方梳头。”
我:“人间如此,那地府呢?你第一次见面就为我梳头了呢,又该怎么算呢?”
话音出口,我才意识到言语间有些暧昧。脸庞微微发着烫,好在檐下灯烛明亮,陆沉大概很难发现。
陆沉:“地府的兔子,身上经常也会打结。尤其是到了秋天,忘川边长出苍耳的时候。”
竟然是梳兔子养成的习惯啊,亏我还一直将此事记在心里呢。
我:“原来你为我梳头是把我当成兔子了啊。”
陆沉:“它们打结的时候,我都会用仙法为它们蜕换一身皮毛。但面对你时,我却不想这么做。这样算下来,倒也不失为一种亲密。”
没想到他会如此认真地同我解释,还将我们之间的亲密说得这般自然,这下大概整条长街的花灯都遮掩不住我脸颊的绯红了。
我顾左右而言他,避开陆沉的视线把小纸人往袖口里推了推。
我:“那个……那边怎么这么多人啊,我们也过去瞧瞧吧。”
袖子里传来轻轻的笑声,我有些心虚,脚步却越发轻快起来。长街的喧闹萦绕在耳边,他的那句“亲密”却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云汉迢遥,明月沾衣,灯华流转十里不绝,正是游艺会开场之时。我跟着摩肩接踵的人群朝花楼走去。
花楼的竹架攀得很高,仿佛星辰夜垂在其间。丝绢与锦缎攒成各色绸花,好似无尽的飞瀑自九霄而下。
我:“好漂亮的花楼啊。”
我将小纸人捧在手心里,起脚尖尽力将手举高,好让他也能看见。
我:“这些装饰很是精致,制作也要耗费许多时间,这里的人们过得应该还算不错吧?”
陆沉:“或许只是表象。”
我:“可我看周围人的衣着,用料也都很讲究,有些还绣着暗纹呢。”
陆沉:“你看他们的鞋子。”
若不是他提起,我大概整晚也不会将目光投向人群的脚下。他们的鞋子大多是粗糙廉价的布料,因终日要与砖石泥泞磋磨,损耗很快,更能体现经济状况。
以华锦伪饰的安宁与幸福,在踏入尘土的瞬间,便全数剥落殆尽了。
陆沉:“再看花楼上那些拉绳的人。”
循着他的指引,我向花楼上望去,这才看到每层的四角都有人在用力拉着绳子。他们身形瘦弱,布衣褴褛,几乎无声消融在浓暗的夜色里。
陆沉:“这个庆典上有募捐活动。而它的发起者是当地的豪绅。人们被告知,花楼前的箱子里银钱越多,这里就越太平。而出不起银钱的人,就要无偿地为建造这座花楼出力。”
我:“原来这场盛大的庆典,竟是这样来的。可他们明明已经过得这么苦了,为什么还要耗费银钱来兴建花楼、筹办庆典呢?”
陆沉:“可能是自欺欺人吧,假装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改变。比起无力更改的现实,虚幻的念头有时也能成为一种信仰。就像这花楼,看似富丽堂皇。但除去璀璨的外衣之后,与废墟无异。”
他的话音在耳畔盘旋,再仰头眺望那座花楼时,心境已然不同。我无法抑制地将目光移向那些被灯火遗忘的角落,移向被藏匿起的真实。
人群中骤然响起一声尖叫,如石子激入平湖。花楼的顶端燃起一蓬灼烧的白火,沿着竹架迅速蔓入人群之中。
如锦的繁花几息间就化为灰烬,绝望的哀嚎与尖叫代替了欢笑,被白火吞噬的身影不断从楼上坠落,重重地摔在尘埃里。
混乱的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声喊了句“幽冥之火,吞没人间,无处不地狱…”,似是在将这一切归咎于地府,又预兆着人间将永无宁日。
于是人们逃窜得更快,方才我们一同逛过的小摊,看过的花灯,分享过的满口甜香的酥皮果子,转眼皆被慌张的人流冲散了。
白火愈燃愈旺,星火被夜风吹落到我的脚边,忽地攫住了我的心神。
地府的白火从来都是寂静的,不会如眼前这般,随着风向肆意摇曳。
我:“这些白火不对劲,难道是假的?”
陆沉:“的确是白火。只不过,它不是来自地府。”
我:“怎么会?难道除了地府以外,还有其他地方有白火吗?”
陆沉:“白火曾经向天庭出借过。”
我:“天庭?你是说……天尊?”
如今天庭都受他的掌控,那使用白火构陷地府的人,也应当是他。
我:“现在该怎么办?不能让它伤害无辜的人。要是你的真身在就好了,这点白火是不在话下的。”
陆沉:“有你在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操纵它。”
我:“白火是神火,我怎么可能操纵得了。这是只有阎王才能做到的事情。”
陆沉:“你不是已经向我展示过你的“控风术”了吗?就当做是一次试炼。”
似乎也没有什么旁的办法,可我看了看自己的指尖,仍觉得有些忐忑。
我:“你真的相信我能操纵白火?”
陆沉:“既然这里的白火能受他人操纵,那么操纵它的人也可以是你。”
我:“那怎么能一样,人命关天,稍有不慎便无法挽回。况且,我那“控风术”什么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
陆沉:“我比你更清楚你的能力。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我:“你真觉得我行?”
陆沉:“当然。”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眼看着竹架倾塌,大火从花楼上袭下,不断有人影被吞没,我深深吸气,决定一试。
我将陆沉的小纸人贴在肩头,在那双墨点的眼睛之后,有一道深邃而安定的目光在凝望我。
陆沉:“别怕,有我在,我会帮你。意守丹田,凝神入气……”
如同在地府中学习控风术时一样,我遵循陆沉声音的指引,将法术凝于白火之上。那火光猛地一跳,竟真的退后了三分。
只是还未等我露出惊喜的笑容,白火忽然摇身化作白虎,怒啸一声,朝着人群扑去。
我:“糟了,这些白火不受控制了。”
陆沉:“它在恫吓你,想让你向它俯首称臣。你愿意就这样被打败吗?”
他的声音沉稳如水,让我隐隐有些熟悉。似乎也曾有人在我耳边问过相似的话。
心间被他唤起一蓬熊熊燃烧的火,此时彼刻我的答案都只有一个,我不愿被打败。
陆沉像是能听见我的想法,他用声音牵引着我。
陆沉:“现在就让它知道,你的回答。”
我重新凝神运气,白火在我的控风术下渐渐化作一条古螭,八爪燃着不熄的火,怒目瞪向人群中的白虎。
白虎调转视线,扬起利爪扑上来,与古螭缠绕在一起,獠牙深深刺入对方的脖颈。
额头传来钻心的痛楚,我尽力控住内力的抵抗。古螭张开巨口,咬住了白虎的喉管,擒着它腾入云霄之上。
如此僵持了不知多久,只听见长空中传来一声哀鸣,白虎的身形化作四散的流火,部分被夜色淹没,部分坠落到我们眼前。
我:“我可不会被你的一点手段轻易吓退!”
我转头看向肩上的陆沉,他的目光此刻投向了远处。
夜风巡游而过,吹起满街空荡荡的尘灰。花楼焚毁,祥和热闹的长街如一场幻梦。
哭喊与呻吟声从风里传来,老翁拖着血肉模糊的残腿,青年的面庞面目全非。走近街口一道残存屋檐下,一位母亲正恸哭着将女儿渐渐冰凉的脸颊擦净。
我下意识抬起手,却又僵在原地。我不知该如何减轻他们的痛苦,就像我不知如何才能消解心间阵阵涌起的对天尊的愤怒。
我转头望向花楼,它真如陆沉所说的那般。短暂的繁华背后,只是一片废墟。
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回到了地府,这里一如既往的安静,我却觉得那些哭声和叫喊并未消失。
熊熊吞噬的烈火,四散奔逃的人群,落满灰烬和残骸的长街……它们在我的脑海里长出根,将那些关于人间的记忆全部替换成今夜。
纷纭的画面次第闪过,一会儿是长街的白火,一会儿是天尊的恶行,一会儿又变成陆沉那双暗红色的眼睛。
忘川的流水映出我的倒影,那些黑莲盛放得绚烂。
陆沉:“在想什么?”
陆沉已变回原本的样子,站在我身侧时,影子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身上。
我:“这些黑莲很漂亮。”
陆沉:“嗯,是很漂亮,但同时也很危险。”
他意有所指,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人间的花楼与烈火。
我:“今日人间之事,你怎么看?”
陆沉:“有人想找地府的麻烦。”
我:“天尊一手遮天,想要将地府也收入囊中并非难事,为何要如此波折。甚至还要大费周章,不惜将人间也卷进来呢?”
陆沉:“因为生死簿在这里。”
我:“生死簿?”
陆沉:“生死簿里藏着天尊的秘密,他畏惧它,但又想掌控它。只是如今的他做不到,所以便制造些麻烦,好阻止别人去发现他的秘密。”
我:“什么秘密?”
陆沉停顿了片刻,短暂的沉默似是不知,又似是藏着什么不想让我知晓的隐情。
陆沉:“我目前还无法确切地断定,或许只有读懂了生死簿以后才能知道。”
生死簿一直由阎王掌管,现在理应在陆沉手中。
我:“既然生死簿掌管三界命数,何不直接更改天尊的死期,此事便可了了。”
陆沉:“因为生死簿是无法被篡改的。”
我:“连你都不可以吗?”
陆沉:“嗯。不过,也有例外。”
我:“例外?谁?”
陆沉静静地注视着我,我的身影映在他眸底深处,渐而被笑意淹没。
陆沉:“一个神通广大却不自知的人。”
我:“若是有这个人,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生死簿打败天尊了……去何处能寻到此人?”
陆沉:“等她愿意出现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不过,就算是她,也无法直接用生死簿杀死天尊。天尊已经修炼无上法力,不死不灭,他的名字也不在这生死簿之上。”
听上去有些棘手,我忍不住蹙起眉心,却被陆沉的指尖抚平。
陆沉:“不必担忧。你今日能击退天尊的白火,已经很厉害了。”
我:“那是因为我知道有你在。”
在今天或是更早之前,我便渐渐意识到,有陆沉在身侧,我能做到许多事。即使是对抗天尊,只要是与他一起,我也能有一战之力。
我:“陆沉,我想去业镜台前试一试。我今日能引白火,是不是代表仙骨修复得不错?”
他没有点头,也没有否认,只是弯起眼睛摸了摸我的头发。
陆沉:“好。”
陆沉带我朝着地府的偏僻之地走去,黑白无常说那里是一片荒芜。因此在地府的这些年间,我从未往此地去过。
这里荒凉寂静,天地稚气浑然融为一体。唯一明亮的便是正前方的那方水镜,风吹过时泛着涟漪。
陆沉说唯有修为强大的人才能承受它的法力,于是我暗暗地运起全部的内力。
然而几番下来,那方水镜仍是纹丝不动,那里什么都没有。无波无澜的镜面,只照出我孤零零的失望的影子。
我:“是我的修为还不够吗?”
陆沉:“或许只是时候未到。”
我:“可是我不能一直活在迷茫与未知里。遇到的人,皆云我过去如何如何,他们畏惧我,轻视我,嘲弄我。
我究竟是作恶多端的妖猴,还是倾覆秩序的悖逆者,是英雄,还是罪人……善的恶的,褒的贬的,总该有一套说法。我想知道真实究竟是什么。”
陆沉:“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世间本就没有绝对的善恶。而人心是流动的,带着现有的认知,去看过去的自己,难免苛责。”
我:“可我还看不到过去,连苛责自己的资格都没有。”
陆沉:“即便你真的做过什么,过去的事也已经无法改变。他们看你,皆是从外象。唯有你自己,才能从心的角度来审视自己。
样子会变,观念会变,这个世界也在变。唯有心,是不会变的。”
从心的选择,是现在我唯一可以握在掌中的真实。
他的话抚平了我心底动荡不安的褶皱,刚刚翻涌而上的执念与焦躁竟消散了不少。
我:“那你呢,一直都在从心选择吗?”
陆沉摇摇头,那一瞬有很多悲喜从他的眼睛里流过去,但最终都化作了平静的湖泊。
陆沉:“我鲜有做选择的时刻。从有意识以来,我便已经在这地府之中。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将要到哪里去。
简而言之,我是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人。”
我:“怎么会……”
我没想过会听到这样的答案,那双淡然而可靠的眼睛望下去的,竟是与我相似的茫然。
我张了张口,却忽然不知所措。
我:“会觉得孤独吗?”
陆沉:“比起孤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不错的机会,让我得以观望命运,以一种局外人的方式。在无尽轮回之中,命运往往只是一场错觉,最终都会归于虚无。当我了解到这一点,我便不再去思考孤独这件事了。”
陆沉看向我,他的目光好像抵达了我心里最深的某处。
陆沉:“不要受困于未知,不要让那些伤害到你。”
弯起的眼睛里溢出一些笑意,他抬起手,一如每日亥时钟声响起。
陆沉:“如果还是害怕,就牵着我的手。就像你初次来这里时那样。”
我笑着点头,牵住了他的手,与他一同步上回往生殿的路。
温暖自掌心传来,驱散了夜晚的寒冷,也驱散了我因没能找回记忆所生发的失落。取而代之的是陌生而熟悉的悸动,心跳声盈满天际,落在荒芜的旷野。
我忽然想起许多事,受伤时轻柔的包扎,教导时温煦的嗓音……连同没来由的欢喜和期待。
我意识到,我大概是有些喜欢陆沉的。
喜欢,信任,依赖……他身上有许多牵扯着我情绪的丝线,让我只要在他身边,就能做到许多想象之外的事。
我犹豫再三,于陆沉焚香之时,从怀中掏出那枚从人间买回来的梳子,放在他的桌案上。
这把梳子的意义,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我想,当他看到的时候,应该就会明白我的心意。
次日,我如往常那样修好了无字碑。路过忘川时,正巧看见黑白无常坐在树上打闹。我轻手轻脚地靠近,想吓他们一吓……
我悄然来到树下,从地上捡起一枚小石子,正要扔向他们身后的树丛,却在看清他们手中把玩之物的瞬间,停下了动作。
他们手里的,正是我送给陆沉的那把梳子。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失落似忘川之水陡然上涨,几乎要将我吞没。
他竟然将我的礼物赠与了别人,原来,他并不喜欢我。
这个念头盘桓在我的脑海中,在我与陆沉如往常一样坐在一起时,依然不肯安静下来。
手中的心经第三次抄错换了新的黄纸,陆沉放下笔,偏头朝我看来。
陆沉:“是今天的茶点不合胃口吗,我让判官去换一些来。”
我:“茶点很可口,不必劳烦他们了。”
陆沉:“那是还在为业镜的事烦恼?”
我:“并非是为了此事。”
陆沉不再尝试寻找原因,他看向我的目光带着探究,仿佛只要这样看着我,我就会忍不住自己将心事说给他听。
我也确实想要亲口问问他,想要从他那处得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我:“如果你不愿接受我的礼物,可以直接告诉我,或是将那把梳子还回来。”
即使此刻,我仍在话里为他留了方寸余地。我希望是我误会了,我希望他会亲口告诉我,这只是一场误会。
陆沉:“原来你看到了。梳子的事,我很抱歉。”
原来并非误会与差错,原来他是真的不愿接受我的心意。
我的心沉沉地坠下去,却仍盯着他的眼睛,不肯让他看出端倪。
我:“陆沉,你可以拒绝我。但我希望,你至少可以对我坦诚些。”
他沉默了片刻,案头灯烛倏忽跳动,让我错过了他眼底的情绪。
陆沉:“如果我告诉你,站在你面前的,并不是全部的我。而这样的我无法对你做出任何回应。”
我:“那就让我看到,让我看到那个真正的你。”
陆沉:“只怕到时候,你会恨我。”
我:“我为什么会恨你?”
这次他没有再说话,像一道沉默的影子。
可我已然明白他的意思。
我:“好,我知道了。”
我抑住难过,尽力让嗓音听上去与素日无异。
我:“你放心,无字碑我会继续刻下去。调查天尊的事,我也会继续帮你。毕竟抛开感情不说,我们还是不错的合作伙伴。”
我朝他笑了笑,不用猜也知道,这个笑容一定很苍白。
我庆幸在情愫尚未变作更深的爱之前向他问出了这个问题,而他给了我明确的,让我可以放弃它的答案。
在那日之后,我还如往常那样,继续每日刻着无字碑,又刻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与陆沉仍在亥时见面,他仍会教我护身的术法,我仍会在他身边抄经,偶尔帮他处理简单的政事。
我已经可以平静地注视他的眼睛,尽管每次对望时,我仍能听见自己汹涌的铺满天地的心跳。
无字碑就要刻满了,或许很快就到了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刻下今日的最后一个名字,却忽然发觉,这个名字我曾刻过。
我对无字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了如指掌,而同一个名字绝不可能出现两次。
我:“难道这无字碑出了什么问题?”
我急着去往生殿寻陆沉,门虚掩着,我像往常一样轻敲了两下便进去了。
我:“陆沉?陆沉……”
我绕到屏风后,却不料他正倚在浴桶旁休憩,有些惊讶地朝我看来。
湿润的长发沿着肩膀滑落,晶莹的水珠不时滚入氤氲的雾气之中,激起久久不散的涟漪,如我骤然起伏的心潮。
我愣了许久,才想起红着脸躲回屏风之后。光透过窗棂又透过屏风,我见他站起身的剪影,有些慌张地偏过头。
我:“我不是故意的。”
他总不会以为我是爱而不得,才会故意在他沐浴时闯入,企图占他便宜的吧?
陆沉:“无妨。如此急切地闯入,一定有你的原因。发生什么事了?”
我:“我发现无字碑上出现了一个重复的名字,叫“无际生”。”
陆沉:“同名同姓的人有很多,你确定是同一个人吗?”
我:“虽然无字碑上不乏有同名同姓的人存在,但每个人的八字是不同的。但他们却完全相同。”
这个同名同姓,甚至连生辰八字也相同的人,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两次呢?
我:“无字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我亲手刻。上去的,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块石头。我一定不会记错。现在只要你确定你是否记错,是否给了我重复的名单。”
陆沉:“这些名单并不出自我的记忆,而是被封印在忘川河底的魂魄的名字。所以不存在我记错的可能。”
陆沉曾说过,无字碑是为超度亡魂所建。我每刻下一个名字,就会有一个亡魂被超度。
如果是这样,在我第一次写无际生的名字时,他就应该已经渡过忘川,进入轮回,不该像现在这般再次出现在名册上。
陆沉顿了顿,我听见一阵衣料的摩挲声。
陆沉:“这件事不太寻常,需从长计议。”
此事似乎有些不太寻常,无论是无字碑的异样,还是陆沉的反应。
回到住处,我仍思索着整件事。桌几上坠下一汪凝固的烛泪,我打了个呵欠,忽然感觉到一阵困意。
眼前的景象渐渐沉入黑暗,像是梦,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朵黑莲。它静静地开在忘川之上,似是将晦夜生做了蕊瓣。
我被吸引着走向它,四处皆是混沌的黑暗,我感到有一双眼睛悬在空中,它凝视着我,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它。
一个清晰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回响,只要踏入忘川之中,我就能找到它……昏然之际,身体已然没入冰冷的河水。
灼烧的痛楚瞬间传遍全身,仿佛永远也不会停止。河水灌进我的鼻子和眼眶,手脚绵软,使不出一丝气力。
微弱的星芒在水波中渐渐熄灭,无尽的疲倦和虚脱包裹住我。难道就要这般永远留在忘川河底了吗?
陆沉:“快回来!”
是陆沉在唤我。声音自很远的地方传来,隔着水声,我却仍是听出来了。
眼帘生出些许气力,我睁开眼睛,隙光中一道模糊的身影正朝我而来……
他的手臂揽住了我,温热的身体变成渡我的船。随即柔软的触感贴上我的唇,若有似无的沉香气息沿着我的血脉四处流淌。
他的舌尖舔过我的唇珠,一下一下好似安抚。我翕动着想要睁眼将他看清,下一刻他的掌心却抚上来,将我的视线遮挡。
动荡的流水之中,那种被我压抑了许久的情愫恍若挣开锁链。报复似的,我用力咬了一下他的唇,尝到些许血锈……
河水从我们身上流泻而下,冷冽的风掠过我们湿漉漉的衣襟。我靠在他的怀中,发觉他已将我从忘川中救了出来。
他总是在危急关头出现,他的声音会让我感到安定。
我:“陆沉……我怎么会在这里?”
陆沉:“我带你回去。”
陆沉将我带回他的往生殿,他步履很快,气息也不似寻常安稳。我强撑着精神仰头看他,却望见他唇上那一点模糊的伤痕。
像之前许多次那样,他为我疗着伤。只是我们从未靠得如此刻这般近,湿润的衣襟贴在一处,连气息也彼此重叠不分。
水珠自他的额发滚落,淋湿了我的眼睫。我悄悄抬眸,毫无征兆地撞进那片平静又深不可测的眼波中。
他的手臂似乎被花茎上的刺划伤了,一道长长的伤痕横过手腕。血被水晕作浅淡而飘摇的红,滴到我的裙摆上,好似一瓣落英。
我:“你受伤了。”
他却轻轻抚摸着我的发丝,摇摇头,示意我无需担忧,他并无大碍。
我仍要说些什么,却昏昏沉沉地睡过去,梦中似有谁的指尖轻柔若风,抚开我的眉心褶皱。
再次睁开眼睛时,身上已经换了干爽的衣物。陆沉坐在我身侧,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也不知他看了多久。
陆沉:“还疼吗?”
我:“不……”
话到了唇边却被我剪断,我本想像往常一样怕他担心说不疼的,此刻却忽然不愿如此。
我:“疼,浑身都疼。”
他的眉头忽然升起一抹不常见的愠色,我尚未来得及细看,忽然跌入了一个温热的怀抱中。
他的手臂并不用力,却有些僵硬。好像直至此刻他仍在克制,克制担忧、恐惧或是其他更为深邃和复杂的情愫。
陆沉:“这样呢?”
我摇摇头,用尽全力回抱住了他。
唯有重叠的不分彼此的心跳,才能让这颗空荡荡的不断向下坠落的心停靠。
我:“我为什么会这样?”
陆沉:“是梦魇,有人利用梦魇之术引你入忘川。”
普通魂魄无法承受忘川河水,会遭受蚀骨之痛,形神俱损,直至魂飞魄散。
我:“可是究竟是谁要害我呢,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陆沉:“天尊,他想阻止你继续修无字碑。”
我:“无字碑不就是一个超度亡灵的石碑吗?天尊为什么要对我下手?”
陆沉顿了顿,他的声音字字清晰,如滚珠般落入我的耳中……
我:“因为,无字碑就是真正的生死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