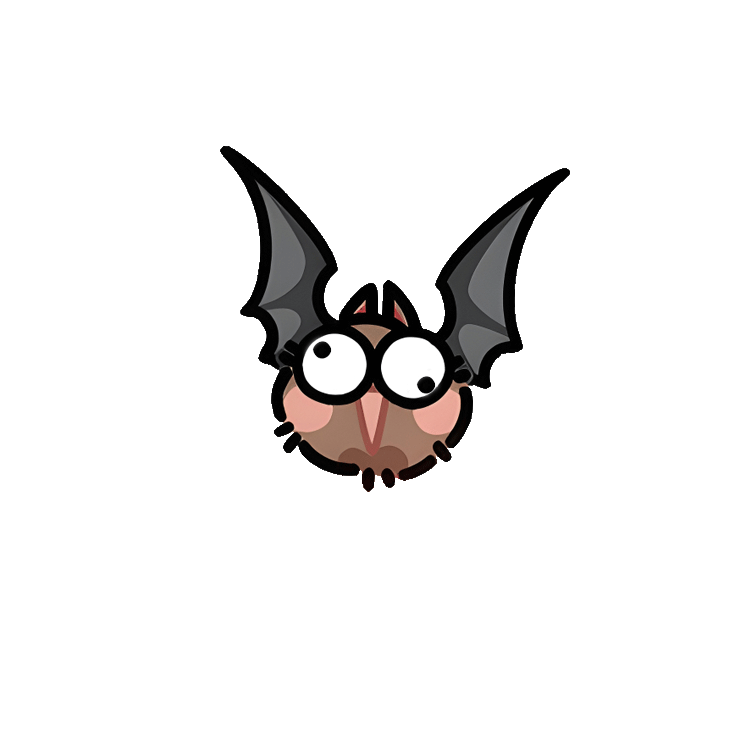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软禁❈
笃笃笃——房间被敲响。等了一会儿,见屋内没反应,站在门口的男人又轻敲了几下。
周严:“ 小姐?”
我:“……!”
我从梦中惊醒,头顶的灯不知何时亮了,让人一时睁不开眼。
窗外漆黑一片,风刮得响亮,连窗玻璃都在震颤。时间仿佛突然被按下了快进键,上午知了还在叫个不停,晚上已经有了萧瑟的兆头。
不过这和我没关系,哪怕外面刮台风下冰雹我都不用担心,现在的我出不去这间房。
周严:“小姐,您今天晚饭吃太少了。我准备了饭菜,放在门口,您饿了可以吃一点。”
我:“陆沉还是不放我走吗?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挣扎着翻身下床,用力敲了几下门,又把耳朵贴上去。可等了好一会儿,门外始终寂静无声。
失望地回到床上,我正准备吃药睡下,周严的声音却忽然传来。
周严:“抱歉,但我暂时还不能让您离开。您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不出意外的回答,这几天每次被问急了他都这样说。我知道他还在外面看着,索性伸手把灯关了。
我:“我要睡了,你拿走吧,吃不下。”
屋内一下子暗了下来,没了光的挤占,回忆争先恐后,从寂静无声地夜里浮出来。
这是我离开陆氏城堡的第三天,也是我被陆沉“关”在这里的第三天。
只是那天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大概是伤心过度吧,大脑自动开启了保护机制。
能记起的只有陆沉最后那句“对不起”,还有在确认他安全后,我故作潇洒转身离开的画面。
醒来后我便在这里了。
一间非常普通的出租屋,和我住的那间很像。以致于睁眼的瞬间我甚至怀疑那天是否真的存在过,而陆沉此刻还在楼下等我。然而也只是一瞬间。很快我便看清了这里的布置,不是我家。
两室一厅的格局,正对着的那间房房门紧闭。客厅摆设简单却流露出几分温馨,应该是有人长期居住的。
我:“这是哪?”
我没有疑惑太久,很快就从窗外得到了答案。熟悉的楼栋、熟悉的中心花园,这间房子居然就在我租住的小区内。
只不过我租的在东区,这里是西区。两个区都有各自的入口和出口,平日里并无交集。从这里的窗户望出去,也看不到我住的楼栋。
换言之,我现在在一个陌生“邻居”家里。
渐渐恢复意识的我开始感到害怕,转身之际撞到了一架看起来价值不菲的老式座钟,摆针剧烈晃动,房间里回荡着铿锵声响。
我连忙捡起,还没放好,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处湿漉漉的屋檐。红豆冰的叫卖声,人声、雨声叠加在一起,往事就这样涌了上来。
而屋檐下的那个人,正望着眼前的大雨出神,目光空茫,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陆沉?!”
手指猛地一跳,下意识就松开了座钟,画面也消失了。
这是陆沉的房子。刹那间我有了这个确切的念头。把我从城堡带走的人应该也是他。
我:“难道是上次我参考房子后,他也觉得这里离公司近,所以租了一套?”
这个猜测甚至还没闪现就被我否定了。他是CEO,不需要跟我一样考虑通勤问题。这也不是什么高档小区,他没有居中的必要。
那么答案是否只剩下一个?监视我,接近我。
心里顿时复杂得难以言说,一股强烈的冲动让我想立刻跑到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清清楚楚、痛痛快快问个明白。
为什么跟我住同一个小区?不是说好两清吗?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这里?
为什么离开了还要回来救我,让我无数次产生你很在乎我的错觉,又为什么在我回应后一次次推开我?
为什么每次遇到困难你都会在身旁,而那些陪伴又是那么温暖动人?
为什么告诉我那么多其实你自己都不愿谈起的过去,却总是回避每一个“以后”?
太多的“为什么”。填满了我们间的空隙,制造出亲密无间的错觉。此刻把它们一个个都拿出来,才发现原来相距遥远。
都是错觉而已。
现在先来,其实他根本没有承诺什么,反而总在叫我别相信他,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一厢情愿。没有谁理应为他人的错觉负责。
而在我提出两清后他什么都没说,这应该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吧。在纠缠下去只会显得我很可悲。算了。
我闭上眼,用力深呼吸,任由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在脑海错乱交叠。其实就这么断了也好,不用再患得患失小心翼翼,不用被他欺骗,自尊也能捡起来。
或者说,本就该这样。我们的亲密有多少是构筑在他处心积虑的接近上,如果没有那些,我们只会是两个陌生人。
什么都没失去,就是回到原点而已,我告诉自己。放下吧,别执着了。
然而越这样想,似乎就越舍不得,甚至有种强烈的心悸感。我完全没有得到斩断一段关系时的轻松与舒畅,应该要有这种感觉的不是吗?
更无药可救的是,我竟然不死心,还想问他要一个答案。
思绪像一团乱麻斩不断,更无从理起。我决定先离开这里,回家一个人静静。
周严却把我拦了下来。
周严:“抱歉,您还不能走,手机也暂时不能还给您。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我不清楚。”
他说,这是陆沉的命令,公司那边已经帮我请好假了。而他会住在隔壁,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找他。
我:“所以这是软禁?!”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试图从他表情里找出一丝丝玩笑的意味,可什么都没有。
我:“为什么?陆沉还有没有说别的?暂时不能离开——是因为外面有危险,我必须得留在这儿?还是……”
我几乎想到了所有合理的解释。
周严看我的目光里忽然多了点同情,但他依然没说话,只是将视线转向别处。这种不对劲的样子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还是他出了什么事?!”
我一下子攥住周严的衣袖。
我:“那天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见他!”
我努力控制住情绪,告诉自己陆沉不会有事,那天不是都确认了吗?可无论如何也无法冷静下来。
我:“你说句话啊!”
周严:“抱歉,不能离开的原因老板没交代。但是请放心,老板真的没事。那天他将您送来这里后才离开的。”
我:“真的?”
我依然不放心,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直到确认他不是在安慰我也没有在撒谎,才迟疑着松开了手。
我:“所以……只是他想把我关起来,对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但就是这么认为了。而周严也没再开口,更加漫长的沉默中,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我:“他怎么可以这样。”
周严始终都是那句话,抱歉。
其实之前的一切并没有让我产生多少愤怒的情绪,更多是难过。但这一刻,我真的生气了。
我用了很多办法让他放我走,但无论是威胁还是央求统统无效。动手我也不是他的对手,甚至在我说了绝食后,他还是面无表情,丝毫没有反应。
我气得抓起手边的靠枕就朝他砸去。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带上门离开。而我站在原地,花了很久才让自己从愤怒里走出来。
我怎么忘了,从来都是这样,只要是陆沉想做的事,他会不惜任何代价。是过去我把自己在他心里想的太重要了。
对他来说,我应该就是某种工具吧。
那么他把我关在这里,是因为我还活着,还有利用价值?还是因为救我打破了他原定的计划,所以必须把我看住,等待时机成熟,再送过去?
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恶意猜测。我必须想得越阴暗越好。
因为只要闭上眼,他在我求救中转身离去的画面就会死死地占据脑海。
因为我发现即使这样,即使他把我骗得团团转,他动过罔顾我生命的念头,我醒来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怎么样了?
包括那天最后他让我离开,我一直在找借口回到他身边。我觉得自己简直疯了,为什么还在关心他?从头到尾他对我好,只是因为我对他有用不是吗?
可是,每每想起他站在破裂的彩窗前,用一种陌生的、悲哀的眼神质问我为什么回去时,我的内心都会动摇。
明明可以不救我的。
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就可以把我送过去。那样,他也许已经成功了。
如今回头去看,那天有太多的不寻常,绝非提前计划好的。
从认识他起,他都是不慌不忙、遇事泰然处之的,不应该这么冲动。
所以是为什么,只差最后一步,他那么聪明,不会不懂衡量与取舍。
是愧疚吗?只有愧疚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可这次我却不敢深想,怕又是在自欺欺人。
那个夜晚我辗转难眠,到天亮才有睡意。而上天似乎觉得我的处境还不够糟糕,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我生病了。
感冒来势汹汹,一下午从轻微鼻塞发展到有点呼吸困难,连翻身都费劲。身体先投降,才制定好的逃跑计划也只好就此作罢。
大概是怕落得一个照顾不周的罪名,周严立即找了医生过来。开了药,挂了点滴,还是不见多少好转。
我心里清楚,这场病最大的病因是我和陆沉的关系,只有我自己走出来才行。
风在窗外呼啸,似乎越来越猛烈。每当有睡意围过来,总会被乍起的风声吓跑。
我不喜欢这样的天气,好像全世界都在狼狈挣扎,却又只能清醒地无助着。
我:“别想了,吃完药就早点睡吧。”
我拖着发烫的身体爬起来,吞完药片,忽然在没拉窗帘的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窗上的女孩呆呆地望着我,眼下是两大团乌青。过去那些神采不见了,嘴唇上的笑也不见了。让我感到陌生。
我试图咧开嘴,想让她快乐一点,然而只是徒劳。
其实没有很难过,只是有点同情。同情那个陷在错觉里还不肯放手的自己。
直到药效渐渐起了作用,我睡着了。然后,又一次梦见了陆沉。
梦里,我们在沙滩席地而坐,风很轻,浪花时不时拍打在脚上。我们紧紧牵着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说到日落,火红的夕阳浮在水面上。
我送给他晴天娃娃,他很高兴地收下。我又忍不住问他,以后我们把世界上的海都看一遍吧?
他没说话,只是眷恋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脸上的神情让我以为我在哭泣。
画面暗了下去。我睁开眼,发现眼泪果真淌了一脸。
原本,我以为那天会是我们新的开始。怪只怪夕阳太美丽,美到让人忍不住期待苦尽甘来。
这一觉睡到了傍晚。太阳已经下山,映得窗户橙红一片。我走下床,突然发觉身体轻松了不少。
盯着远处的云霞发了会呆,忽然的,我想起了很久以前陆沉跟我说过的一个词,魔法时刻。他说黄昏是魔法时刻。
当时我还很懵懂,此刻长久地凝望着昼与夜交界的地方,我的心里涌起了从未有过的惆怅。一种空茫的、要失去什么的感觉笼罩着我。
我想我有点明白陆沉说的魔法指什么了。
黄昏拥有把世界上一切尖锐、赤裸的情感变得温吞的力量,但那种力量不是谅解、宽容或者释怀,它没那么善良。
那是一种“算了”,一种人类至今都不曾明白的东西。
在神明的俯瞰下,一遍遍细数自己还有什么东西可失去,人会变得平静,最后不为所动,如此这般,我们才可以和自己天长地久下去。
我突然也明白了,为什么他说如果喜欢一样东西,不一定非要拥有,远远看着或许才是拥有。
只有得到的人才有资格害怕失去。我从来不曾想现在这样理解他,也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渴望从未理解他。
我:“就当成一场病,放下才能好起来。”
凌晨时分,伦敦罕见地起了大雾,一个朦胧的身影从浓重的灰色里走出。
利落的黑色冲锋衣,皮革手套,仿佛生来就是穿梭于黑色的猎人。
与他一同走出来的,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
老人一身得体的手工西服,礼帽下露出花白的鬓发。尽管年事已高,双目却炯炯有神,举手投足间透着股威严之意。
虽是长辈,但他拒绝了陆沉的搀扶,手杖在地面敲出规律的声响。他早就听闻国内血族出了位天赋极高、运筹帷幄的继承人,只可惜他向来不认同那个家族奉行的观念,便没放在心上。
后来听说了更多他的事。
听说他是第一个人能在陆霆的眼皮子底下长到成年的继承人,甚至能与陆霆分庭抗礼,这让他起了好奇心,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
直到去年冬天在南部的那场狩猎。自己遭遇埋伏,所幸及时得到救援。哪怕明白他是带着示好的目的前来,但这份示好却并不令他反感。
他直觉这位年轻人不似传闻中的冷血无情,在后来的私人宴会上,这份直觉也得到了印证。
一首大提琴曲悠扬哀婉,让他想起了多年未曾回去的家乡。
北部家主:“Lu,你刚才说的陆霆的行踪我会多留意。一旦他出现在北部和南部境内,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陆沉:“多谢。”
北部家主:“不用跟我客气。能够拿下南部这块宝地,有你的功劳,你是我们北部重要的盟友。”
陆沉礼貌微笑,结果身后仆从递来的手帕,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
北部家主:“不过,你刚才说老家主的魂魄现在在陆霆手上?”
陆沉:“嗯。当时家主的魂魄遭到重创,有溃散的迹象。
我原本以为叔叔出手夺走是着急回城堡,修复魂魄。
可我来到地下,却没见到一个人。
我又去了叔叔的宅邸,大门紧闭。担心家主有什么不测,我硬闯了进去,接过还是没见到人。
后来听说叔叔早就离开了光启。我猜他可能会来这里,毕竟他跟西部家主私交甚好。”
听到魂魄二字时,老人额头纵横的纹路深深地皱了起来。他沉思片刻,严肃地点了点头。
北部家主:“Lu,我跟你有同样的猜测,但不仅仅是这个原因。”
陆沉:“愿闻其详。”
北部家主:“你知道英国的血族其实并没有经历过镇压这一劫吗?”
陆沉脚步放缓,这与他之前从家主口中得知的事情并不完全符合。
而老者也没有继续说下去去,他在犹豫,犹豫是否该全盘托出,他害怕会改变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命运。
陆沉:“您放心,无论您说了什么,我都会当成秘密保守。”
老者深吸了一口气。
北部家主:“现在全英国知道这些的,大概也只剩我们家族了。这还是我祖父在世时告诉我的。
当年血族还是神,因与造物神交好,没有听命销毁由她创造出来的人类,惹怒了创世神。
将他们镇压进海底,但有一部分在火神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就是我们的先祖。
你应该知道,现在光启市的血族是因为自愿接受天谴,才在百年前从海底被放出。
可奇怪的是,我们的先祖并没有遭受天谴,但在岁月的演变里,也出现了血族的特征。
这至今是个未解之谜,也许等我入土都得不到答案了。
所以比起你们,这里的血族天赋更弱,感知力也是。
接近于人类。光启的血族为了存续研制了容器,这里的血族为了天赋,也动了同样的心思。
四十年前,他们研制出了一种药水。能把同族的灵魂吞噬,天赋也会因此转移。”
陆沉始终平静地在听老人讲述。
北部家主:“你不惊讶?”
老人欣赏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陆沉:“世界上的故事无非就是那么几种,尤其是为了权力。不新鲜。
所以您觉得陆霆这次来,是为了吞噬家主的魂魄?”
北部家主:“我的猜测。”
“我知道了,谢谢您的提醒。
您可以告诉我这款药水的研究所哪里吗?或者您是否认识的研究人员?”
北部家主:“我们北部并没有参与这件事,知道的很少。
研究院的话,我记得攻克这一难题的是位杰出的女科学家。
我家里应该有些资料,不过年代久远,需要的话,你跟我回去一趟。”
陆沉:“谢谢,您帮了我大忙。”
陆沉拉开车门,待老人入座后,他正准备上车,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紧急的脚步声。回过头,几位仆人正向这边匆匆跑来。
陆沉:“怎么了?”
仆人:“家主,陆沉少爷。刚才接到West夫人的电话,她说在东部看到了陆霆的踪迹。”
陆沉:“东部?”
陆沉垂下眸。在他仅有的几次印象里,东部家主脾气古怪,向来与其他血族不合,也从未听过他与陆霆有什么私交。
难道是自己疏忽了?就像那天……陆沉按在车门上的手指蜷了一下。
他想起那天的黄昏,自己前所未有的失控。而她奋力挣开怀抱,退得远远的,仰头看着自己。
那双蓄满泪的眼睛不再包含怜悯与天真,只剩下用平静极力掩饰的痛苦。她慢慢地转过身去,每走一步都在发颤,却又那样用力、坚决。
仿佛一只奄奄一息的小兽,终于明白忠诚的爱只能换来伤害。绝望使她不得不捂紧伤口,头也不回地奔向丛林深处。
他突然心里一紧,失去的预感模糊了眼睛。等追过去,女孩已经倒在陆霆面前。
陆霆似乎认为是他导致了家主重伤,暂时没有注意到女孩身上不寻常的力量。
他松了口气,却也因此忽略了陆霆故意输给自己真正的目的,等意识到不对时,陆霆已经带走了家主的魂魄。
北部家主:“这东部老头自从女儿跟他断绝关系后,就再没出现在我们面前。Lu,需要我安排人去调查吗?”
陆沉:“不,您只需要告诉我,吞噬灵魂需要多长时间?”
北部家主:“如果快的话,几天就能完成。”
陆沉低下头思考。女科学家、东部家族、断绝关系的女儿……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关联。
尽管这关联只是自己的推断,并无证据,但他不想放过任何一种可能。
北部家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的确有这个可能。一旦陆霆成功,他的天赋可能会强大到超出你我的想象,你要做好准备。我派直升机送你。”
陆沉:“谢谢,但这不够快。
我有个忙想请您帮一下。您在东部的军队,可以借我几个人吗?”
一开始老人还有些不解,但很快他明白过来,笑着点了点头。
北部家主:“注意安全,你身上还有伤。要是再受伤,我女儿会很伤心的。我等着你回来切磋棋艺。”
陆沉:“那我先告辞了。”
他转身再次没入大雾中,纵身一跃。整个人仿佛一种敏捷的狮鹫,无声地跳上了教堂高耸的塔尖。
那速度太快,已经超过肉眼捕捉的上限,唯有衣襟上的纽扣反射出月亮的光,在夜空中留下短暂的红色光点。
陆沉朝着东部的方向飞速跃去。
——位于伦敦东部的废弃实验室——
身穿白色制服的中年女人正聚精会神地操纵着手中的仪器。仪器中央躺着一个男人,一团团血肉在“咕嘟”声中化作血雾,注入他的体内。
随着血雾的注入,废弃粘液开始从他毛孔排出,滴滴答答,淌了一地。
直到最后一滴粘液落下,他猛地睁开眼,瞳孔瞬间收紧,围绕在他周身的玻璃骤然碎裂。
女人满意地站起,正欲宣布魂魄转移成功,突然咔嚓一声,原本还在她手中的金属物直直刺入胸口。
不出两秒,她整个人就碎成了一堆血块,散发出令人恶心的铁腥味。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已经坐起身,他一双猩红的眼半眯着,饶有趣味地盯着地上那滩自己的杰作。
陆沉到的时候,地上的血块已经化得只剩下了眼睛,睁得很大。
陆霆:“你果然来了,比我预计的更早。但真可惜,还是晚了。”
捕捉到陆沉脸上一闪而逝的震惊,陆霆笑着一步步走近。
陆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趁我不在拿到了万甄,但我告诉你,活着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你听——有了那老东西的天赋,我这颗心脏跳得多有力。
我等着一天实在太久了,叔叔还要感谢你,替我实现心愿。你放心,送你走之后我会把那个女人一起杀了,就当是叔叔的谢礼。”
陆沉:“家主的葬礼还没开始筹办,叔叔就等不及去陪他老人家了吗?”
就是这副虚伪自大的模样最让他讨厌。陆霆忍不住抬起手指,月光下,无数只罕见的血色蝙蝠化作一股疾风,向陆沉袭去。
然而陆沉并不闪避,任由那些蝙蝠缠裹,在皮肤上留下道道可怖的血痕。
他依旧稳稳向前走,一步一步逼近陆霆。只是每走一步,他的瞳色就暗一分。
竟然抵御住了家主的武器。陆霆不得不承认他之前有点小看这位侄子。
于是他定了定心神,压低嗓子笑起来,可那笑声却不像从喉头发出的。
在渗人的低音里,实验室迅速震颤起来,试剂瓶、仪器接二连三地倾倒,砸开满地刺耳的碎裂。
锋利的玻璃碎片如横斜而下的急雨!
陆沉侧身闪避,然而那攀附在脚踝的蝙蝠却不断紧缩,牵动起他尚未愈合的伤口。
陆沉:“……!”
刹那间,碎玻璃直插入陆沉胸口,周遭一大片皮肤顿时变得糜烂,鲜血喷涌的同时,血肉也碎成了块状直往下掉。
露在外面的玻璃上映出他微蹙的眉。
陆霆咧开嘴角,随着弧度的扭曲,那玻璃又深了几分。
陆霆:“你不会是快要死了吧?怎么办,我都还没用上一半的实力。”
陆霆的手背上开始显现出更为罕见的血色纹路。他不过是扬了扬手,居然涌来了更多蝙蝠,它们争先恐后地吞食着陆沉掉下的血肉。蜿蜒的黑色无孔不入,与陆沉的影子互相纠缠。
鲜血滴在大团黑影上,黑影兴奋地抖动,疯狂吸取养分。
家主就是这样吧,在绝望和痛苦中,被陆霆一点一点地吞噬。
而此刻,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陆沉身上。他所能使用的天赋跟现在的陆霆相比微乎其微——这是来自对方赤裸裸的血统压制。
短短数秒,黑影已逼近他深红色的双瞳。
陆霆正要上前,忽然,一只蝙蝠直直坠落,在地板上“咚”的一声,挡住了去路。
继而成千上万的蝙蝠闯入实验室,夜风簌簌作响。
有人破窗而入,陆霆的能力尚不稳定,稍稍分心,那团黑影便松开了几分。
身体陡然失去依靠,陆沉趔了半步,前额渗出细密汗珠,不过好在还能稳住呼吸。
趁双方交手间,一小队人马亮起信号,迅速掩护陆沉遁入无边月色中。
空旷的荒地上,只剩下陆霆的身影和满地狼藉。
他望着陆沉消失的方向,脸上最轻蔑的表情,渐渐的,轻蔑变成了迟疑,最后又变成难以置信。
他不知道这位天赋强如怪物的侄子,是什么时候与北部家族结识,又做了什么居然获得他如此鼎力的相助。
尽管已将家主的天赋转移,但冥冥中他仍感到一股寒意。他伸出手,在虚空中一抓,整间屋子在瞬间化为粉尘,消散于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