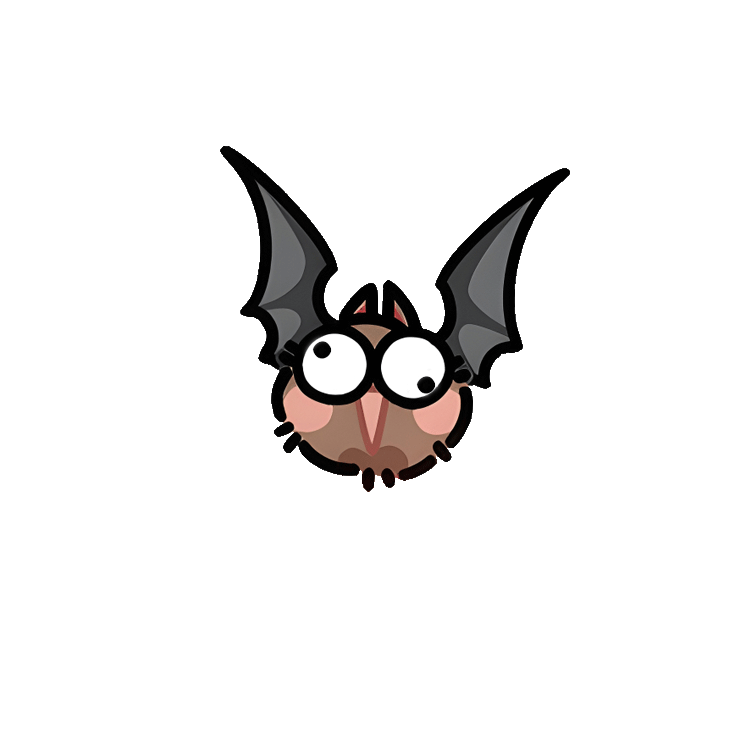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眠于玫瑰Ⅰ❈
一枝修剪好的玫瑰递到我面前,我熟练地接过,将它插进花瓶中羊齿叶的旁边……
新的花束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正在准备一场宴会,是陆沉设的宴,地点是在一艘旧的轮船里。
而宴请的对象,是泽维尔。
陆沉:“很漂亮,你想让它出现在哪里。”
每一个桌角都已经摆满花束,我想了想,指着一处座位,它的前方还有些空荡。
我:“那里吧,你觉得怎么样?”
陆沉:“还不错,那里很空,刚好缺一束花。”
他把花束放在我指定的位置上,又抬头望过来,静静等待我的评价。
我:“唔,偏客人右手边,可能会挡到他用餐。”
我又物色了一处更远一些的空位,抬起的手指刚放下,花束便已经被他换到对应的地方。
我:“还是放这里比较好。”
隔着满桌盛放的鲜花,他同我温柔地对望,含笑的嗓音也沾染了花瓣的柔软。
陆沉:“好,还是你想得周到。”
和煦日光渐渐西斜,一整个下午过去,陆沉都在和我做着类似的事。
搭配鲜花,摆放烛台,挑选酒杯,敲定菜单……凡是我的建议,他都耐心地依次执行,把餐厅装点为我们希望呈现的模样。
我们庄重地去做这一切,一起确定每一处细节,俨然一对默契配合的男女主人。
给泽维尔的邀请函,也是我们一同设计和执笔的。就像一对邀请老朋友前来叙旧的新婚夫妇,在落款中并排写下两个人的名字。
所有琐碎事务都变成印证亲密的细节,让我由衷地开心,而陆沉似乎也乐在其中。
不过,泽维尔能不能称得上是陆沉的老朋友,我也不得而知。
就像我同样没有想到,在看到那天的骇人场景后,陆沉会决定用一次宴请来解决,但又莫名觉得这样似乎很好。
我:“你为什么想要宴请泽维尔?”
手中的餐巾有些不听话,始终折不出我想要的样子。
而陆沉自然地接过,餐巾在修长手指间来回翻折,变成一朵玫瑰。随后,他又把这朵玫瑰放在了我的餐盘上。
陆沉:“我从前觉得,一段历史会引起我的兴趣。后来我发现,比起历史本身,更值得追问的是历史里的人。”
他的回答有些故作玄虚,我不满地拽拽他的衣袖,陆沉只是笑着握住我的手腕。
陆沉:“我以为经过那天,你不会想要见到他。”
我:“有点吧……”
那天的场景的确很有冲击力,以致于回来的路上,我只要闭上眼睛,就又会看到那间囚牢。
恶心的感觉,后半夜渐渐消退,我让陆沉替我烤了一块舒芙蕾。
但我也记得,陆沉看到那些画面时的神色,他寂静得像是在看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或许在某些时刻,他也把他看作了同类。
我:“有点吧,但还是兴趣更大。”
餐厅的门传来几声轻叩,周严走了进来。
周严:“老板,你邀请的人,已经来了。”
陆沉:“好,去准备吧。”
周严点点头,带着一贯了然的沉默,转身离开了。
随后船只配备的老式电梯上来了,在我们面前停下,泽维尔出现在闸门之后。
他迈动脚步时有片刻的迟疑,浑身姿态都很紧绷。他换上了合体的西装,头发和胡须被潦草打理过,却难掩枯槁。
令我惊讶的是,他仍然在遵守赴宴的礼仪,将怀抱的红酒递给陆沉。陆沉接过,微笑着向他伸出右手。
陆沉:“欢迎。”
泽维尔也短促地笑了一下,握了握陆沉的手。
一旁的周严走过来,接过陆沉手中的酒。他擦拭瓶身后,轻轻开启软木塞,把酒倒入醒酒器中。
陆沉:“谢谢你带来的餐前酒,它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先吃些开胃菜,聊聊天。”
泽维尔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餐厅,相比之下,陆沉表现得坦然而从容。
他走到我身边,帮我拉开座椅,让我先坐下。
邀请泽维尔入座后,陆沉也坐在我身旁。我们面前各摆着一小盘佛罗伦萨饼干,其中有杏仁片和树莓,底部抹上一层咖啡风味的奶油酱。
其实这不符合正餐礼仪,但我和陆沉很喜欢这样搭配。咖啡会中和饼干的甜腻,清爽的果干和一点黄油香气也能熨帖地唤醒味蕾。
这道很有主人风格的餐前甜点,让宴请多了几分随意和亲切的氛围。泽维尔看着它们,若有所思。
泽维尔:“很多年前,我也曾参加过你们陆氏的晚宴。我记得那时我五岁。”
陆沉:“是吗?抱歉,我对你没有什么印象。”
泽维尔:“很正常,我又不像你,站在家族视线的中心。更何况,和现在的我相比,那时候的我瘦弱得像一只随时都能被风吹走的小绵羊。
可我记得你,你比我年长几岁,坐在餐桌的角落里,一声不响地吃饭。”
泽维尔:“整顿饭的过程中,你一次都没有笑过。我当时在想,一定是因为菜太难吃了。”
陆沉:“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些是什么样的菜。”
陆沉的语气很平和,与平日和人交谈无异。
泽维尔终于笑起来,看上去比刚进来时轻松了一些。
泽维尔:“盘子里只有一些五分熟的蔬菜和红肉,连一块蜜瓜都没有。我在你们的城堡里待了三天,连着三天。每一顿几乎都是一样的菜单,实在是无聊透顶。
我们的家族当然也会遵循血族古老的传统,但仅限于一年中的那几个节日。我没想到竟然有人是会一直这样吃饭的。”
我听得有些出神,原来那时候的陆沉在面对客人时是这样的。
陆沉:“看来那是一段不怎么愉快的旅行。希望今天这一餐能让你满意。”
见酒已经醒好,陆沉正要起身,但泽维尔却先一步拿起了醒酒器。
泽维尔看着陆沉,没有松手,似乎有些坚持。
陆沉点点头,任由面前的客人为我们倒酒。
浓郁的暗红色液体流入杯中,我想起这瓶酒是泽维尔带过来的。
他应当是有目的地在寻找陆沉,倘若暗中采取什么手段……看着这杯酒,我伸出手去打算用天赋查看。
然而,陆沉已经举起了酒杯。
我:“主人怎么能先喝呢……我是说,客人都还没有举杯。”
我想要拖延,但陆沉却用平和的眼神示意我放心,转而将杯口的方向对准了泽维尔。
陆沉:“祝我们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陆沉……”
他将那杯酒尽数喝下。
泽维尔笑了,也把酒倒入自己的杯中,喝下了大半。
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指尖传回的画面也很正常,我庆幸一切是我多虑,悄悄舒了口气。
气氛渐渐放松下来,他们也有来有往地交谈着,似乎和以往陆沉参加的那些应酬并无区别。
他们谈起这里冬季阴雨连绵的天气,聊警局里错综而嘈杂的局面……他们谈比兰,谈工作,甚至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生活。
我才发现陆沉对比兰很了解,他熟悉餐馆里的时令菜品,也通晓混乱不堪的本地势力……一点都不像他所说的,只是短暂地来过。
餐前酒喝完,温热的汤盘被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
陆沉面前是一道奶油蘑菇汤,而泽维尔的是调味更为复杂的洋葱汤。
陆沉尝了一口汤,随后笑着看向我,因为他面前的那道汤是我做的。
陆沉:“很好喝,这一定是我今晚最期待也最喜欢的一道菜。”
我:“真的?你不是在恭维我吧?”
旁边的泽维尔也颇为期待地喝下一口汤,眉头忽然皱起,勉强咽下后,一脸困惑地转头,想对陆沉说些什么。
陆沉:“你那份是周严做的,他对于洋葱汤很有心得。”
泽维尔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陆沉的话堵了回去。
陆沉没有说错,周严很擅长洋葱汤,给客人吃很合适。但泽维尔眉头紧皱又有苦难言的样子,叫我有些困惑,又有些好笑。
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放松下来,忘记先前一切龃龉,感受到真正属于宴会的氛围。
但这份轻松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很快就到了主菜。
陆沉:“这道菜,是我做的。”
是一道经典菜式,慢煮鸭胸肉配南瓜泥。但陆沉做的这道多了几分别样的香气,选择的摆盘更具家常气息。
陆沉:“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代替南瓜,使用了栗子。这是我从一对血族夫妇那里学到的,虽然我做的比他们差得远。”
泽维尔沉默地盯着那道菜,呼吸略微急促,急剧变化的神色中,是我看不懂的异常。
难道,这道菜和泽维尔有什么关联?
陆沉:“我刚满十八岁的时候,去过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对夫妇家中寄宿了一夜。他们也是血族,却和我认识的血族都不太一样。他们会在门口的院子里装上秋千,还会用带露水的蔷薇花藤去装点它。
他们有个儿子,据说经常溜出去玩,一玩就是一整夜。夫妇俩商量着等他回来时,一定要狠狠惩罚他。他们为用哪种方式惩罚他而争执。一种是写完所有束雪节的贺卡,另一种则是在节日当天堆出一个两米高的雪人。”
说到这里,陆沉停了下来,用探究的目光看向泽维尔。
泽维尔依然呆滞地看着餐盘,手边的刀叉似乎有他难以支撑的重量,他没有吃饭。
陆沉:“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血族也有不那么吓人的惩罚。可这样的事,让当时的我感到恐惧。于是,那天夜里,我悄悄离开了那对夫妇的家。”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个夜晚,那个更加年轻的陆沉,把他无法理解、也抗拒接受的温暖灯火,甩在身后。
他的身形一定比现在单薄,却依旧要隐入仿佛没有尽头的黑暗,当时的他是轻轻松了口气,还是也悄悄叹息过……
反应过来时,我已经握住了陆沉的手。力度很轻,仿佛这样就不会触碰到那些血脉之下的伤口。
泽维尔的嘴唇绷成一条直线,肩膀微微颤抖,不停眨动的眼睛边缘泛起红色。
他越发剧烈的反应,使我几乎确信,陆沉提及的那段过往以及那对夫妇,与他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发现,他的情绪有多容易外放,几乎一眼就可以看懂。
最终,泽维尔选择叉起一块肉,艰难地吞咽着,可是手却还在轻轻颤抖。
或许,是因为这道菜的确与传统的做法不太一样,如陆沉所说的那样,味道也有些差别。
泽维尔:“小的时候,我很贪玩,经常被我的父亲责罚。都是一些,罚抄族训、禁足之类的小事情。”
这与陆沉所说的那对血族夫妇的故事似乎重合了。
原来陆沉去比兰那次,遇到了泽维尔的父母,去过泽维尔的家。
泽维尔:“有一次,我从森林里捡回来一只失明的猫头鹰。我的家人告诉我,不要去养一只看不见的猫头鹰。
但我不以为然,逢人便说,我的猫头鹰和别人的不一样,它的眼里有星空。”
我:“后来呢,他们允许你养它了吗?”
泽维尔点点头。
我:“你们是很善良的一家人。”
泽维尔勾了勾嘴角,可眸色却越发黯淡。
泽维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家族内部开始出现了争吵,对抗。起初只是一些玩得很好的伙伴,被禁止与我往来。后来是那些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陆氏成功了。”
陆沉没有回避泽维尔不甘而愤恨的眼神,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果然是陆氏的阴谋,用一些离间计划,让一个原本紧密的家族分崩离析。
我隐约能猜到的,通过一些只言片语,通过陆沉修撰族史的起因,通过泽维尔看陆沉的眼神。
泽维尔:“我和我的父母,遭遇了同族的追杀,躲在了一个地下室。进去前,我带上了那只猫头鹰。”
陆沉:“生死关头,为什么要带上它?”
泽维尔:“没有为什么,我只是单纯地需要一些伙伴。一些不会离开我,不会背叛我的伙伴”
突如其来的变故,年少时遭遇的背叛,不知为何,我下意识地看了看陆沉。
泽维尔:“没想到,在地下室,我们一待就是一个多月。父亲和母亲将吃的都留给了我。然后在某个夜晚,当然,也有可能是清晨……自杀了。”
他一定很痛苦吧,亲眼看着他们离开自己。光是想象,也叫人难以接受……泽维尔看了我一眼,似乎捕捉到了我此刻的心情。
泽维尔:“比起悲伤,更多的是恐惧。”
我:“恐惧?”
泽维尔:“是我从察觉到那只猫头鹰的异样开始的。我发现它会时不时注视着他们的尸体,就像它能看得见一样。
于是,我将一块饼干分成好多好多份,每天喂食那只猫头鹰。试图去阻止些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不小心睡着了。醒来时,母亲不见了一只眼睛。”
陆沉:“所以你就杀死了那只猫头鹰?”
泽维尔:“是的,我杀死了它,并且吞下了它的血肉。”
陆沉已经猜到了那只猫头鹰的结局。我告诉自己,或许是因为钟楼上那些被人弄瞎又被人豢养的猫头鹰……
我不愿再深入这个想法,只盼望他之所以猜测如此准确,是因为强大的判断力,而不是……某种隐约的共鸣。
泽维尔:“再后来,我模仿了别人的幻境,成功逃离了比兰。”
陆沉:“你不该回来。”
泽维尔点头,又轻轻笑了笑,像是在笑自己当时无法舍弃的念头。
泽维尔:“我还是回来了。比兰已经变成了一座荒城。从那之后,我们从血族的族史里消失了……”
泽维尔放下了手中的餐叉,叉子的末梢擦过盘边,发出刺耳的声响。
但陆沉却在这时,将面前的餐叉拾起。
陆沉:“而就在不久之前,你得知血族改换了家主。你打算见他,并不是为了恫吓或者复仇,而是为了请求。我说得对吗?”
陆沉身体略微前倾,目光几乎要穿透对方。
无形的威压下,泽维尔反而像是放松了一些,就像是即将坠落的绝望之人,抓到了一缕蛛丝。
泽维尔:“陆沉,我们没有什么交情。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所以,我没有理由让你为我的家族做什么。我只能想办法引你来比兰。
起初是试探。我想用这些事情,去唤醒你对当年之事的记忆。后来我发觉,杀戮虽然不会让我高兴,但它让我平静。”
杀戮之于泽维尔,是一种仇恨、憎恶、痛苦……乃至绝望的表达。
那之于陆沉呢?
如果这种极端而爆裂的方式是泽维尔的解脱,那么,陆沉又会找到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出口。
我想,这对陆沉来说,应该是很难的,反而是很难的。
在地下室里,当陆沉看到那些被囚禁、被虐待的血族时,他又在想什么?无动于衷?亦或是,与泽维尔相同的平静,甚至,是快感……
我忍不住抚上他的手背,迫切地去感受那些更为真实的温度。
陆沉反握住了我的手,指节渐渐分开,缓慢而坚定地把我的手紧攥在他的掌心。
他又看向泽维尔,语气和缓了些。
陆沉:“就算族史重写,与你的痛苦有关的东西不存于世,已经消失的人也不会再次出现。这是既定的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泽维尔:“我原本也以为是这样,但事实是,我一刻也没有从噩梦中醒来过。”
泽维尔偏过头,他的眼神有些空洞,茫然地落向漆黑的窗外。
泽维尔:“我很快就会死了,比兰总有一天也会消失在海平面之下。”
我心里一震,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寂寂的海面格外宁静,只有对岸的码头闪烁着零星的微光。
我看过有关比兰的新闻,环绕城市的海平面每年都在上涨,陆地也时刻都在被吞没。
在遥远的世界角落,每天都有东西在消失、在毁灭,但大多数人与它无关,残余的尘灰飞不到他们的眼前。
泽维尔收回视线,又一次落在陆沉身上的目光,却沉重得如有实质。
泽维尔:“总有一天没有人知道泽维尔家族的存在。重写那一页,把真实发生过的一切都记录进去。这就是我全部的请求。”
过往那些挑衅、威胁,还有虚与委蛇的面具,此刻统统不见了。
陆沉:“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
泽维尔:“我当然不确定你会不会答应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跟你很像。你和我一样,不择手段,也和我一样,厌恶着血族。
但有时候,我又不这样想。我只是在赌。赌你少写的那一笔。或许,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因为你的恻隐之心。”
不论他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向陆沉,陆沉始终沉默。
这个反应使泽维尔焦急。有新的菜肴陆续上来,但他不再去看它们。
泽维尔:“你还是无法回答我吗?”
陆沉抬眼望向他,瞳色似乎又幽深了几分。
陆沉:“如果我回答是,又会怎么样?”
泽维尔愣住了,他张了张口,好像有很明确的答案急于诉诸,最终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而陆沉,只是将一块银鳕鱼分到我盘中。
陆沉:“你猜错了,我与你看到的那些血族并无不同。少写的那一笔,并不是因为同情或是恻隐。而是,厌恶。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事情的结果没有任何差别。”
我看着陆沉,想要说些什么,他却示意我看向盘中闪烁着诱人光泽的菜肴。
陆沉:“吃饭吧,菜都要凉了。”
泽维尔看着陆沉,却迟迟未得答复,陆沉只是慢慢地、将剩余的几道菜肴也切割分好。最终,他也只能举起刀叉,将食物塞入口中,咀嚼着。
起初,他的咀嚼有些机械,似乎食不知味,但渐渐地,他吃得越来越快,像要用这些填满胸中的空洞。
直到他再顾不得吃相,有些菜肴甚至不经过刀叉分割,便直接吞入口中。
餐桌上更加安静,没有人再说些什么,只有烛台上的火苗偶尔跳动。
我也品尝着食物,就像是品尝着陆沉。尤其是那道陆沉做的菜,许多感受瞬时涌向我。
我知道,他厌恶血族,厌恶在一个被冠冕堂皇伪造的世界里,那些不必存在的愿望,和天经地义的牺牲,更厌恶被这些刻印的自己。
但我也知道,他在厨房里几次拿起汤匙,想偷偷尝一尝我做好的浓汤,又笑着放弃,把惊喜留到和我共同揭晓的那一刻。
我心里浮现出极其复杂的感情,但唯一清晰可辨的是,我很爱陆沉,我很爱他。
窗外忽然传来细碎的声响,泽维尔抬头去看,我也疑惑地循声望去。
陆沉:“看来,我们还有一些晚到的客人。”
陆沉起身,打开窗户……那些声响跟着变大,变得密集,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落雨。
一大团灰棕色的乌云,携着冷风从窗外涌进来,争相降落在宴会桌上,变成一只只猫头鹰。
爪印落在宴会桌洁白的绸缎上,它们不停拍打翅膀,转动着无神的眼睛,兀自享用着面前的食物,却又不时被飞来的同伴挤到一旁。
它们挤满餐桌,也包围着泽维尔。一只幼小的猫头鹰被挤下餐桌,又挥动双翅飞起,停在他的肩膀上。
泽维尔失神地看着猫头鹰,又看向陆沉,嘴唇张合,像说了一句什么。
但在凌乱的翅膀拍打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他说了什么?”
羽毛在我面前纷纷扬扬地落下,落成了一张密织的网,于是我看不到更远处的泽维尔,眼前的世界只剩下陆沉一个人。
陆沉:“他说,在他坐上这张餐桌的时候,他以为我会比他不痛苦。”
我又想起他先前独自走入的深夜,对泽维尔直觉般的了解,和每一步都不曾失误的周旋,它们就像羽毛,重新落回我的心里。
他不是了解泽维尔,而是熟悉在伤口结疤的过程中,被他解剖无数遍的自己。泽维尔是他的另一种可能,是他或许会走上的道路。
我:“你说,是为了那一段历史而设宴,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你请他来,其实是想看看他会做到什么地步。而他来,也是想看看你,对吗?”
陆沉:“应该是,尽管我也还不明白为什么。”
他低垂着头,看向我,神情无比柔软,丝毫不掩饰其中的迷茫,坦白得让我眼睛都有些酸涩
……铛、铛——钟声接连敲响了十二下,终于准确的时间。一种直觉告诉我,这一切虽然还没有找到完整的答案,但它们已经快要结束。
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要问他。
还有很多,哪怕———
陆沉:“宴席,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