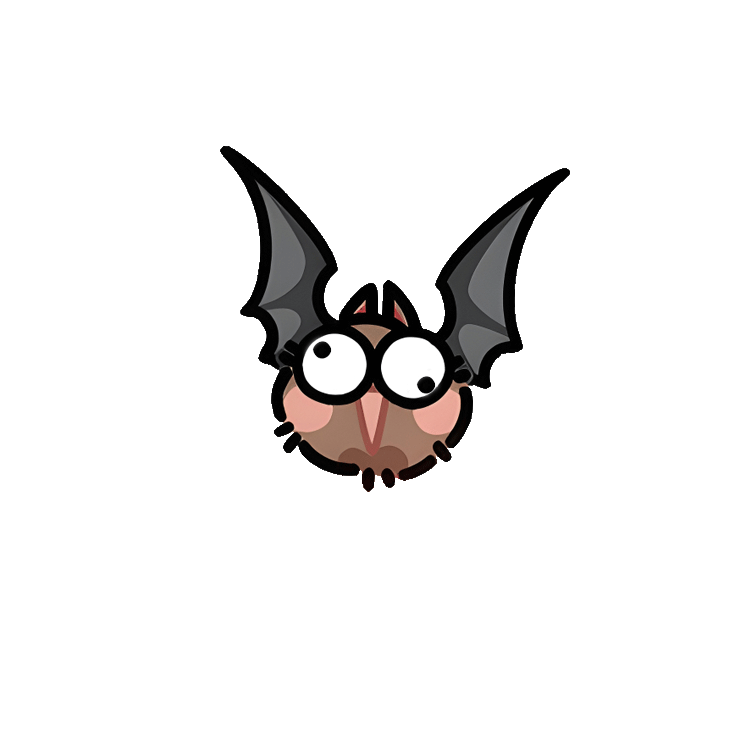❈世俗婚礼❈
我的目光划过安瑟尔字体写就的指示牌,落在最后一块上。
我:“Civil Marriage?”
陆沉:“世俗婚礼,或者叫做公证结婚。”
签字仪式和婚宴会在同一天举行,而司仪将在那天,来到婚礼现场进行公证。
不远处传来“砰砰”两声,喷射而出的彩带在阳光中缓缓降落,盖住了视线中新娘那胜雪的头纱。
继而人群里鼎沸喧闹,起泡酒甜腻的香气挥洒在半空,连装点的玫瑰也略带微醺。
我:“在众人的祝福中,和对方一起写下名字,听起来的确很美好。”
我望着草坪上被亲友簇拥的新人有些出神,直到掌心传来熨帖的温热。
陆沉牵起我的手放在唇边,轻轻吹走那片停在袖口的明黄色彩带。
陆沉:“看来,你已经有了决定。”
我:“当然,这可是整场仪式里最特别的环节!”
陆沉:“有你在,这比仪式本身,更让人觉得特别。”
藏在镜片下的眼角微微弯起,我也忍不住扬起嘴角,任由他牵着,交扣住他的五指。
六月的萨拉尔小镇,日光依旧温煦,仿佛还停在融融春日的尾声。
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服装区,一排排婚纱与礼服依次陈列,在灯光下显得尤为圣洁。我游走其中,一时犹豫起来。
陆沉:“慢慢试,我很乐意在这里,做你忠实的观众。”
一条香槟色的领带被我轻巧勾起,放在陆沉领口处比了比。
我:“让我犯难的不是婚纱,而是这个——选哪个颜色好呢?”
陆沉:“嗯……你手里这条,就很好看。”
陆沉宽厚的掌心覆上我停在他颈边的手背,将我们之间的距离缓缓拉近。
陆沉:“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系上它,好吗?”
我:“怎么这么赖皮,帮你选了,还要我帮你系?”
陆沉:“是人总有不擅长的事。”
陆沉笑得坦然,我只好踮起脚尖,将香槟色的ascot tie挽成一个复古的结。
我:“时间不早了,我先去换衣服。”
尽管参与过数次婚纱设计,但以“新娘”的身份进入更衣室,还是第一次。
宽大的落地镜前,我缓缓转动身体,带起拖曳的裙尾。
42姆重磅真丝泛出柔软光泽,鱼骨支撑的暗纹绣花则为慵懒的垂坠感平添了几分庄重。
深吸一口气,我紧张地掀开隔帘一角。
我:“陆沉,我准备好啦——”
一束炽白的灯光照射进来,陆沉不知何时,早已斜靠在墙边。
见我微微愣怔,他轻声笑了,伸手将隔帘掀到身后,钻进更衣室。
我:“你怎么进来了……”
陆沉:“你帮我选了领带,我也当然要为你选一件,与今天身份相称的礼物。”
陆沉抬起骨节分明的左手,食指指尖挑着一根蕾丝编织的缎带。
我:“是发圈吗,还是项……”
缎带末端的金属暗扣有意无意触在一起,发出清脆的轻响。
我这才意识到,它所应该出现的位置,既不是发间,也不是脖颈。而是更往下的地方……
耳尖升腾起莫名的温度,陆沉微微俯身,那镜片后的视线落向我绞动的双手。
陆沉:“怎么不说了,还是什么?”
我:“是袜带。”
我的声音不自觉弱下来,他却饶有兴味地抬起眉眼。
陆沉:“除了抛捧花,Civil Marriage还有一项传统习俗。”
仪式当天,新娘往往会在腿部绑上袜带,这是专属于她的幸运装饰物。等典礼结束后,再由新郎亲自取下。
陆沉有条不紊地解开袜带上的金属暗扣,“啪嗒”一下,和我的心跳重合。
随后,他的目光落向我的婚纱,长长的鱼尾贴合双腿垂落,形成一道流畅的曲线,却也限制了我的动作。
陆沉:“看来,想要自己佩戴,的确有些困难。”
我:“……嗯。”
陆沉:“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习俗,将“取下”改为……在典礼开始前,由新郎来为新娘,藏起这一份独属的幸运?”
明明是问句,可在他的注视里,身体却先一步行动,将裙摆轻轻提起。
我抬起腿,踩在皮质沙发上。那柔顺的绸缎自开叉口垂落,拂过皮肤的时候有些微凉。
陆沉的指尖先是停在脚踝,随后扫过小腿,接着一寸一寸向上游移。
陆沉:“能再抬高些吗?”
于是我踮起脚尖,将膝盖收拢。
遮面头纱自上而下笼在面前,透过薄薄的轻纱,射灯的光线也变得异常柔软。
在一片朦胧的暖黄色中,我看见陆沉挑起袜带,慢条斯理地将它绑在膝盖上方。
那小小的白色蕾丝袜带,被他用手指勾起缓缓向上,推至更隐秘的区域。
布料与皮肤相触的地方泛起一丝难耐痒意,我下意识地绷直了小腿。
陆沉:“我想,系在这个位置,应该刚刚好。”
我:“……谢谢。”
我轻舒一口气,迅速拢好裙摆。
高跟鞋重新落回地面,微微发酸的脚尖忽然发软,连同身体也失去平衡。
我:“!”
慌乱中,熟悉的苦艾香气压过来,一双有力的臂膀迅速将我拦腰环住。
横亘在彼此间的头纱悄然飘落,露出斜插在发端的三色堇。一朵花瓣从陆沉眼前飘落,他却微微怔住了目光。
我:“怎么了吗?”
陆沉:“没什么,只是装饰花歪了。”
陆沉伸手将我鬓角松散的紫色花朵重新固定,又将几缕碎发拢向耳后。
视线越过他的肩膀,能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此刻耳尖正慢慢透出粉色。
我:“本来戴的是白玫瑰,不过我想来想去,还是最喜欢三色堇。我尤其喜欢它的花语——”
陆沉:“沉默的爱。”
我:“你怎么知道?”
陆沉缓缓接话,可目光却从我身上移开,投向不知名的空虚。
我正欲说点什么,欢畅的交响乐隐隐传来,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陆沉:“走吧,仪式开始了。”
他牵住我的手,走出更衣室,走向铺满鲜花的长廊。
天气由晴转阴,原本明媚的日光被云层遮蔽,逐渐黯淡下来。
瑰色花瓣自四方飘下落在肩头,我低头看着长长的绒毯,一步一步抵向礼台。
或许这只是一次旅途过程中的偶然体验,然而在交织礼花与祝福的午后,我的心跳深处,却忍不住把它当作婚礼的预演。
站定在榉木所制的演讲台前,我和陆沉将手交叠相握,等待司仪宣读证词。
司仪:“你们一同诞生,你们也将永远合一。
当死亡那白色的羽翼击毁你们的岁月的时候,你们也将合一。
是的,当你们静心回忆神明的时候,你们也将合一。”
短暂的停顿后,司仪将一张鹅黄色的皮纹纸郑重地推至我们面前。
司仪:“陆沉先生,小姐。
倘若你们出于自愿,渴望缔结这场婚盟,现在,请在婚书上签署自己的姓名。”
我接过司仪递来的卓尔金夹墨水笔,握住笔杆的手指紧张地收拢,余光悄悄瞥向陆沉。
他低着头,银色笔尖停在署名栏许久,直到墨点在纸面上缓缓晕开。
我迅速收回视线,盯着空白的纸面发呆。
陆沉……是在迟疑吗?
下意识地,钢笔在皮纹纸上划开一道潦草的痕迹,继而“嗒”地一下,从手中脱落。
陆沉:“小心。”
听到陆沉的声音,我才回过神,匆忙转身去接。
指尖与钢笔恰好错开,弯拢的五指却不小心抓住了他伸来的手腕。
脉搏跃动的地方有些冰凉,忽然,我感觉一股不可名状的悲伤。
身后传来钢笔坠地的声音,咕噜咕噜滚出去好远。我却僵在原地,任由不属于自己的记忆侵入脑海。
——一张很旧很旧的婚纸,两个陌生的名字,墓边凋零的三色堇。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血液不住地落下,一滴,两滴,将婚纸染上点点殷红。
陆沉:“ , ?”
肆意蔓延的悲伤满溢心脏,我本能地松开陆沉的手。
再度看向桌台,才发现那纸面上的一点血色,只是氤氲的水渍。
乌云密布,鼻尖泛起了一丝湿润的微凉,我抬起头,原来是下雨了。
陆沉:“先去那边躲一躲。”
雨越下越大,《婚礼进行曲》的演奏戛然而止,只余下雨滴压弯青草的淅沥。
陆沉握住我的手,那一点温热的力量注入掌心,带我逃离骤雨忽至的广场。
疾驰的步履溅开无数水滴,当我们躲进尤尼克教堂的时候,正好响起14点的钟声。
雨水顺着发梢滴落,陆沉伸手拭去我唇角的水珠,拇指上残留下淡淡的珊瑚色。
我:“如果不是穿了高跟鞋,可以跑得更快。”
我提起裙摆,将脚踝露出,只见后跟处被摩擦得红红的。
迟疑片刻,我干脆把高跟鞋踢到一边,光脚踩在大理石地板上。
我:“呼——舒服多了!”
惬意地转了一圈,地面有些微凉,却令人无比自在。
陆沉弯起嘴角,似有些无奈,却任由我牵起他的手,穿过一排排空荡的坐席。
告解亭边,一把棕红色的大提琴孤独地倚在门边,它倾斜着身体,如同微微低头的信徒,在忏悔着什么。
我:“总觉得站在教堂里,好像自己的一切都会暴露在神明面前。”
陆沉:“明明是暴露,却成为人类安全感的来源。”
我:“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宗教的力量?”
然而,对于不属于人类世界的陆沉来说,暴露真实,无异于将自己的软肋双手奉上。
想起刚才所见到的记忆残片,我不禁抬起眼皮,偷偷向他瞥去。
余光里,那双深红色的瞳仁和往常一样平静如水,只是落向大提琴的时候,有一瞬短暂的失焦。
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吗……成为陆沉安全感的来源。
收回思绪,我俯身拨动那细长的尼龙弦,一缕低音缓缓泄出,回响在寂静的教堂里。
我:“陆沉。”
我转过头,捏住他礼服的下摆轻轻晃了晃。
我:“好久没听你拉琴了。”
陆沉移开与我对视的目光,在琴身上停顿片刻,才伸手将它拿起。
陆沉:“想听哪首?”
我:“听你现在想演奏的,什么都可以。”
我环抱着膝盖坐在地上,微微扬起的下巴看向陆沉。
他的身体位于琴凳的三分之一处,握弓的右手自然张开,架在身前的琴面略微向右倾斜。
陆沉垂下双眼,拉动琴弓,低沉的弦音从指尖缓缓流出,是《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抒情的曲调如同正在回忆往昔倏忽而逝的温情时刻,只是在淅沥而下的雨声里,绵延不断的音色却浮出淡淡伤感。
一曲终了,慢板乐章仍有震颤的余音,像告解结束时隐忍的哽咽。
空气静默下来,陆沉见我不说话,便将大提琴放在一边。
陆沉:“在想什么?”
我:“我在想,为什么你会选这首。”
陆沉:“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突然想到教我这首曲子的人。”
我:“你的老师?”
陆沉垂下琴弓,指尖轻轻抚过苏木弓杆,像是拂落了某段记忆的尘埃。
陆沉:“算是吧,不过她已经过世很久了。”
那天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演奏这部作品,今天是第一次。
我:“为什么?”
陆沉:“你似乎对她很感兴趣?”
陆沉侧目看向我,嘴角轻轻抿起,只是这一点笑意不如平时那般轻松。
我拢了拢散在地面的裙摆,也同样抬头去回应他。
我:“因为你说起她的态度,好像也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陆沉:“是吗。”
渐弱的雨声里,陆沉像是问我,又像是问自己。他停顿片刻,又继续往下说。
陆沉:“或许是因为人的感官总是相通的,当听到熟悉的旋律,就会掘出原本淡去的记忆。
很多年前的秋天,她生了一场重病,那段时间,她经常一个人坐在床边拉琴。
有时候,也会让我拉给她听。”
我:“大提琴是她的事业,也像她的情人,对吗?”
陆沉摇了摇头,起身走到告解亭面前,手掌轻轻贴上了木质门沿。
陆沉:“她的确很有天赋,不过恰恰相反,演奏大提琴对她来说,并不是值得钦羡的事业。
对于出生在血族的女性而言,才华只是一笔婚姻交易的筹码。
以此证明,这将会是一位家教良好的妻子。”
我:“所以,她是吗?”
陆沉:“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她永远不是。”
栖息在钟楼上的野鸽子飞腾起来,在白光里咕咕鸣叫着飞过,飞到黑暗里去。
空气沉寂,只有微光从穹顶的高窗户中透进来,渐渐消隐。
陆沉:“其实,《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不是她最喜欢的。只是后来反反复复演奏的,就剩下这一首。”
据说这是埃尔加献给亡妻的情书,在他疾病缠身的暮年,那位少将的女儿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她也是这样期待着吧?就像结婚誓词里说的那样。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会忠贞不渝,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
陆沉:“与其说是期待,不如说是努力确认。
在一遍一遍的弹奏中,确认那段所谓的婚姻,也有值得贪恋的时光。
遗憾的是,作为血族的女儿,当她签下婚书的时候,幸福就与她失之交臂了。”
陆沉垂下眼眸,疏离的目光落在教堂的墙壁上。
碎玻璃嵌成的神像,展演着各式各样的圣经故事,好像人世间的悲苦喜乐都一折一折地浓缩在此。
我:“那你呢,你也是这样认为的?”
想到刚才仪式上陆沉那片刻的迟疑,我环住手臂的五指不动声色地收紧。
陆沉:“只要是血族,都无法例外。”
我原本还想说些什么,陆沉却转过身,缓缓停在我面前。
陆沉:“起来吧,地上太凉,会感冒的。”
我握住他伸来的手,他宽厚的掌心带来余温,五指却比大理石地板更冷。
膝盖弯曲太久,起身的时候踉跄了下,脚底传来一阵麻意。
陆沉:“还好吗?”
我:“没事,只是小腿有点发麻……嘶——”
活动脚踝的时候,拉扯到了后跟的伤口,带来陡然升起的刺痛。
陆沉:“别动,让我看看。”
未等我应声,陆沉便半蹲下来,伸手握住我的脚背浅浅抬起。
冰凉的指腹划过踝骨,触到后跟磨破的皮屑,我绷直足弓往回缩了缩。
他立刻停下手边的动作,稍稍向前倾身,靠近略显红肿的伤口吹了口气。
温热气息扑过来,撩动起神经末梢的痒意。
陆沉:“现在呢?”
我:“……好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仔细看他。
深棕色的碎发柔软地垂下,下颌角也没那么锋利,藏在金丝边镜片后的双眼翕张着,带着几分不设防的漠然。
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一句话。
她们说,对女生而言,婚姻应该是一双合脚的鞋,才能陪伴自己走得更远。但是你看,就算是最最正好的鞋,也是会磨脚的。
陆沉依旧没有起身,他低着头,指尖一下一下抚着我踝骨下方的皮肤。”
陆沉:“还很疼吗?”
我:“疼。但我知道,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我搭着陆沉的肩膀,将赤裸的双足重新纳入那双银灰色的高跟鞋。
我:“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明知道那是一双不合脚的鞋,我也会穿上它立刻出发。”
陆沉:“就算流血了也要去?”
我:“嗯,就算流血了也要去,无论如何,都想去到对方身边。”
一声几乎难以察觉的叹息从身下传来。
鞋跟重新落回地面,横亘在脚背上的珍珠扣带碰撞出低响,如同回应着什么。
陆沉:“我曾经去墓地看过她。那天和今天一样,也下了很大的雨。我花费整个下午待在花店,却只买了一束三色堇。”
我:“因为“沉默的爱”?你认为她在痛苦和欢愉之间徘徊,然而这段婚姻最终剩下的,只有长久的沉默?”
陆沉:“鞋子或许可以,但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勉强的。”
一团晦暗不明的光圈浮动在裙摆周围,我提起礼服,蹲下身与陆沉平视。
我缓缓靠近他,直到那双红色的瞳仁里,能够清晰地倒映出我的样子。
我:“如果我说,我偏要勉强呢?”
陆沉的睫毛颤了颤,眼睛里长扬起雾气。
我环抱住他,两人的心跳交错悦动着,但渐渐地,变成同一个声音。
我:“陆沉,告诉我,血族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陆沉:“你想知道?”
我:“嗯,这对我很重要。”
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显得尤为冷清,我们来到神台边,将未曾燃尽的烛光缓缓点亮。
温柔的光线围绕着圣洁的神像,成为教堂里唯一令人温暖的角落。
陆沉:“在血族的仪式里,缔结婚盟的标志也被称作荆棘之吻。这代表两个陌生灵魂,从今往后将要共喜乐,也要同忍受。”
陆沉顿了顿,烛火的微光在他脸上跳跃。
陆沉:“ ,你真的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觉得似乎不够分量,又补充道。
我:“我明白。”
陆沉:“那现在,转过身去。”
在陆沉的引导下,我将身体背对他,视线里只剩下斑驳的彩色玻璃。
空气里静到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直到他沉缓的声音再度响起。
陆沉:“我,陆沉,请你做我的妻子,做我生生世世的伴侣和唯一的爱人。
你是我永不枯萎的欲望,你是我最深的堕落与沉迷。
我承诺永远地爱你,无论受到祝福或是诅咒,无论身处天堂或是地狱。
我将用双手带你走出绝望和痛苦。用我的心,酿造你的生命之醇酒。
如若永劫的暗夜来临,我将燃尽我的每一寸,为你照亮生的路途。”
当脚步声停下的时候,我转过头,向身后看去。
日光透过巨大的玻璃彩绘,倾洒在那条以忠诚为名的地毯上。
陆沉站定在我面前,拉起我的手在心口轻触一下,仿佛是在完成某种特别的仪式。
陆沉:“现在,请允许我向你求得宽恕。”
郑重的誓言落在心脏,产生细微共鸣。我缓缓收拢五指,反握住他。
我:“我宽恕。”
话音落下,嘴角蓦地沾上一片温热的柔软,在六月潮湿的萨拉尔,陆沉俯身将我吻住。
他小心翼翼地破开我的唇瓣,将铁锈味的鲜血一点一点吞入腹中。那只环住我腰际的手微微战栗,似乎正在努力控制某种危险的本能。
透过濡湿的声音,我终于明白,血族的荆棘之吻究竟是什么——
如同荆棘刺破彼此,让彼此成为自己唯一的欲望,才算得上献出魂灵。
两具身体相互抵在一起,直到头顶的玻璃花窗透出一束温暖的斜阳,我才缓缓抬起头。
我:“陆沉,放晴了。”
陆沉:“是啊,放晴了。”
熟悉的《婚礼进行曲》自礼堂外传来,我为陆沉拢好领带。
不知为何,眼眶有些微微发热。
我:“走吧。”
下过雨的草坪湿漉漉的,空气里满是泥土清冽的香气。
天色仍亮,夕阳隐没于教堂高耸的钟楼,只映出天际一抹极淡的橙红霞光。
我站在礼台前,挽住陆沉的臂膀,再度聆听司仪宣读证词。
司仪:“倘若你们出于自愿,渴望缔结这场婚盟——
现在,请在婚书上签署自己的姓名。”
不过这一次,陆沉手中的钢笔却被我坦然抽走。
陆沉:“怎么了?”
我抬起指尖,轻轻点了点桌台上的婚书,在他耳边放低声音。
我:“我想,我已经拥有了最好的仪式。”
黄昏里微风吹来,轻薄的婚书扬起一角,向尤尼克教堂缓缓飘去。
我和陆沉于无声处牵住了手,没有十指交扣,只是这样安静地握着。
恍惚中,我看见暖阳洒在教堂长长的楼梯上,我提起裙摆,一步一步地顺阶而下。
那漫长而短暂的阶梯尽头,是背身而立的陆沉。
陆沉:“你来了。”
他回头看向我,发梢浮动着点点金色碎光。
在时间的荒野里,我像是走了很久,陆沉也像是等了很久。
他屈起单膝,跪落在我面前。
他托住我纤细的脚腕,微微抚平一路上流血的脚腕。
他褪去我落满尘埃的高跟鞋,让我踏着自由的双足,跌入他的怀抱。
思绪回到满浸暮色的广场,暝色云雾下,那翻飞的婚书愈来愈远。
我:“你知道吗,司仪念的证词,其实来自一首英文诗。
诗的后两句是这样写的,Love one another——”
陆沉:“But make not a bond of love.”
即使没有这一纸,陆沉,你的名字,早就已经刻在我的心底了。